革命家想废除家庭制度已经很久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消亡中没有看到它的幸存。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思·费尔斯通将家庭视为所有性别压迫的根源,并在1970年的著作《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畅想了这样一幅图景:婴儿均用试管技术生育,以及(更少被人记住的)人们可以根据意愿随时进入和脱离的自选家庭。
酷儿女权主义理论家、地理学家苏菲·刘易斯在新书《立即完全代孕:女权主义反对家庭》(Full Surrogacy Now:Feminism Against Family)中检视了这些观念。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尽管家庭是人们逃离世界、寻求慰藉的地方,但她认为,这也给了人们寻求解脱的力量支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她断言家庭通过将一代代子孙引入等级制的方式,为资本主义添柴续火。和费尔斯通一样,她也谴责家庭对性别不平等观念的灌输。更尖锐的是,她认为体制将亲密关系转变为了商品,将孩子变成了如财产一般的东西:这是一种未来的私人投资,且只属于那些做了投资的人(即父母)。
为了瓦解资本主义,刘易斯认为人们需要一种“怀孕共产主义”——那是一个“人人都有责任抚养婴儿的世界,宝宝们‘不属于’任何人”,婴儿的孕育也将“为实现集体需要和愿望而分配执行”。在未来,生物学层面的血缘关系将会被“亲朋与友善”取代,人们终将意识到,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
在今天,做出这样一种无家庭的乌托邦畅想是很困难的。在特朗普时代,代孕已经成为一种男权压迫的象征。特朗普胜选之后,根据亚马逊的数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冲进畅销榜,成为2017年最受欢迎的书籍。在这部小说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寡头统领了美国,通过强奸强迫育龄女性生育孩子,将她们视作代孕工具。对新一代的读者而言,使女子宫的征用很快演变为了一场激烈的针对女性机构的攻击,尤其是在试图限制堕胎方面。对那些穿着红色女仆装冲进州府的支持堕胎抗议者来说,代孕的概念已经成为了所有性别不自由的象征。

刘易斯认为,如果觉得代孕本质而言是反乌托邦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去想象一个从平等姿态出发的、代孕者自由进行服务的世界。今天的代孕产业在宣扬一个观念:代孕者并不是真正的工作者,而是那些别无选择的贫穷女人的专利。刘易斯研究了纳伊娜·帕特尔博士——她是媒体红人,是位于印度阿南德的著名“阿肯克沙” 不孕诊所的创办者——是如何将代孕视为无技能女性摆脱贫困的途径的。在这个就业项目中,她们一边忙着学习“刺绣、机器缝纫、计算机、蜡烛工艺和美容护理”,一边等待子宫租约到期。
在一部关于该诊所的纪录片中,当一名代孕者抱怨帕特尔没给够工资时,诊所医生“将代孕者说成是游手好闲的穷人,她们只是在向体面的工作过渡,从而不着痕迹地为拒绝加薪进行辩护”,刘易斯这样写道。在这个逻辑下,“代孕毕竟就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双赢投资,与其说它是一项财富来源,不如说是一个实习。”(刘易斯并没有说明这种观念流传得有多广。她的大部分关于代孕产业的批评,都建基于她对这个小诊所的单一研究——这是个偶尔会让人感觉有局限的选择。)

与此同时,帕特尔把她为达到自己目的所做的贡献浪漫化了。在一次访谈中,她告诉BBC,印度代孕者的行为是出于对无子嗣夫妇的同情。刘易斯写道,代孕者仿佛“一个不计报酬的无产阶级”和“一个天使般的、富有同情心的志愿者”,她愿意奉献生命来“做任何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将怀孕看作一份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够想象代孕者们对工资讨价还价和罢工的场景。刘易斯引用了PBS的一段话,讲的是一名代孕母亲被禁止前往探望一位即将死去的家庭成员,她威胁说,如果不允许她去,她就“打掉”孩子——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健康的妊娠。另一名女性逃离了诊所,并且威胁称要留下自己生育的婴儿,以抗议监禁。这些战术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在许多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例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堕胎多属于非法,因此也就不安全。为了反抗而终结一个不想要的孩子的生命,代价也太大。不过,刘易斯认为,代孕要摆脱使女故事式的痕迹,必须建立在身体自主权的基础上,包括停止代孕的权利。如果代孕是一种工作,那么工人们就可以停止——这是一种真实权力的赋予。
刘易斯希望,在未来,被赋予权力的代孕者能“敲开”她们帮助创建的家庭的大门,要求一定程度的承认,这可以打破该家庭“自给自足”的幻象,提醒我们不可避免的纠缠。目前,许多委托父母选择不与代孕母亲保持联系,一些人在同意之后又改变了主意。每一张全家福,除了抱着孩子的爸爸妈妈,代孕者无迹可寻——刘易斯写道,每一张剔除了代孕母亲的照片,都像一个“难看的假体”,并强化着这样一种观念:核心家庭是自然的,没有其他选择。

刘易斯设想,在通往“怀孕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可能是一种代孕形式,它将取代在富裕的买家和他们寻求服务的落后国家居民之间建立持久纽带的做法(她说,在一个“完全代孕”的世界里,代孕将不会为了利润目的而进行)。在分子水平上,她认为这个行业已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这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还要多。“有一个简单但不常被注意到的事实是,怀孕的身体并不一定要区分含有和不含有自身DNA的胚胎,”刘易斯写道,“代孕行业曾保证,买家的孩子不会带着其他人的血肉,但揭示这一承诺的错误,可能会带来极端而混乱的后果。”
最终,这就是刘易斯在代孕中看到的乌托邦式的潜力:它提醒我们,生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繁衍,也并不存在“某人自己的孩子”这种东西。在子宫里,妊娠的过程如何影响基因表达的方式,答案仍在探索中。在此之外,即使是最规范的家庭的后代,也带有姑妈、叔叔、老师的印记——一个由其他人组成的完整网络。“我们是彼此的创造者,”刘易斯写道,“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如何那样行动。我想把这些真相称为真正的代孕,完全代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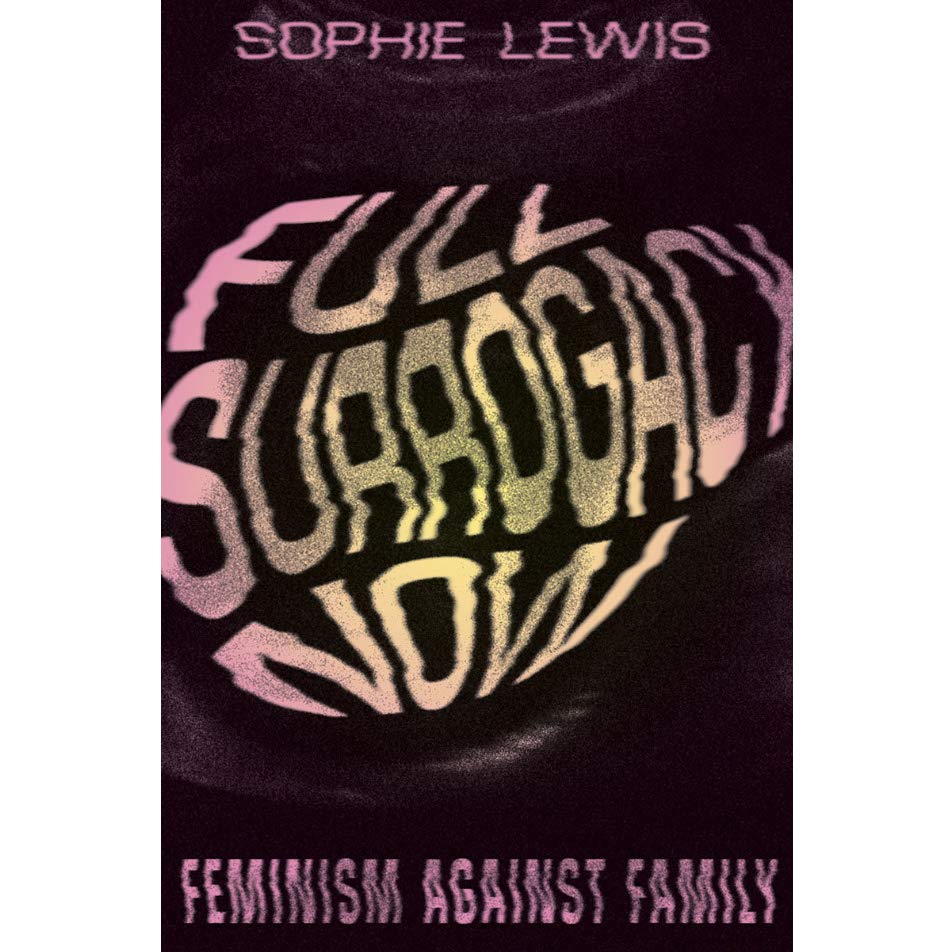
那么,“完全代孕”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刘易斯的乌托邦景象显然是去中心化的:怀孕的人并不因为所生育的孩子由国家抚养就不被称为“代孕者”,而是因为她们创造出的孩子将可以选择自己亲人。刘易斯引用的最具体的模型之一是费尔斯通的辩证法,它设想的共产主义“家庭”将由“十来个自愿的成年人”组成,他们将分担家务,并照顾他们亲生的或他们一起收养的孩子。在任何时候,儿童和成人都有权从现有家庭“移出”,进入另一个家庭(费尔斯通建议,国家在这项权利中应扮演强制角色,正如它今日在婚姻与离婚中的角色那样)。她写道,这样做的目标是“削弱和切断血缘关系”,直到所有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自然亲和的基础上,而不是出于需要或义务。
“成人/儿童的关系会像今天最好的关系一样发展:有些成年人可能更喜欢某些孩子而不是另一些孩子,就像有些孩子可能更喜欢某些成年人而不是其他人一样——这可能会成为终生的依恋。”
费尔斯通最令人难忘的提议是,所有的繁衍都是自动化的——这是“断绝血缘关系”的捷径,许多人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美丽新世界”。与前辈不同,刘易斯不相信自动化的“技术修复”将成为我们改变人类行为的手段。不过,正如费尔斯通所写的那样,她的最终目的同样是消除这样一种观念,即一旦一个人经历了怀孕,“所有这些痛苦和不适的产物(即孩子),就‘归属于’她。”
对所有乌托邦式的废家庭主义者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果想象中的未来到来之时,那种占有本能却拒绝消失,将会发生什么。社会或国家会强迫妇女把孩子交给社区抚养吗?看上去是不同的政治,但又回到了同一个使女故事式的反乌托邦。在《性的辩证法》一书中,费尔斯通简要地承认“怀孕本能”的存在会给她的项目带来问题——但她接着又说,一旦我们“摆脱文化上层建筑”,我们就不会发现这种与生俱来的驱动力。

刘易斯似乎同样相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人们会选择完全代孕而不是私人家庭。她在书中写到,作为一个人,她是通过同性友谊来维持生活的;而作为一名学者,她受到黑人亲属关系网络的历史和女性主义色彩理论家的著作的启发。她引用了黑人单身母亲姐妹会(Sisterhood of Black Single Mothers)的话,该组织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纽约女性组成,她们宣称自己的孩子“不属于父权制,他们也不属于我们——他们只属于自己”。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刘易斯看到了对生物学定义的亲属关系或亲属关系规定的所有权的观点的蔑视。“在我周围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能看到美丽的斗士,她们不顾一切地再生,而不是自我复制,”她写道。
以现有的状态将一个人增添到这个星球上,自我复制显然是一个不够充分的理由。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生孩子是给未来树立希望的一种方式——抛开其他所有——或者为帮助修复这个世界而贡献多一个人。刘易斯对完全代孕充满激情的主张让我想到,集体抚养的孩子可能会更好地为这项任务做好准备。毕竟,我们早已彼此依赖:一旦我们习惯了“我们属于彼此”这一观念,我们就会像危机一般,一边冲击着最脆弱的人,一边影响着人们行动起来。那听起来像是一种乌托邦宣言,但却更接近无可回避的真相。
本文作者Nora Caplan-Bricker是一名作家,现居波士顿。
(翻译:马元西)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