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天主教特拉普派修道士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就描述了科技悄悄渗入,并改造重组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景。他写道,“当然,照这样看,电视也许会成为对沉思的一种非自然的替代品,人们会变得懒惰迟钝,完全服从于那些粗俗的图象,堕入一种亚自然的被动接受状态,而不是升格,积极地汲取理解与爱。”就在默顿写下这些话的几年前,马丁·海德格尔也留下了类似的看法。再把时间轴拉长,他们都像是在重复柏拉图观点的基础上即兴发挥——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担心,当我们将口头的语言记录在书面上,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海德格尔说,没错,打字机就是这个时代的罪魁祸首,它遮蔽了人们写作的实质,“将人们的手这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挪走了,而人们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抽离。”
我们还在数字饱和的环境中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开始了离奇有趣的旅程。不管是肯塔基州修道院里的默顿,还是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尔,他们大部分的成人岁月都与世隔绝,这也让我开始思考今天的虚拟新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够逃离呢?我们对屏幕的热爱越来越深,已经到了沉迷上瘾的地步。行为指标表明,人们对化学药物依赖度与他们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变化曲线是非常吻合的。除此之外,有了这种复杂性和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动力,硅谷的天才也一直据此改写我们的神经回路,导致我们在数码设备上花更多时间。照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已经无药可救了。
幸运的是,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的《数字极简主义: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Digital Minimalism: 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提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困境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出路的。纽波特对于这个话题有着一种无可置辩的态度,言辞咄咄逼人,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言辞激烈。但这正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它毫不客气,坚称如果我们想要重建对数字生活的掌控,就必须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的行为。“照我的经验来看,”纽波特写道,“循序渐进地改变生活习惯并没有什么用。我们活在精心设计的注意力经济之下,各种便捷性会给我们的改变造成摩擦,最终抵消你改变的惯性,直到你滑落回起点。” 他提出了30天的 “数字断舍离”,也就是严格限制我们对科技的使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了问题所在,并且带着读者走过一个排毒脱瘾的过程;第二部分便开始给出建议,告诉我们要想建立新的极简主义自我应该怎么做。
纽波特之所以崇尚极简主义,是因为受到一群二十一世纪生活骇客和效率大师的影响,他们传福音般的鼓吹着自己“少即是多”的教义,其中《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亚·菲尔茨·米尔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 和瑞安·尼科迪默斯(Ryan Nicodemus)就是最有头有脸的两位。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极简主义者,同时也给读者推销一种观念:舍弃生活中那些多余的东西,不要让它们挤掉了我们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纽波特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技术,将数字极简主义看作是一种“科技使用的哲学”。他总结出了三大基本原则:杂乱成本昂贵、优化意义重大、意向性能令人满足。他认为,只要能完全改变凡事都拍拍脑袋说“有个APP可以解决”的思维模式,我们便能依靠真实具体的自己,想清楚面对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用到科技手段。如果需要,又该如何使用。反之,为了一点小事不断产生新的科技解决办法则是自讨苦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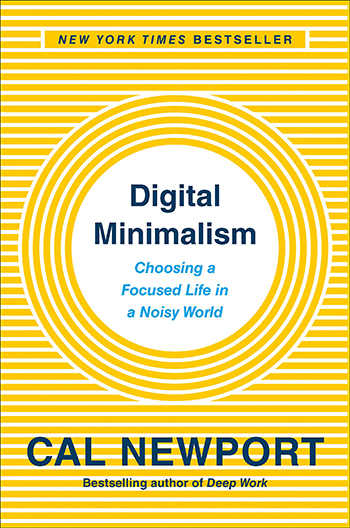
不过“数字断舍离”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我们重新回归那些简单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活动时,突破就随之产生了——我们要体验独处,学会感受面对面的交流,多进行有益的休闲活动。纽波特提出的这所有“实践”,隐含的根本要义就是把人们重新拉回现实的具象自我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倒退的现象学:起点是在数字环境下,我们的思想与肉体被剥离,于是需要让二者相互接近,直到我们的精神再生转世,重新进入我们天然的躯壳中。
为此,纽波特指出,由于技术的过度使用,我们人生中的三个核心活动已经被挤得没有立足之地了,它们分别是孤独、对话与休闲。这位作者借用雷蒙德·基斯利奇(Raymond Kethledge)和迈克尔·埃尔文(Michael Erwin)的定义,认为孤独就是缺乏 “外界观念的输入”。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有了完全弃绝孤独感的可能性,这还是头一遭。通过和数字世界保持距离,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无可否认,大多数人都会因此感到不安。纽波特还提出,我们应该学着给未来的自己写信,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不过感受孤独的最好办法反而简单得多,也就是独自行走。纽波特对林肯在华盛顿北郊小屋“士兵之家”待的那段时间评价很高,正是在这里,这位前总统得以从忙到头炸的白宫工作中抽出身来喘口气。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山间漫游的十年对他也有不容小觑的影响。这些抽身日常生活的日子给他们腾出了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好让他们更好地做出艰难的抉择,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正如纽波特所言,我们需要孤独才能发展进步,因为“人类没有插电,不能永远不间断地在线”。无独有偶,美国超经验主义作家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也是纽波特的精神伴侣,要想进城,梭罗一般会选择步行,而不是骑马或是乘坐马车,这样看来,他也不失为一个科技极简主义的典型范本。事实上,索罗还计算了他从瓦尔登湖走到康科德镇的时间,和他花费心力雇马车的时间正好抵消。不幸的是,在今天注意力经济的经销商面前,我们投降了,慢慢放弃了独处。纽波特在书中称,现代人为了换取一点点便利,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现在,我们的自我已经在数字环境中崩裂得东一块西一片,想要重新定位,必须付出更长的时间。
至于对话,纽波特指出了“高带宽交流”与“低带宽交流”的区别。他认为,交谈是一种高带宽的沟通方式。与其浸没在社交媒体中,接受其源源不断的信息炮轰,对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来说,交谈与对话更能够带来更加实质性的发展。讽刺的是,我们今天太过迷信“喜欢”这个按键,却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我们给别人点赞,却并不了解他人。事实上,我们摒弃了与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人际焦虑的鸿沟也进一步扩大,不管多少“喜欢”都无法弥合。在面向大学生的调查中,这种现象得到了证实。2011年,焦虑相关的疾病在大学年龄层的群体中激增,正是这一年,智能手机成了消费热门,青少年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手机。
根据他提出的这些实践活动,纽波特还从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性” (Entelecheia)理论里找到了灵感。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目的性和终点是其活动的内在因素。纽波特从而敦促读者发展自己的兴趣,但只应该以其产生的愉悦为目的。瑞典哲学家约瑟夫·皮普尔(Josef Pieper)也指出,这种休闲并不是工作之余无所事事的闲暇时光,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甚至可能是有着高要求高标准的脑力和体力追求。通过费神费力的活动,我们能够对抗自己对数码产品的渴望,将原有杂乱无章的低带宽沟通转化成高度结构化的高带宽社交,同时把我们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抽离出来,转而投入真实的世界,创造具体可触碰的东西。矛盾的是,我们在休闲上花的时间越多,为了挣脱数字旋涡需要耗费的气力就越少。
在2008年的电影《拆弹部队》有这样一个镜头,直戳人心。伊拉克战争期间,主角威廉·詹姆斯曾经带领陆军亡命连拆弹组,负责拆除爆炸装置。当他的海外任务告一段落,便回到美国,与家人短暂相聚。这一天詹姆斯一家人来到超市,妻子让他去找麦片。他在商场里到处兜圈子,终于找到了放早餐的货架。 此刻他眼前摆着数不清的诱人选择,虽然每一个都是那么无足轻重,但詹姆斯还是盯着这堆成一道高墙的硬纸盒看了好久,整个人傻了眼。放空了一会儿,他抓过了伸手可及最近的一盒,生无可恋地把它扔进购物车。

十多年来,每每想到这个片段我都心头一颤,它恰如其分地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我们需要清楚明白的决策来消除恼人的噪音,我们需要意义来把好生活的舵。面对几乎吞没我们时间的繁复商业与科技,我们寻求突破。总而言之,我们想要像托马斯·默顿说的那样,升格到一种积极的接收,体会理解与爱,或是像海德格尔努力探求的那样,找回与“存在”的紧密联系。
我们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些飘在天上的目标,目前还无从知晓。但如果打算开启这个旅程,第一步必然是清除数字世界的入侵,不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野蛮生长。在这一点上,纽波特的《数字极简主义》不失为一个好机会,让我们为之战斗。
本文作者Tayler Fayle是休斯顿大学的一名教学设计师,同时任教于自由主义研究项目。
(翻译:马昕)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