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Pengfei Li
编辑 | 黄月
民族主义势力近些年来正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人们渐渐开始担忧全球化的退潮以及“地球村”愿景消逝背后更深层的文明/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之间真的只有冲突这一条路吗?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追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源流与演变,在当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中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教条和价值取向由来已久,这虽然是一个相对模糊、众说纷纭的理论,但其核心理念“个人是宇宙/世界这个更广大的共同体的一员”还是很明晰的。世界主义可以从多个角度被言说——道德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政治世界主义、经济世界主义、基督教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共产革命的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等等。
在世界主义的昨天与今天之中,我们可以望见一条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通向未来的道路以及这条道路上的重重自问或他问:加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世界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吗?一个人的国家归属感和国家责任真的是在道德上优先于一个人的世界归属感和世界责任吗?“天下大同”的理想是否根本回避了世界秩序、国家权威与个体自由之间的调和?如果世界主义失去了世界性,我们是否还能抵达“地球村”?

世界主义的昨天
在古希腊的社会环境和哲学语境里,世界(cosmos)人和城邦(polis)人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希腊古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虽然已经有打破城邦人走向世界人的哲学进路,但并没有提出“世界主义”这个概念。但从柏拉图记载下来的苏格拉底对话篇的哲学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已经在用“人之为普遍人的拷问”(a man as a universal man)来打破雅典城邦对“美”“善”这些概念和价值的传统教条。

换言之,“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如此思考/行为?”在苏格拉底那里是被拷问的。“我是雅典的城民”与“雅典的诸神告诉我要如此思考/行为”在他看来已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了,因为地域性和独断性的价值教条和行为准则无法通过理性的审视。虽然苏格拉底没有在诸多哲学大问题上给出很积极的答案,但他坚信“未经审视的生命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这种“破”的哲学,在第一个直接言说世界主义的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那里被推向了一种“否定性的肯定”。在第欧根尼看来,他不要做任何一个城邦的人(否定),而要做一个自然人、世界人(肯定)。他并不是觉得做一个自然人、世界人有多伟大(否定),而是做一个城邦人太虚伪(否定性的肯定)。说实话,用“犬儒主义”来翻译第欧根尼的“Cynicism”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第欧根尼只是一个不合作的、玩世不恭的天涯流浪汉而已。这种古希腊“天涯人”的世界性有一种极强的“主体性”。在那个广为传颂的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第欧更尼的“犬”决非中国文化符号下的“狗”。当亚历山大大帝问可以为这位声名远播的哲学家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很干脆——“请不要挡着我的阳光。”换言之,第欧根尼把自己自嘲为一个“世界犬”,一个有原则(信奉自然)的世界公民——什么都吃,但是不臣服于任何一个地方和君主。

玩世不恭也好,犬儒主义也罢,“否定性”的世界主义是很难有众多追随者的。多数人也许天然地厌恶思考和怀疑,既没法接受“苏格拉底式”的、怀疑的、拷问性的人生,也没法接受“第欧更尼式”的、愤世嫉俗的、不臣服任何地方性的人生。确定性一直以来备受推崇,人们倾向于相信有个“地方”或有个“神”——城邦、家乡、国家、上帝、君主、长者——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可以做。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百家齐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变成了一家独鸣,世界主义也从古希腊“否定性”的世界主义变成了“肯定性”的世界主义。基督教世界里有两个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世俗之城”的人遵循着世俗的规则和习俗,而“上帝之城”的人践行着上帝的教诲。“上帝之城”不仅是整个世界的,而且是整个宇宙的。
这个“肯定性”的基督教世界主义充满了理论困境。一个奉行基督教教义的世界主义的确为信奉者们提供了更肯定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悖论——加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世界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吗?那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怎么办呢?当代世界或许仍有基督教神学家在试图证明只有基督教才是普世的,但这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学理层面都很难令人信服。
同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还是一种地域性的价值取向:它是源自地中海东岸和欧洲、在古希腊罗马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具有普世性和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但它也只是一种文化而已,并没有成为这个星球上所有人都信奉和内化的“文化”。

世界主义的今天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下的欧洲对世界主义的言说和我们当下的思考很像。不少欧洲作家和商人在欧洲各国迁徙式居住,有些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为任何一个国家负责。这种近代欧洲的世界主义和“第欧更尼式的”世界主义有着明显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加入了一个阶级的成分——衣食无忧、具有“世界性”才能和资本的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甚至跨大西洋的欧美大陆)“自由迁徙”。
这种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阶级性与当下惊人相似。谁可以在全球自由迁徙?别说普通民众,连每年可以跨国旅游的中产阶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和当下部分左翼学者把世界主义看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只有具备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世界公民”,才可以实践在现当代世界的迁徙自由。
撇开可实践性和经济基础,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纯价值取向——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真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又言之,一个人的国家归属感和国家责任真的是在道德上优先于一个人的世界归属感和世界责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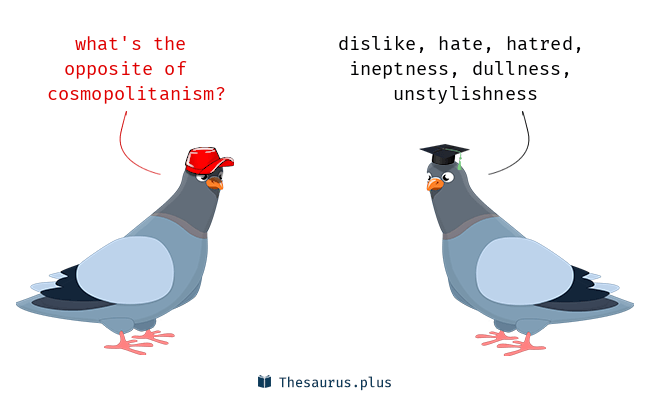
对于第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思想起源的问题来说,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被证明的,“思想/主义”诚然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但“百家的思想”没法被“百种的阶级”所决定。举一个在当代欧美(以及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学术人物思想为例,当福柯用“治理术”这个概念来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时——人们通过“自由”的消费完成了“自我规训”和“自我治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反思,很难说是被他“大学老师/学者身份”下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后一个问题属于道德哲学范畴,很多哲学流派对此争论数千年但仍没有答案。萨特在“一个法国士兵是该为法国而战,还是该留在家照顾母亲?”这个问题上持一个经典的存在主义立场——一个人做了什么道德选择,他就活成了那样一个人。当熊培云在他的“思想国”文章篇首便做出“我的世界时间在中国,我的中国时间在内地”这样的论断时,他没有提醒读者的是,他的这一论断并不具备道德哲学意义上的不证自明乃至超验性。
这个道德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个宽容的自由主义者会说,只要一个个体没有对他/她的国家以及世界带来伤害,他/她可以自由地选择对国家还是世界负更大的责任。一个充满激情的社群主义者会说,一个个体天然地对他/她所属的一个更小的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兴趣团体/一个职业团体)负更多的责任,国家和世界在他/她这里过于抽象和不着边际。一个刻板的儒家信徒会说,一个个体天然地对他/她的家人负责,从而延伸到国家,而后是天下/世界。一个洒脱的道家/庄子信徒会说,一个个体只不过是天地万物的一气而已,不存在什么对国家和世界负责。
如果说从纯道德哲学的讨论中我们无法得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的合法性的话,那我们同样也得不出世界主义的不合法性。更进一步看,在上文所述的四种价值取向中,自由主义最能接受世界主义的核心内核,道家次之,儒家和社群主义甚至与之直接冲突。
世界主义的未来
在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种“新天下主义”论受到追捧。简单来说,大部分言说新天下主义的学者似乎在用一种隐秘的方式证成及推崇一种新的“儒家”天下观。即,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里就有“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求同存异”等思想,这种思想再加以理论化不就是未来社会的世界主义吗?
而事实上,“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求同存异”并不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孟子的“性善说”“义利观”和“社稷民君说”,是宋明儒学的“理和心”。如果持新天下主义论的中国学者可以从“四海之内皆兄弟”中构建出一种新的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话,那它就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似乎比自由主义更支持世界主义的核心理念——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

部分当代学者(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试图为这个新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浇灌一个儒家的道统,并认为这个中国的“天下”比当下的(西方的)世界观念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在这样一个儒家伦理体系下的“中国的天下”,世界、国家和家庭的张力要如何调和?世界秩序、国家权威和个体自由又要如何调和?一种儒家文化的世界主义,很可能落入与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同的理论困境。既然都是地域的、群体的、加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文化,那又如何可以是整个世界的呢?这个由中国定义的世界主义理想的内核是儒家道统吗?
在中国学者高扬中国的“天下”大旗时,西方学者普遍在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进行后殖民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如前文提到的福柯)。这种中国的“立”和西方的“破”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即未来的世界在中国(东方),未来的思想也在中国(东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在《从天下理想到新世界主义》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一个未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既得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腔调,也得避免中国中心论和任何其他种族/民族/文化中心论的腔调,而真正走世界协商的道路。一个平等协商的、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任何厚重的世界价值在未来唯一可以实现的方式。
在这里,“厚重的”所指的是值得被进一步书写的,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相信并且被实践的多维度的价值取向。它不同于“单薄的”口号式立场。它指向的不是德国纳粹士兵“德国万岁”的狂热高呼,而是法国士兵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自己是要“为法国而战”还是要“照顾母亲”的复杂选择。
一个平等协商的、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必须得充分尊重各个地域、各个文化的特殊性,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协商性地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主义—— 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在多种文化的价值互动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第欧更尼式的否定性的世界主义是一种薄的价值取向,它并没有多少肯定的内核(但第欧根尼还是倾其一生实践他薄而反权威的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同样偏向单薄,因为它只是支持自由选择,而没法更有力地推动世界主义;基督教世界主义和儒家世界主义虽然是厚重的“世界主义”,但它们以某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内核来填充世界主义,从而让世界主义失去了世界性。在未来世界,如果人类想避免文明/文化冲突,其出路绝不是回到一种地域性的世界主义上去——无论这个地域是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美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