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全部诗歌的集合,准确地说,它收录的是公元前9到8世纪所流行的中国古代歌谣。在当时,人们生活的古代氏族社会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因此具有极强的封闭性质。在族长和宗老的强力统治下,民众难以与外界发生联结,只能遵循氏族内部的传统制度,他们信奉的神祇也具有排他性与好斗性。随着氏族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古代的小型氏族渐次解体,民众也因此获得解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歌谣作为人们最本能的抒情方式应运而生。正如《诗经》序言中所提到的“诗言志”,这些诗句本质上都是对自由之后的新时代的歌咏。人们相信,这是一个神人同在的时代,而歌谣就是他们与神祇之间交流、表达信仰的媒介。
有趣的是,在《诗经》产生以后约一千年的唐代,日本受其影响,诞生了一部同样宏伟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与《诗经》相似,《万叶集》也是由民谣发展而成的歌谣,它的形成同样基于民众的生活,因此可以理解为对社会史实的重要反映。在主题和内容上,《万叶集》与《诗经》亦有诸多共通之处,另外,《万叶集》大量地运用汉语俗语,或直接取用《诗经》中的语汇进行创作,也是其突出特点之一。从表现手法上看,二者都重视对修辞手法的使用:《诗经》中大量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分别代表直叙、比喻和隐喻;在《万叶集》中,发挥与“兴”相似作用的乃是“枕词”和“序词”。
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认为,无论是《诗经》还是《万叶集》,它们所歌咏的事物或行为都与过去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联,其中很多都具有象征意味,比如摘草、咏玉、穿衣、饮酒等。因此,“兴”的表达对于理解古代歌谣的性质至关重要。在近日推出的《诗经的世界》一书中,白川静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将《诗经》中不同主题的诗篇与《万叶集》中的类似作品进行比对研究,力图为读者还原一个鲜活的古代歌谣的世界。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从中选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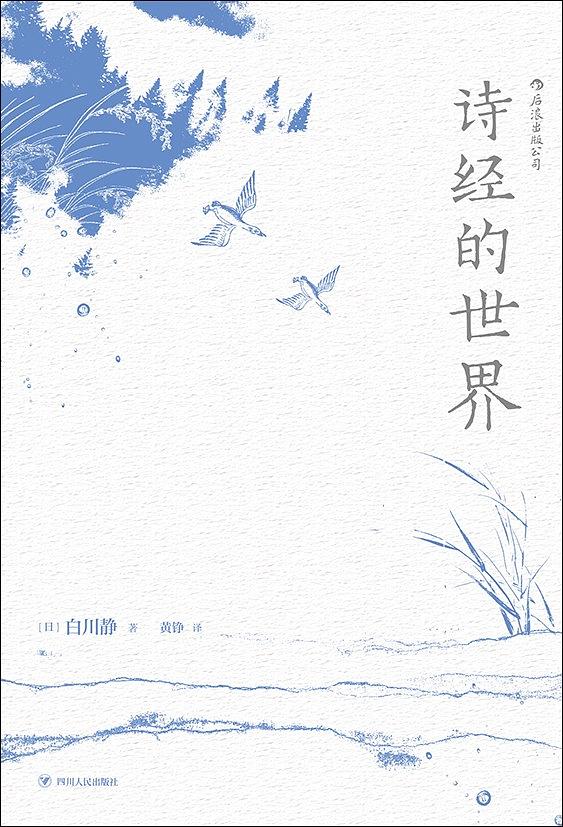
[日] 白川静 著 黄铮 译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6
《古代歌谣的世界》(节选)
文 | 白川静 译 | 黄铮
在历史迎来黎明之时,古代歌谣也正处在辉煌灿烂的时代。历史与歌谣是相伴产生的。《梨俱吠陀本集》的圣歌、荷马的史诗、《圣经》的诗篇,都属于古代歌谣。它们共同构成了各民族展开其历史与命运的序章。

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成书于前12世纪前后。于此时间稍晚——大概前10世纪左右,中国即开始了《诗经》的时代。虽然绝对年代上相当晚,但日本的《万叶集》也是具有上述古代歌谣特性的歌集。在各民族历史开始的时期,为何古代歌谣的时代会突然到来?这是一大谜题。
从历史时期而言,中国古代氏族的解体应始于西周后期,而日本则是在《万叶集》的早期时代。《诗经》与《万叶集》这两部古代歌谣集从本质而言具有很多相似性,都基于这种古代氏族社会崩塌的社会史实。两者都从此前被绝对畏惧的神灵咒缚之祭祀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进入了历史世界之中。每个人都于此第一次获得了自由。感情得到解放,爱恋与悲伤可以自由抒发。在新的视角下,自然是新鲜的,人们的感情也变得鲜明。这是人类在历史上首次经历的新生时代。人们追求共同的情感,遂将这种喜悦和悲伤形诸歌咏。这种歌咏并不似其他的古代歌谣,只歌咏深刻的冥想、胜利的喜悦,或表现对命运的恐惧。古代歌谣的本质,毋宁须求之于《诗经》和《万叶集》这种民众生活感情的丰沛表现。于此,与神祇同在的人们,从对神祇的隶属之中解放出来,在逐渐鲜明地歌咏中确立了现实感情的精神历史。
表达的样式
歌谣起源于令神祇显灵、向神祇祈求的语言。那时,人们还能自由地与神祇沟通。他们相信语言作为与神祇之间的媒介,具有咒诵的能力。对言灵的信仰就在这样的时代产生了。
在神人同在的时代,与神祇之间的交流,除了语言以外,还可以通过行为上的种种方面来进行。例如,神祇是否能实现人的愿望,可以通过他人无意间的话语占卜出来。通常来说,可以立于门外,将过往人言当作神托,是为“夕占”;规定距离,计算所走步数来占卜,是为“足占”。将献给神的一枝初柴付诸流水,据其起伏状态而占卜的“水占”,与刈柴的行事之间是存在着关联的。为祈求旅途平安而采集野草、编结草木等行为,其本身就具有预祝之意。以上这些咒诵的行为,都是在与神祇的约定基础上发挥效力,而这种约定也是神祇所认可的。
神祇是无所不在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当说到“问语草木”时,人们相信草木之中也有神同在。高大的树木尤为神圣,像鉾杉以及有蔓藤、寄生植物攀附的大树,必有神明居住。山峦苍翠,河流湍急,都是灵异之物的表现。即便仅仅纵目于此,也能看出其中的灵异之力、自然所具神秘之力,震撼着人的灵魂,为生命力带来充实。特别是林间鸟儿鸣唱,季节更替中鸟类奇特的生态,都让人们相信灵异的存在。鸟形灵的观念,不只在日本古代,也是一种通行于世的古代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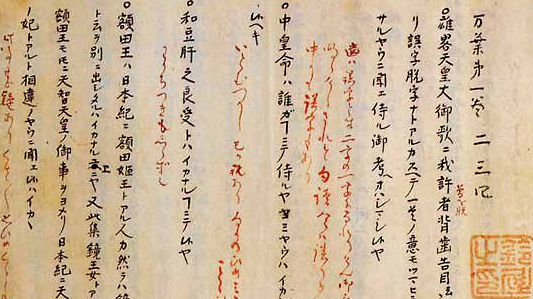
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在《万叶集》中见到的这种泛神论世界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咒诵性民俗,构成了这些歌谣表达的根基;在古代歌谣的解释中不能无视此一事实,这一点如今已成了常识公论。《万叶集》中往往沉浸于对自然的畏惧而至于毕恭毕敬的程度;若尝试从近代短歌的立场对《万叶集》进行再度解释,实际上是无法相通的。若无视古代歌谣的这种古代特性,则不可能将此文学置于正确的位置上。
上文说过,《诗经》的诗篇与《万叶集》的绝对年代虽然大有差异,但都是在相同的历史条件时期创作的。据此想来,诗篇的表达和《万叶集》也应该立足于同样的社会根基。诗篇里很多歌咏自然景象以及草摘、采薪等行为,这或许与《万叶集》相同,都具有咒诵歌谣性质的表达。
诗篇之所谓兴的表达方式,与主题的契合之处很难明了,这使得对诗篇的理解变得困难,也多有歪曲之处。以前对于诗篇的解释,常见到传说故事的附会,便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文将会详述:在婚礼的祝颂中,为何要歌咏束薪和鱼?在祭祀和征旅的诗中,为何会经常出现鸟兽的生态?在诱情之诗里为何歌咏投掷果物的行为?在哀伤之诗里为何会提到衣裳?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比喻,但其歌咏之中所蕴含的深刻意味,已经无法充分知晓了。

诗篇中所运用的兴的表达,与日本的序词与枕词那样固定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同是欲与神祇交流的表达和表现。所谓暗示性表达的兴,其本质是歌谣中古代咒诵歌谣机能的余绪。因之,它与当时的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人们从令他们强烈隶属于神祇的古代氏族制羁绊解放出来,进入到能自由表达感情的时代;即便如此,那种咒缚在古代歌谣的表达之中,作为规定着思维样式的古代观念,依然有深厚的遗留。不把握这一点,要在当时的存在方式下理解诗篇,便会困难重重。由于摆脱了从前注释学的或者印象性批判的解释,在古代人的生活和心理当中追求其表达情状,导入将《万叶集》的表现方式作为时代样式之一来把握的这种民俗学方法,对于《万叶集》的研究已经迅疾展开。于诗篇的研究中,这种方法亦应极其行之有效。
表现的问题
在诗篇的解释之中,除表达方式的问题之外,其表现的问题亦有古代歌谣独特之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其所歌咏的事物与行为,与古代的思维方式之间有着直接关联,其中很多都具有所谓象征性的意味。而这种象征性的意味,又与当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紧密相连。像是摘草属于预祝性的行为一样,歌咏玉和衣服,也是意味着这些物品能与佩戴者产生灵性的——有时甚至是超过于此的交流。像在歌咏风雨这样的自然景象时,并非用于对心理状态的比喻,而象征着具体的事实。论及表现与事实,则被表现的事物也成了事实,二者处于不能分离、彼此交融的关系当中。
在《邶风》中有《绿衣》一诗:
绿兮衣兮 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 曷维其已 (第一章)
绿兮衣兮 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 曷维其亡 (第二章)
绿兮丝兮 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 俾无訧兮 (第三章)
絺兮绤兮 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 实获我心 (第四章)
在旧说中,此诗是讽刺觊觎夫人地位的贱妾之诗。春秋初年,卫庄公因喜爱妾室,而抛弃了自己的正夫人,时人作此诗以为谴责。绿是间色,黄是正色,用正色的黄色来做里衣和下裳,间色的绿色来做上衣,是价值的颠倒,也表示正妃与妾之间地位的颠倒。当寒冷的秋风乍起,就将夏天用麻所做的絺绤扔掉了;失去宠爱的正夫人就像这夏衣一样。以前的世守其道,繁花似锦,却又不知从何得以说起了。
此旧说的解释,主要是从“绿衣黄里”“绿衣黄裳”这两句中推导出来的。用颜色的正色与间色来标明妃妾的地位,这是否就表明有贱妾僭上的意思呢?在儒家的经书之一《周易》坤卦中有“黄裳,元吉也”之语,是说黄裳为庆贺祝福之物。同是经书之一的《仪礼》中关于婚仪的《士昏礼》,以及《礼记》中规定礼服的《玉藻》里,都有提到“黄裳”一词,皆认定其为正服之裳所用色。从“黄裳”一词在文献之中的用例来看,并不存在贱妾僭上这类的解释余地。
《绿衣》这首诗是首悼亡诗,类似日本的哀伤歌或挽歌。绿色的御衣,黄色的下裳,都是已故妻子的遗物。见到遗留在家中的遗物,睹物思人。这衣服是妻子亲手缝制、精心而作,但如今却已物是人非。而今秋风吹拂,却不忍收起妻子遗留的衣物。这是一首思念亡人的哀切之歌。
衣服是包裹着人灵魂的物品,其人的灵魂亦在于此。所以哪怕只是暂时的别离,都可以通过衣物来思念其人。
以我衣为赠 见君奉于前 裹衣于枕放 夜夜寝安眠 《万叶集》四·六三六
(我が衣形見に奉る敷栲の枕を放けずまきてさ寝ませ)
妹赠予我裳 着身心欢畅 直至相逢时 终日不除脱 《万叶集》四·七四七
(我妹子が形見の衣下に着て直に逢ふまでは我れ脱かめやも)
男女相别之时,赠送衣物以表达爱意。第一首是汤原王的歌谣。寄托思念的衣物,是男女互相赠与对方的。在《唐风·无衣》一诗中,也有以衣物寄托爱情的描写:
岂曰无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 (第一章)
岂曰无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兮 (第二章)
这首诗的旧说讲,晋之武公是民望很高的君主,而不受周王室赐予其的七命、六命之诸侯命服。民众为此惋惜感叹,而作此诗。七命、六命是诸侯礼服,但此诗中“衣七”“衣六”的表现,并不符合这种解释。“虽然还有别的衣服,但还是你给的好。”一看就知道是喜欢所赠衣物的诗。衣物是用来表示爱情的。
筑波岭上桑 新发茧作衣 妾心只所欲 为君制所衣 《万叶集》十四·三三五〇
(筑波嶺の新桑繭の衣はあれど君が御衣しあやに着欲しも)
《无衣》与这首歌有着相同的表现手法。《郑风·缁衣》中,对赠送衣物也有同样的歌咏:
缁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首诗旧说是,仰慕郑武公德性的民众,送给他合身的黑衣,在休息的时候还奉上饮食,用以表达赞颂之意。松本雅明认为,上一首《无衣》是对贵公子的赞颂之诗,本诗则是对君子领主的赞颂之诗。但是衣服和饮食,在民谣之中乃是有关男女之情的表现。特别是很多描写饮食的诗歌,其实是极大胆的诱引之诗。例如这首《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 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第一章)
彼狡童兮 不与我食兮
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 (第二章)
这个女子喜欢的男子有很多相好,无论如何都不来女人的身边。
在《陈风》之中多歌垣之歌,自然有很多这种表现的诗歌。如历来被认为是隐士避世之诗的《衡门》,其实是描写幽会的诗歌:
衡门之下 可以栖迟
泌之洋洋 可以乐饥 (第一章)
岂其食鱼 必河之魴
岂其娶妻 必齐之姜 (第二章)
岂其食鱼 必河之鲤
岂其娶妻 必宋之子 (第三章)
朱子说:“此隐居自乐而无求与之词。”(《诗集传》)柴门废屋,是涓涓泉畔的幽会之地;“栖迟”一词因这首诗被说成表现隐居自乐的高尚生活,而在此实为约会的意思。饥代表着欲望,这诗必定讲的是要寻求更大的满足。
在二、三章中所出现的,魴也好鲤也好,并不单限于姜姓齐之姬君、子姓宋之姬君,而只是不选择对象的意思。鱼代指好的女子,新婚之歌必然有鱼的名字出现。鱼与女子之间有着何种关系,从《邶风·谷风》等描写离婚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其中有“毋逝我梁 毋发我笱”这样的诀别之语。在日本,也有将男女之间形容成山川中笱里的鱼的歌谣:
山间川流中 付筌守鱼空 相待八年久 悄然我自丰 《万叶集》十一·二八三二
(山川に筌を伏せて守りもあへず年の八年を我がぬすまひし)
在这首歌中也可以看出相同的联想方式。
这里对衣服、饮食、鱼三者进行了叙述。其表现方式的意味,只从言语的表面是不能够理解的。由于不能理解,遂使得历来对诗篇的解释,变得极不自然,有时甚至滑稽可笑。理解这些古代表现手法的关键,以现在尝试过的情况可知,或许可以大量求之于日本的古代歌谣之中。诗篇与《万叶集》表达基础的相似性,使得这样的探求方法成为可能。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诗经的世界》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