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的最后一个周末,还在英国议会的休会期,汉普斯特德希思公园天气晴朗。在伦敦“光是怎么进来的(HowtheLightGetsIn)”哲学与音乐节的一顶活动帐篷里,肖莎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教授正谈起她的新书《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的新疆域为人类未来而战》(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朱伯夫站在低矮的台上,与观众进行着眼神交流。她找出看上去心怀疑虑的听众,邀请他们提出自己的担忧。“这本书一月份出版的时候,我开始离家上路三个星期,”她说道,“而我至今还在路上。”
观众发出了笑声。因为《监视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对数字时代进行了700多页社会学分析——已经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畅销书,人们将其与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革命性著作相提并论。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力劝每个人都去读读这本书,以此来“作为一种数字化的自卫行为”。
这本书讲述了像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全球科技公司如何说服我们为了便利而放弃隐私,而被这些公司采集走的个人信息(“数据”)又如何为他人所用——不仅被用来预测、而且还被用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及这些做法何以为民主和自由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就是本书题目所说的“监视资本主义”,朱伯夫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以及“对关键人权的剥夺,最准确的理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
随后朱伯夫解释了她写这本书的原因。在角质框架眼镜之后,她有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以及浓密的黑色卷发和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她博学多才,用鞭辟入里、精心思考的措辞勾勒出自己的论点,就像是在大声朗诵一样。关于《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她最早的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她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正在写关于工业革命的博士论文。为了赚钱,她成为了一位组织变革咨询顾问,在那些头一回“电脑化”的办公室工作。“他们期待的是立竿见影的生产力、增长和效率。但得到的是混乱和灾难。疯狂的事情正在发生。人们说‘我们的工作是空中楼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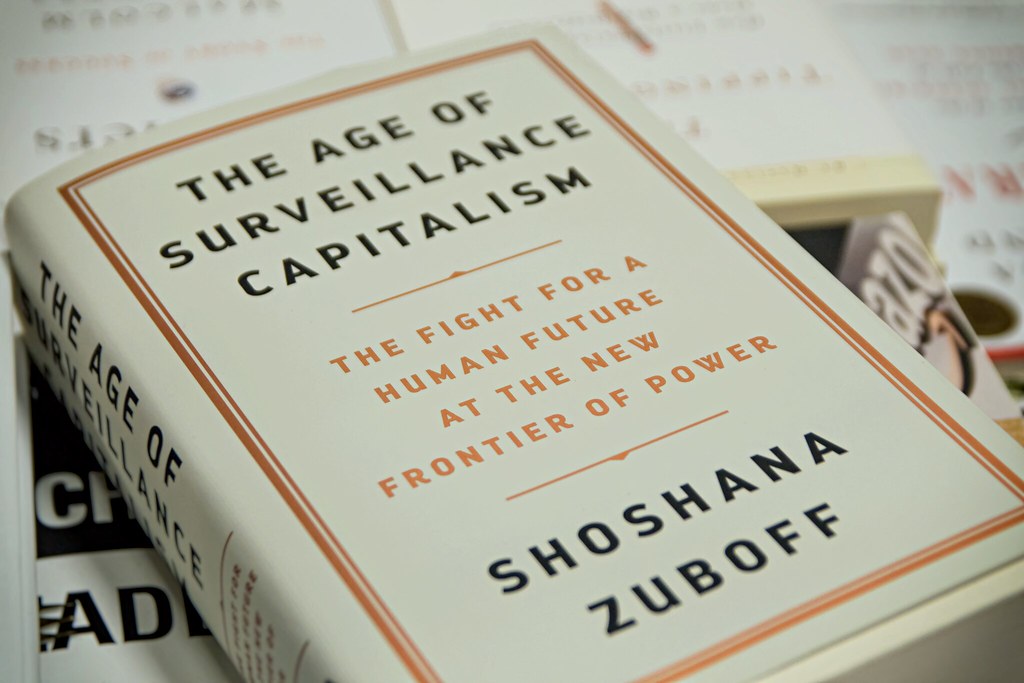
1978年,朱伯夫正在《华盛顿邮报》工作,那时报社的金属活字铸排机正被计算机照排技术所取代。“有天我刚上完大夜班,溜达进美国国家艺术馆,在那儿看到那些笨重、肮脏、黑乎乎的物件陈列在一座明亮的白色圆形剧场的正厅后排。”那是大卫·史密斯的“沃特利-博尔顿”系列——上世纪60年代,这位美国雕塑家用老旧的工厂机器和碎片来创作雕塑作品。“当时我意识到,电子计算机化的进程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而它将会改变一切——包括我们如何去思考、怎样去感受,以及怎样创造意义。我有个笔记本,于是我就动笔开始写。从那个时候起,这就是我精神生活的议程表。”
这引出了朱伯夫的第一本书:《智能机器时代:工作与权力的未来》,这本书针对信息技术将如何改变职业生活做出的分析拥有惊人的预见性。早在因特网浮出水面之前,朱伯夫就认为,所有能够被转化为信息的东西——包括交流、活动和物品——都将被转化为信息,而这样的数据流会被尽可能地用于监视和控制。那之后是她和丈夫詹姆斯·马克西明(James Maxmin)合著的《支持性经济:为什么公司对个人不利,以及资本主义的下个篇章》(Support Economy: Why Corporations Are Failing Individuals and the Next Episode of Capitalism)。马克西明曾经担任包括罗兰爱思(Laura Ashley,英国女装及家装品牌——译注)在内多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经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杰出学者奖学金,于2016年去世。

凭借她的第一本书,朱伯夫先是成为了哈佛商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后来又成为了最年轻的讲席教授之一。她和丈夫一起去美国缅因州的乡间生活,一起育儿,一起养鹿。2009年,闪电劈中了他们的房子,并在火光中将之夷为平地。这家人成功逃出生天,但失去了包括藏书、研究资料和证件在内的所有财产。“有件怪事:房子烧掉了,但那本从华盛顿特区带回来的旧笔记却得以幸免。”没过多久,朱伯夫就开始动笔写作《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了。
这本书讲述了数字革命以及互联网早期乌托邦式的愿景如何黑化成“资本主义的凶猛突变,特点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财富、知识与权力的集聚”的故事。Gmail邮箱于2004年推出,随后Google承认它曾经扫描过私人通信来获取个人信息。同年,Facebook成立,其商业模式同样建立在对个人信息的获取和访问之上。朱伯夫将之比喻为一种征服:“尚未被商品化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私密的人生经历是仅存的处女地。”在1986年,全世界仅有1%的资讯被数字化;而在2013年,这个比例是98%。
这是一场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预测算法和数学计算之上的运动。监视资本家(Surveillance capitalists)“把确定性卖给想要确切得知我们在做什么的商业客户。没错,针对性的广告,还有那些商家,他们想知道,无论是在向我们推销(车辆)按揭还是(车辆)保险的时候,应该如何向我们收费,我们开车安全吗?他们想要知道能够在一次交易当中从我们身上搜刮出多大的利益。他们想知道我们表现如何,从而获知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干预我们的行为”。要使你的预测令客户满意,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它们成真:“调和、牧养并形塑我们,并且推动我们朝着能够为他们的商业成功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做法)无法“被粉饰为除了行为矫正(behavioural modification,心理学术语——译注)以外的任何东西”。在2012年和2013年,Facebook开展了“大规模传染性实验”,以观察他们能否“在用户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现实世界中的情绪和行为”。

社会和个人生活当中常有紧要之处。譬如,一次画廊里的启示、一场灾难性的火灾,以及一本被抢救出来的笔记。而朱伯夫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更紧要的关头:“监视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和我们每个人之间一场巨大的斗争。它是对自由意志的直接干涉,是对人类自主权的侵犯。”它是对我们个人隐私细节——甚至是我们的脸庞——的捕捉。“他们无权触及我的脸庞,无权在我走在街上的时候采集它。”
朱伯夫说,这样的侵犯行为威胁着我们的自由。“当我们思考自由意志的时候,哲学家们谈论的是缩小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我们对自己许下承诺:我会在未来的那一刻去做些事情——去开会、去打电话。如果我们被当作一群‘用户’,被牧养和劝诱,那这样的承诺就变得意义阙如。我是一个独特的人,有着自己不可磨灭的力量……我应该决定我的脸庞、我的房子、我的车和我的声音是否变成数据。这个选择权应该在我。”
1951年,朱伯夫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她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她的外祖父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发明了自动售货机里的伺服机构。年轻时,她“在阿根廷长大,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上同过着简单生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她热爱自然,经常用农耕生活和农村环境来作类比。唯一一次她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停顿下来,是当一只有着漂亮蓝色羽毛的喜鹊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多漂亮的鸟啊!”朱伯夫告诉我,在工业革命初期,说服农民到工厂里做工就像让鹿去拉犁耕田一样困难。这太不协调了,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没过多久,鹿拉起了犁。这是社会性失忆症(social amnesia)出现之前一段短暂的窗口期。”
当我问起她所有这些经过了多大程度上的深思熟虑的时候——如果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拉里·佩奇(Google创始人之一)和谢尔盖·布林(Google创始人之一)只不过是一群快乐的科技乌托邦主义者,仅仅是在无意之中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呢?她报以苦笑。“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财富创造。”监视资本家有“许多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法律制裁。游说、政治窃听,以及其他一些我们通常与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垄断化的一种形式——译注)联系起来的经济手段”。 他们还声称,互联网是种新的现实,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协约:“拉里·佩奇曾经说,Google如何可能去遵循那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形成了的法律呢?——这就是种宣传(propaganda)。”
在这次哲学与音乐节的演讲当中,朱伯夫还否定了另一个观点,即这些公司是锐意革新的,只不过偶尔会犯错。“没错,就像Google Nest(Google的家庭安防系统)那样:‘哦,很抱歉,我们在Nest的监控系统里放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就忘了!我们忘记把它放进示意图里了。”(这篇报道是今年2月曝光的,Google称未能将麦克风列明在技术规格上是“一个差错”——原注,Google所使用的error一词有“无心之失”的意涵——译注)
那么,扎克伯格主张的“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埃里克·施密特(2001年至2011年间任Google首席执行官)关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建议又如何呢?当然,朱伯夫已经听过这句话千百遍了。重复这些话的不仅有监视资本家,还有赞成对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的政府。她轻快地回答道:“我对人们说,如果你没什么可隐藏的,那你就什么都不是。这并不是哈耶克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这是个体化与政治自由和民主携手并进的历史性进程”。这同样无关乎奥威尔,无关乎于“老大哥”。“没人会送任何人去古拉格。它(指监视资本主义——译注)不想杀掉我们。它只是想让我们朝着它预期的方向前进,并且获取数据。”不过,“在有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将这些技术纳入专制国家的企图。”
还有些人提出,如果使用得当,“建构选择”——助推和劝诱也可能对社会有所裨益。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包括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二人是《助推:改进关于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策》(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一书的合著者——原注】。朱伯夫对此强烈反对。“一旦你认同了“ex-machina”式(取自于拉丁习语Deus Ex Machina即“机械降神”,意思是“来自机器的神”,源自于希腊悲剧中饰演神的演员会从舞台顶端的平台(机器)上降下来解决剧中问题,后被引申为介入改变局面的外力或外人——译注)说服的合理性,那就令人无法忍受了。这是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行为,而不是教育或警醒。助推行为是家长式作风。像塞勒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助推行为合理化,是为监控资本家赋权而且壮了贼胆。但塞勒获得了诺贝尔奖。”
为什么她这么在乎?“多年来,我为了写这本书付出了很多时间,”她这样说道,“我付出了同丈夫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付出了我的健康。我付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同社会失忆和精神麻木的进程作斗争——人们正在失去他们的惊讶感。”是的,她同意“斯诺登为唤醒人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技公司也牵涉其中”。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正从雅虎、Google、Facebook和微软那儿收集数据。而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呢?“卡罗尔·卡德瓦拉德(Carole Cadwalladr,Facebook与剑桥分析公司丑闻的报道作者——译注)的作品十分英勇。而克里斯·威利(Chris Wylie,剑桥分析公司的线人)则透露出,剑桥分析公司的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只是在模仿一个监视资本家的生活日常。”如果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开展行为矫正呢?为了选票,而非购买?“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民主政治已经岌岌可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监视资本主义的运作。”
每当朱伯夫当众讲演时,她都会向听众发问:“是对什么东西的关切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人们大声喊出一些词:隐私、反乌托邦、控制、垄断、操纵、侵入、剥削、民主、误导、恐惧、自由、权力、反叛、奴役、抵抗。实际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听众喊出来的词都差不多是这些。我们能做什么呢?人们提出反对,但却无事发生,这难道不会令人心生倦意吗?“监管,”她坚定地说,“这是科技公司最害怕的东西。我们认为交易人类的未来是不合法的,就像奴隶贸易被定性为非法一样。”于是我们设计“能够闭环运行的程序(programs as a closed loop)”,并且“重申这一观点:我们能够在免于监视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拥抱数字化”,这需要公民、记者、学者和立法者的“义愤”。“监视资本主义游离法外已经有20年了,但它仍然还很年轻。”
在后一天,朱伯夫会做另一场演讲,并向另一群听众发问:“是对什么东西的关切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就像是Facebook主页上那个老问题的翻版:“你在想什么?(What’s on your mind,简体中文版页面显示为“分享你的新鲜事吧”——译注)”
朱伯夫已经在路上奔波九个月了。而另一条路,也就是在无所事事中被“纯粹的权力所统摄”并不是她的选择。“我们不是简单的用户(user)。我们经常是被利用的(used)。我们必须醒悟于我们所共有的未来。”
(翻译:李元哲)
来源:卫报
原标题:Shoshana 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is an assault on human autonomy’
最新更新时间:11/01 10:23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