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安妮·博耶(Anne Boyer)在过完41岁生日的一周后,便被诊断出患有三阴乳腺癌。她必须要接受副作用严重的化疗和两侧乳房切除手术。小说家詹恩·阿什沃思(Jenn Ashworth)在30多岁的时候,曾因剖腹产而大面积出血。当时,硬膜外麻醉效果已经消失了,但医生们并不知道。于是,在接下里的手术中,虽然她没办法讲话和移动,但是她的意识一直很清醒。这次经历使得她患上了长期的创伤后精神病。她总觉得自己小时候曾杀死了一个婴儿。
这些都是叙事事件,是生活中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但是,它们同时也是不利于叙事的事件,特别是对于工作便是叙事的人来说。这两本精彩的书籍——《死不了》(The Undying)和《病中笔记》(Notes Made While Falling)——都是反回忆录式的回忆录,拒绝个人化的个人描述。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发现一种新的语言和形式结构,博耶将其称为“痛苦的漏洞民主,痛苦的共同景象”。
这两本书中也对一种药物进行了控诉。这种药物曾挽救过这两位女性的生命,但她们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博耶还曾说过:“我的生活是一种奢侈的商品,但我却被腐蚀,被肢解。”)。这种治疗需要以毒攻毒,需要切开病人。甚至,服从诊断便意味着病人被客观化和抽象化。医生考虑的不再是病人本身,而是将其转变成一系列对患者来说可能尚不清晰的症状。服从诊断能够获得奖励,而异议则不受欢迎,女性的异议尤其如此。阿什沃思总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裂开了,内脏掉到了脚下。这种感觉无处不在,甚至她都没办法系上安全带,必须要用绷带将自己的腰部包扎住。几年之后,一位医生才想起来向她解释道,这个症状并不是她的幻想,而是外科粘连的结果。用正常的话来说,就是她的器官粘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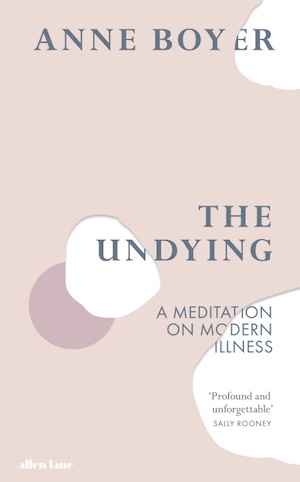
博耶对这个行业的商业性特别感兴趣。是谁在工作,又是谁从中获利?阿什沃思在发烧昏迷的时候,曾撞倒一台价值2万英镑的机器。当时,她被一名护士责骂了,内心还充满内疚。但是,并没有人向她出示账单。另一方面,博耶是一位美国人。她将自己接受治疗的地方称为“癌症馆(the cancerpavilion)”。这个地方的主营业务并不是照料病人,而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获取利益。博耶是一名教授,但是,她化疗一次的费用就超过了她的年薪。尽管她有健康保险,但是,在两侧乳房切除手术结束后,她必须立马下床离开医院,而因为麻醉和休克的原因,当时的她还昏昏沉沉、踉踉跄跄。十天后,她必须要重返工作岗位。她举办了一场三个小时的讲座,讲解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而当时,她胸前的伤口上还绑着外科引流袋。毋庸置疑,任何打算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进一步私有化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死不了》这本书。
如果说病床有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可能认为这很自恋。但是,这里主要反映了集体性。尽管灾难无处不在,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正如阿什沃思所说:“这个世界确实包含着许多事实,其中一个事实便是,一些身体对某些类型的灾难拥有某种形式的免疫力。”鲍耶在接受副作用严重、生命受到威胁的治疗时,会去想象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被关押的女性接受化疗,没有保险的病人无家可归。
所有人的疾病都有相似的原因和结果。人们吃下那些原本作为化学武器的药物,这会对生态造成不利,也会让个人蒙受损失:人们会失去睫毛,会神经衰弱,工厂排放的污水和人们受到污染的尿液会让河流中充满毒素。患上癌症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基因或选择不良,还有可能是环境导致的,是晚期资本主义中被污染的养分,例如有毒的空气和水源所带来的结果,博耶将此称之为“致癌大气”(carcinogenosphere)。甚至连粉红丝带都十分可疑。粉红丝带是乳腺癌组织苏珊科曼乳腺癌基金会(Susan G. Komen)的标志。这个组织曾借此牟取暴利,它开展“强有力的公共关系运动,以反对……激进分子针对它的批评”,并在2014年与Baker-Hughes公司合作,制作了一千个粉红色的水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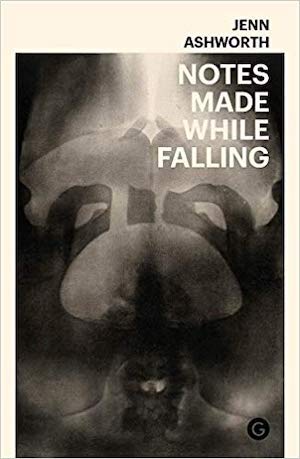
博耶写道:“癌症有着近乎犯罪般的奇异之处,这意味着对它的任何研究都会像证词一样。人们会根据它的真实性,实用性或感觉深度,但很少根据它的形式来进行判断。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却不得不接受。”但是,两位作者的主要兴趣,也是两本书最大的乐趣在于,她们在叙述这些复杂曲折的故事时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建构、创新和野心。特别是阿什沃思,她在近乎疯狂地寻找一种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形式,去捕捉创伤的波动、闪烁、跳针、脱轨的本质。她尝试用断断续续的叙事方式,来打破时间的桎梏,强调痛苦的当下状态。她解释说:“创伤的‘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无法解释的方面,并不是创伤本身——至少并不总是——而是‘现在’的后果。齐格弗里德·沙宣(Siegfried Sassoon)写道:‘那时不是他们的邪恶时刻,而是现在。’”鲍尔拒绝去充当“主显节的天使”,而阿什沃思同样也在严厉指责轻易便能够得到救赎的结局。伤害和精神病的故事难道不是更真实的说法吗:就像是突然间充满意义的随机数。这两位作家都是学者,也是犀利的文化评论家。阿什沃思曾评论过《德古拉》《东方快车谋杀案》、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和《李尔王》。鲍耶观看癌症短视频博主,读过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病床上写的《突发事件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以及小说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对她在1811年完全清醒时所进行的乳房切除术的叙述,范妮·伯尼用了很多年才走出了这种经历的影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没有一个词可以描述颤抖和头痛。这两位作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正如博耶所说:“几乎每一部描述疾病的文学作品都会说:没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去描述疾病。”撰写这样一部作品可能意味着要像博耶那样,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寓言故事,或者是像侦探一样,搜寻自己的过去。在她恢复期间,阿什沃思躺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痴迷地看连环杀手纪录片,她废寝忘食,试图在这些纪录片中寻找自己所遗失的受伤时的事实。她曾叙述过和《摩门经》一模一样的童年,还描述过有暴力倾向的父亲。对母亲家中的照片进行分类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记忆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偏差,并因此而感到震惊。但是,写作并不能填补这些空白,只能让它们清晰可辨,成为故事中的一部分。
你如何找回那些被拿走的东西呢?如何找回自己的整个身体,那个健康的、未被切割的自我?答案是:你做不到。作为补偿,你能得到的,是发现博耶所说的“死亡的华丽框架”,这是脆弱性的共同基础。这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也是一个写作的好地方。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比这两本更好的类似著作,那我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翻译:尉艳华)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