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12日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这一新闻在短时间内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通常在啮齿动物之间流行,偶尔能引起人间流行。近年来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中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至10例左右。
鼠疫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令人恐慌的传染病,清代文人师道南所著的《死鼠行》这样描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也曾饱受鼠疫疫情之苦。有历史记载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有三次。第一次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导致东罗马帝国全国人口死亡近半,并几乎蔓延至当时所有的知名国家。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14世纪的中亚,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导致欧洲人口四分之一死亡,史称“黑死病”,它给世界造成的混乱、恐慌与损失不亚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大流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源于1855年的云南,于1894年在广东爆发,传至香港后,经过航海交通散布至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期间全球先后死于鼠疫者达数千万。

第三次鼠疫流行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渴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医学工作者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人类开始对鼠疫有了真正的认识,研究科学的防治措施,使得疫情得到控制。在下面这段书摘当中,《瘟疫与人》一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探讨了19-20世纪的源于中国的鼠疫大流行,他看到,人类真正了解鼠疫是从1894年的香港开始的,虽然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但鼠疫大流行也得到了医生团队的有效遏制,是现代医学中“最富戏剧性的胜利”。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节选)

文 |[美]威廉·麦克尼尔 译 | 余新忠 毕会成
故事开始于中国腹地。早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抑或更早时代,鼠疫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就已作为地方病扎下根来。19世纪早期,萨尔温江上游构成了感染区与未感染区的分界线。后来,1855年云南爆发了起义,中国军队跨过萨尔温江前往镇压,由于未意识到鼠疫传染的危险,染病后的军人就把它带往各地。此后,鼠疫接连暴发于中国内地各处,但未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1894年该病传至广州和香港,给当地的欧洲居民带来了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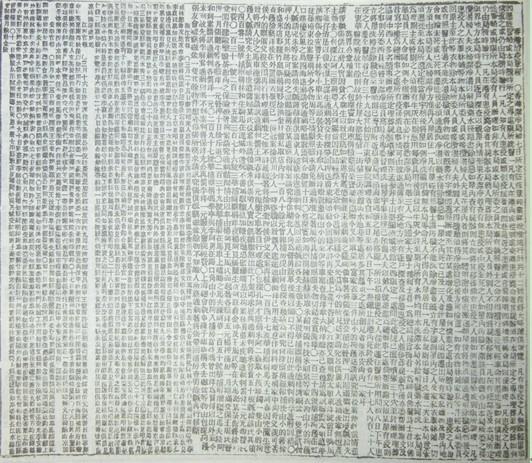
1894年,细菌学说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鼠疫在中国的出现,激活了欧洲梦魇般的民间记忆,受业于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和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德国细菌学家)的弟子们急切地要去揭示其传播的秘密,国际研究小组于是被派往现场。仅在他们到达香港的几周内,一名日本和一名法国的细菌学家(译者注:分别是北里柴三郎和耶尔辛),就分别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即鼠疫杆菌(1894年)。在随后10年间,从事这项研究的国际医疗特遣队在香港、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众多地区展开研究,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之逐渐浮出水面。
在鼠疫出现在香港的10年里,世界所有的重要海港都经历了这一可怕疫病的袭击。这一事实,也不断强化了国际社会对鼠疫的关注。在大多数地方,传染很快被遏制了;但在印度,鼠疫却深入内地,在它到达孟买(1898年)的10年中造成大约600万人的死亡。
鼠疫接连不断的小规模暴发,以及有可能给欧洲、美洲和非洲带来重大灾难的风险,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渴望。最具意义的发现之一便是,在美国、南非和阿根廷,穴居的野生啮齿类动物群落甚至比人更容易感染鼠疫杆菌。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地鼠最先被发现感染了鼠疫,同年,该病局部地流行于旧金山的华人当中。鼠疫在人群当中很快消失了,但杆菌仍兴盛地存活于地鼠之中,并一直持续至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类似的传染病在感染了南非的德班(Durban)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又很快在德班以外的南非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阿根廷的穴居啮齿类动物群落中被发现。
上述啮齿动物在种类上存在区域性差异,与亚洲穴居的啮齿动物群落也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啮齿动物的洞穴里,不管混居着哪些种群,对杆菌的态度都被证明是友好的。事实上,自从这种传染病在旧金山外围地区首次出现后,北美受感染的地区逐年增加,到1975年,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疫源地,并且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如此广阔的感染区域,事实上不比旧大陆任何长期的疫源地逊色。
考虑到穴居啮齿类动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疫病从一个地下“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地下“城市”的条件,鼠疫在北美的地理扩张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当啮齿类动物的幼崽稍稍长大时,它们就被父母逐出老洞穴,到处乱闯,甚至干脆远离群落,漫游几英里寻找新家。这些盲目的漫游者,一旦发现新的啮齿动物群落就会企图加入。这种生活方式给它们提供了交换基因的绝佳途径,也使它们从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进化优势;但也为群落间的疫病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传播速度高达每年10~20英里。此外,人类活动亦加快了鼠疫在北美啮齿动物中的传播。牧场工人把生病的啮齿动物装进卡车,以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目的是让它们把致命的鼠疫传染给那里的草原松鼠,尽可能地消灭它们,为牲畜留出更多的牧草。然而,北美鼠疫的传播在受这类行为影响的同时,却并不限于人类的干预。结果,到1940年,美国全部穴居啮齿动物至少有3/4的种类都携带鼠疫杆菌,各类跳蚤中也有3/5被感染。
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然而,1911年(译者注:实际应为1910年,宣统二年冬),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暴发于满洲,又复发于1921年。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随后的调查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但到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长期禁止关内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官方规定不再被遵守,毫无经验的大批关内移民追随土拨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鼠疫最先在他们中间暴发,并使哈尔滨市迅速成为鼠疫中心区,然后从这里出发,沿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1894—1921年的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具有职业敏感的医学小组的眼皮底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确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传染途径和传播路线。没有这些研究和随后的预防性措施,20世纪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躏,由此造成的死亡将令那些查士丁尼时代留下的记录相形见绌,甚至14世纪肆虐欧洲和旧大陆的黑死病,也无法与之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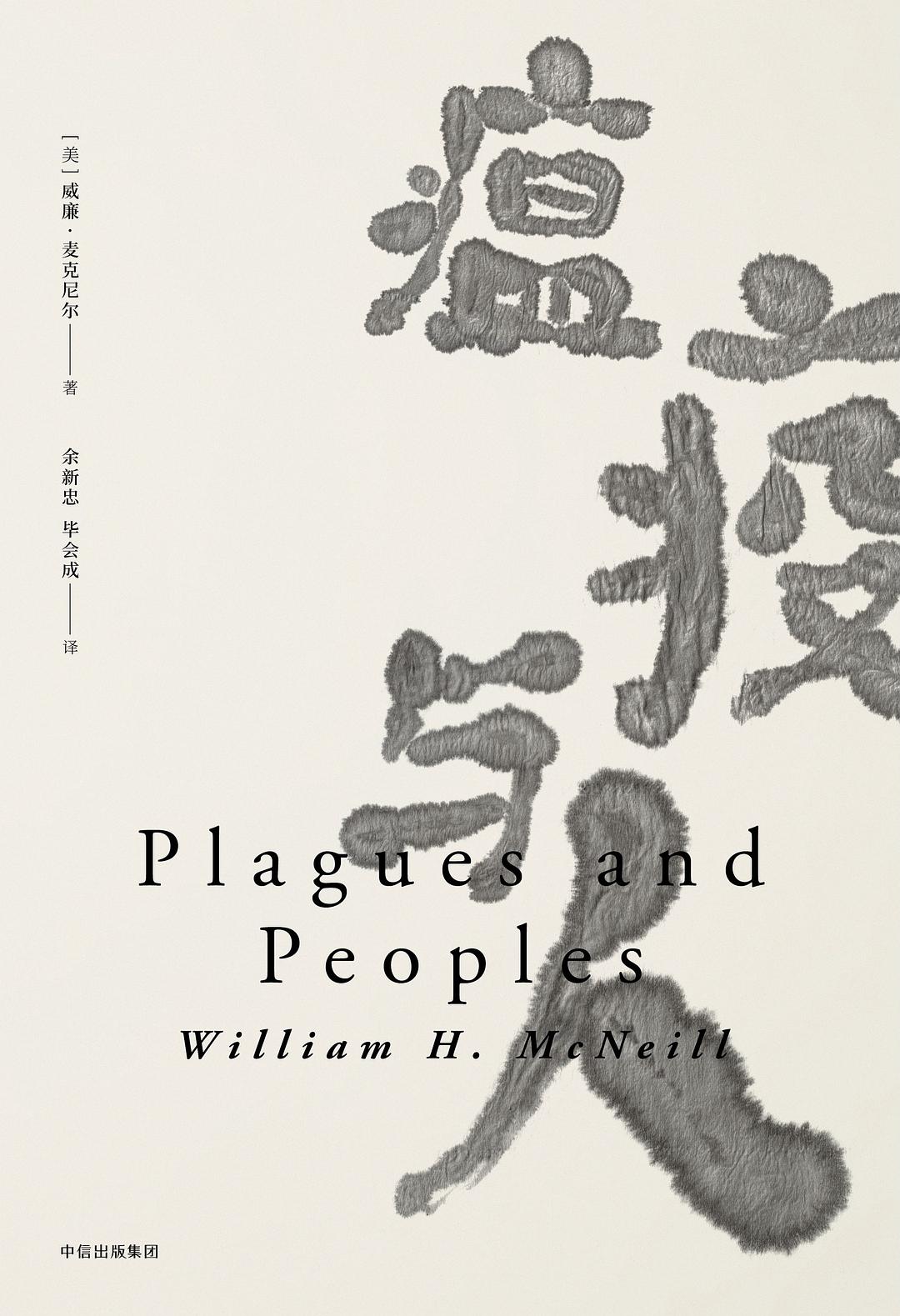
[美] 威廉·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毕会成 译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8-5
审视已知的19—20世纪人类与鼠疫的对抗过程,有必要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汽船航线网是将鼠疫扩散到全球的便利渠道。事实上,一旦鼠疫出现于广州和香港,其传播的速度就只受限于轮船把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带到新港口的速度。传染链如果能从一个港口延伸到另一港口而不被切断,速度显然是关键。既然鼠疫杆菌会使幸存者产生免疫力,它在船上的老鼠、跳蚤和人类宿主中的存活就很难坚持数周以上。在航海时间太长、大洋太宽的过去,鼠疫杆菌无法在船上长期存活,更谈不上登陆美洲和南非的港口,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处了。但是,当汽船更大、更快,或许还携带了更多的老鼠,便将传染链拉得更长,跨越大洋顿时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了。
其二,船上感染的老鼠及其跳蚤,不仅把鼠疫传染给港口上的人,还传染给它们在半干旱地区的野生远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阿根廷和南非,野生状态的鼠疫潜在宿主种群已经存在了无数代。要产生新的疫源地,所需的只是杆菌赖以跨越地理障碍(此处指海洋),蔓延至已有适量穴居啮齿动物的新地区的途径。穴居的啮齿动物,尽管在种类和习性上存在很大地域性差别,但它们既易于感染又能维持传染链永不中断。自从医务工作者开始观察到这类现象,重要疫病就未再发生地理上的意外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类似的突变没有发生过。相反,19—20世纪的鼠疫史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范例和模式,一旦阻碍鼠疫杆菌扩散的既有障碍被突破,它就会极其迅速地占据新的领地。实际上,无论变化看起来多么突然,鼠疫的最新胜利也依然是一种正常的生态现象。因为某个生态龛一旦空出,通常很快就会被某种人类或非人类的有机体占领,并据以繁衍生息。
其三,在中国云南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当地人当中同样存在的古老习俗,似乎相当有效地阻止了鼠疫对人类的感染。尽管这些地区的啮齿动物洞穴中始终存在着鼠疫杆菌,但只有当新来者不再遵守当地的“ 迷信”做法时,鼠疫才成为人类的问题;而且对传染病一无所知的外来者对当地的侵扰,还经常伴随着军事—政治动荡,这类动荡在过去也经常引发疫病灾难。
从云南和东北的民间习俗在鼠疫防范的有效性上,我们可以看出,1894—1924年成功发展起来的医学预防措施,不过是人类应对疫病危机的正常反应,只是更为迅速和科学有效而已。在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容许神话和习俗通过试错法,来确定一套可接受的人类行为方式,把疫病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但科学的医学不再如此,而是就新的行为规则达成共识,并动用“国际检疫规则”这一全球性的政治框架,来强制推行新规则。就这一角度而言,20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辉煌成就,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富有创意;尽管这个世纪应对鼠疫的医学措施的有效性,远远超过了以前限制疫病肆虐的那些方式。事实上,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可以事先制止这些流行病,而这些流行病本来可能抑制甚至扭转人口大量增长的趋势。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瘟疫与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略有删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