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诺尔(Henry Noll)是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工人之一,但出名一事既非他自己的选择,用的也不是他的本名。诺尔在伯利恒钢厂(Bethleham Steel)工作,日薪1.15美元,在工友中以精力充沛、生活俭朴闻名,与某种“高大全”的故事情节类似,他于1899年被年轻有为的管理顾问弗里德里希·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相中,参加了一项实验。某天上班时间,泰勒来到诺尔身旁——后者之后以“施密特”这一化名而闻名——并询问他,“你是个高价值的人吗?”这个故事见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一书,面对这个显然有诱导性的问题,“施密特”谨慎地答道:“唔,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你肯定清楚,”泰勒坚称,“我想了解你究竟是不是一个高价值的人。”
“唔,”施密特重复了一遍,“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嗨,快回答我的问题,”泰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希望了解你究竟是一个高价值的人,还是跟那些廉价的同事没什么两样。我希望了解你究竟是希望每天能挣1.85美元,还是满足于目前的1.15美元,也就是和那些廉价的同事持平。”
施密特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显然他愿意接受那额外的70美分(“我是一个高价值的人”)。接下来,麻烦来了:“看到那堆生铁了吗?”泰勒解释称,一个高价值的人要能令行禁止,“从早到晚。”施密特——泰勒不太恰当地将其比作“聪明的大猩猩”——的工作将有精确的计时,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最优,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叫他干活他就干,叫他休息他就休息。”以此方式,泰勒极大地提升了施密特的产能,其每天处理的生铁量从12吨升至47吨。
这就是“科学管理”的发端场景,它迅速在全世界的工作场所普及。施密特和泰勒之间的讨价还价模式,明白无误地预示着一项定义了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折中方案:提高你的产出,赚更多的钱;生产力越强,工资也就越高。

现实是这个模式持续不下去了。近几十年来,默契发生了动摇,对工人产出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工资条却并不与这种高预期同步,近来的诸多讨论与争议正聚焦于此。工会的衰落、不平等的加剧、自由民主的危机以及美国文化的变迁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一转型相关。我们拼命工作也只能勉强度日,而财富的总数却膨胀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量级。你要叠放更多的生铁,但不要幻想自己有什么高价值。艾米丽·君德斯贝格(Emily Guendelsberger)与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的新书就此发问:这种公然羞辱人的做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出所料,君德斯贝格观察到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疯狂。”
君德斯贝格在其新书《上班时间:低薪工作对我的影响及其如何逼疯美国》(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里重演了一遍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里做过的著名实验。君德斯贝格曾在非传统周报《费城报》当记者,直到2015年这家报纸出清并转卖,其间她暗访过三处低薪工作场所:印第安纳州的亚马逊货仓、北卡罗来纳州的某处话务中心及旧金山的一家麦当劳。艾伦赖克的主要发现是,一个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仍旧存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的争议点——而君德斯贝格则将不平等和剥削视为既定的,转而追问这些工作对千百万工作者的具体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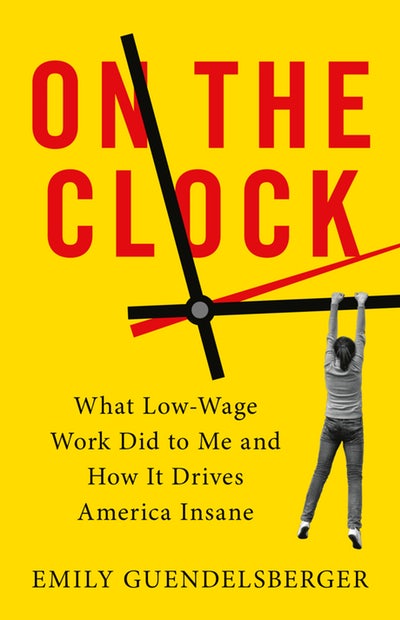
“一团乱麻”(in the weeds)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职业-管理阶层中,“一团乱麻”指棘手的琐事(参见VOX的公共政策播客《芜杂》)。君德斯贝格指出,工人阶级眼里的“一团乱麻”相当于专业人士话语里的“应接不暇”(swamped):被淹没且不堪重负。她进一步提出,美国工人阶级每时每刻都面对着“一团乱麻”,日渐受制于一种自动化的新泰勒主义(automated neo-Taylorism)。工人的作息由算法来规划,其任务的计时实现了全自动化,并有数位化的绩效监控机制。君德斯贝格对此类工作的体会是:“这团乱麻对人类极其有害。它已经把我们逼疯了。它让我们整个人都不好了。它摧毁了家庭生活。它把人们推向毒品。它真的会取人性命。”
君德斯贝格在实验中发现,如今的雇主“要的是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言说、感受和捡起东西的劳动力——如同机器人一般除了工作之外别无所求。他们坚称工人应摒弃各种凡夫俗子的杂念——家人朋友、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结果就是一系列“半人半机器的工作”,据君德斯贝格的估计,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将近一半。老板们筛查并封杀了一切令工作尚可忍受的忙里偷闲机会:以往把机器调慢的把戏不再管用,或者不再有那23分钟的老板一定看不见你的时间。其间残存的每一丝人性都被摧毁得干干净净。
君德斯贝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马逊的“物流中心”,她发现其中的体制堪称“泰勒理念的完美化身”(一名同事察觉到了泰勒的影子,称亚马逊“是一项社会实验,考察一家企业究竟能把人压榨到什么程度”)。身为“分拣工”的君德斯贝格手腕上佩戴着扫描枪,这件设备可以监控她的方位,在堆积如山的库房里为她准确定位货架上的某件物品及计算出处理该物品所需的时间。身旁的读秒器令她有了一种负罪感。等到她在庞大的仓库里最终找到货架,在货柜里翻检并扫描完毕后,下一件东西又就位了。
虽然亚马逊的货仓——一般设在经济萧条破败的城市——开的工资通常比周边都要高,它的日程表仍然逼死人。工作内容极为单调乏味(为了解闷,君德斯贝格违反了公司的纪律,在帽子里藏了耳机听歌)。到了休息时间,抵达货仓出口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她几乎刚走出门就要转身回到岗位上了。心理压力大,身体也痛苦不堪。她观察到,公司的休假政策还不如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提供的好。亚马逊为工人提供免费的止痛药,君德斯贝格没过多久就忘记了自己究竟用过多少药。有一次,当她蹲下身子准备从货架低处取东西时,身体突然“不听使唤了”。她写道,“我每天要向大腿下几百次命令,好让它站起来,但它似乎已经受够了各种折磨,开始和大脑较劲了。大脑气急败坏地三令五申,而我慢慢地瘫软成了坐姿。”另一名工人则抱怨称,“我的脚就像踩在水果馅里一样。以前我可以负重徒步20英里不换袜子,现在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别的工作也没什么两样。在Convergys公司的话务中心,君德斯贝格发现自己不过是失望的顾客和店大欺客的公司之间的人肉盾牌(事实证明,如果你不够小心的话,还会在工作地点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份工作对职员的要求,是在互动中向来电者推销商品,尽管来电的客户一般而言只想花大约相当于有线电视费的钱就把问题解决。致电者人数众多,工人已经不胜其烦,但还得处理电脑系统失灵和不兼容等问题,同时要富有同情心,要趁机“带货(upselling)”。君德斯贝格开始想象自己具有多重人格:一个要同时处理助手、销售、礼宾、速记、沟通、短时记忆、善解人意、记者和老板——要能掌控全局——等多项任务的艾米丽。“她的工作混账不堪。”她最坏的一次呼入来自同事,后者只能在午饭时间抓住难得的机会来反映一些服务上的问题。
如果员工在两次呼叫之间关掉了系统,便会遭到监视、规训和责备,理由是偷取时间。涉猎广泛、兼容并蓄是君德斯贝格的一大优点,书里的亚马逊章节就为读者介绍了泰勒,让读者对边沁的全景敞视塔(Panopticon)有了概念,顺带还提到一些进化心理学。假如你知道上级可能会随时盯着你,或者某些不在你控制范围内的因素会让客户发火,那你将会如何应对?你整天都会是一种高度紧张、一触即发的状态。你的身体和大脑并不适应这样的状态。压力反应原则上是短时性的,“战斗抑或逃跑”的模式不可持续。每天都做这样的工作差不多等于在毒气室里做深呼吸(君德斯贝格就此讲了一个有关栖息于后院、繁殖迅速的类人生物“旺达”的寓言故事,它会毫无原因地工作)。
最后一份在麦当劳的工作并没有带来深刻印象——无非是因为它太稀松平常。做快餐的艰苦不难想象,更别提薪酬非常微薄。“流水线总是存在的,”君德斯贝格写道,“我们总是要面对一团乱麻。”在话务中心,她需要直接和客户打交道,并设法将其需求融入自己多少有些模式化的工作流程,为此她必须马不停蹄。有一次她在倒咖啡时不慎被咖啡壶割伤——无论如何不能让咖啡洒出来——把手断掉了,壶砸到了她身上。由于裤子不方便换,她只得忍受滚烫的咖啡,为保证温度,麦当劳会把咖啡烧到接近于沸腾的水平。“我经常有种感觉,我们的人员配备俨然是有意缺斤少两的,正好处在一个让买家卖家都吃最大亏的程度。”
如果说,麦当劳在要和众多的人打交道这件事上和Convergys相同,其不同点则在于不讲道理的顾客现在是面对面的、是能见到真人的。他们会找她的麻烦。有个耐心很差、派头十足的客人(“快快快”)要求她额外添加蜂蜜芥末酱,而原则上她是不能这么做的(“蜂蜜芥末酱!快给我蜂蜜芥末酱!”)。为避免冲突,君德斯贝格只得违规给客人加量。然而她在愤怒面前不太镇定,一包酱料脱手滑到了柜台上。“客人就跟棒球赛里的游击手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捡起酱料包,重重地扔到了我的身上。酱料包破掉了,我被溅了一身,周围也受到波及。”这名客人和朋友串通一气,一口咬定是君德斯贝格先动手扔了酱料包。随后自然就是各种责怪受害者。这是在2010年代。
从君德斯贝格的角度看,美国的工人阶级受累于压力和恐惧,腿脚不堪重负,也都被泼了一身蜂蜜芥末酱。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利已经足够恶劣,但君德斯贝格还发现了某种更深刻、更糟糕的东西:“日常的高压让人们失去了同情、耐心以及对新事物的宽容。”我们被粗暴地对待、欺侮、被忽悠进而被训练成工作动物却换不来相应的薪酬涨幅。难怪我们的社会四分五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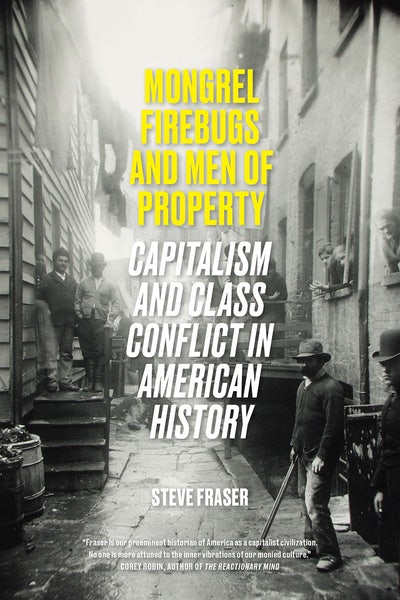
史蒂夫·弗雷泽在其新出的论文集《纵火的杂种与有钱人:美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Mongrel Firebugs and Men of Property: Capitalism and Class Conflictin American History)中称此状况为“莫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祭祀仪式里有将儿童活活烧死的环节——译注)。他引用弥尔顿和金斯伯格表示,“资本主义的莫洛克神的致命与无情与其在迦南人先祖那里并无二致。但其祭坛如今无处不在,表面上不可见但却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享有华尔街的祈祷,另一方面规定了每个人情感生活里最隐秘的欲望和不安。”这些祈求、欲望和不安——及其历史与暗流涌动——构成了书中11篇论文的主旨,几乎对美国历史来了一次总览。作为一名有胆略的记者,君德斯贝格与问题近距离接触,而以高产闻名的历史学家弗雷泽则着眼于勾勒事物的整体面貌。他的风格接近于老派的美国研究,对原初神话和某种类似于国民心理的东西更感兴趣。
论文集基于并提炼自弗雷泽的两本新书《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和《默认时代》(The Age of Acquiescence),以后者为重,而该书也是其封笔巨作。虽然新书的内容大致面向最近十年来的杂志读者,且谈论问题的笔法也不算艰深,但它们仍表现出了弗雷泽对美国历史的百科全书式把握,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弗雷泽早年对二十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原创性研究在当时是一项突破,如《劳工说了算》(Labor Will Rule)对制衣厂工人领袖西德尼·希尔曼的生平有精到的考察,1989年的论文选集《新政秩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仍具有启发意义。
在最近的著作——尤其是前文提到的论文集里,弗雷泽追踪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轨迹。19世纪是资本疯狂扩张的时代,所到之处不惜一切代价。“它无情地推进着,”他写道,“占有着原本因各类奴隶制、短视以及止步于基本生存而难以染指的土地以及人力和自然资源。”面对这一社会灾难,人们发起了积极的抵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以持久而暴烈的社会冲突为标志,弗雷泽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组织化的流离失所者形成了美国第一批无产阶级。其登场兼具许诺与责备的意涵。”弗雷泽写道。
这一时代也是大罢工和总罢工的时代,运动超越了具体劳资关系的藩篱,呼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全国大游行即是一例。
本文开头提到的亨利·诺尔就很可能是部分运动的亲历者:伯利恒钢厂在1910、1918和1919年三度发生声势浩大的罢工。
斗争时代结束于新政。例如,伯利恒钢厂的工人在1937年与1941年又发起过两次罢工——全美范围内也有大量类似的运动。他们最终赢得了承认,并很快地融入了美国的主流。偏于保守的妥协起初有助于新秩序的稳定,后来则以制度化的形式确认了种族与性别的等级制、迫使工人不再激进以及令不完整的福利国家受制于私人领域——此外也遗留下了一堆矛盾,致使其最终于1970年代退化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弗雷泽的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在此也就凸显了出来:考察我们时代的心理经济(psychic economy,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机制也具有经济学色彩,倾向于节约能量耗损——译注)。弗雷泽提出,以往“镀金时代”里的不平等遭逢了如潮的抗议,如今的我们则生活在一种漫不经心的、去道德化的顺从文化里。经济上的冒险倾向在大萧条后一度被打入冷宫,如今又受到英雄般的对待:敢于冒险的人终将赢得一切(可在谷歌上搜一下risk-taker这个词,切勿对结果大惊小怪)。事实上的债务奴役和惩罚性劳动也沉渣泛起,不过眼下这两者都没有引发愤慨,与基于以往历史经验的推测背道而驰。在1890年代,田纳西州的煤矿工人曾武装营救被捕劳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失业在十九世纪晚期被视为荒唐事以及不可接受的社会现象,人们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抵制,如今它们已经是自然的了——循环往复,如同四季更替。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豪车自由派”的怒火构成了反抗运动中的最强音。在论文集的后半部分,弗雷泽考察了这一美国民粹主义的传统,发现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恰好可称为特朗普的前身。但他也提到,一个世纪以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好歹还需要一个亲近劳工的姿态。“如今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很少像赫斯特那样公然鼓动人们与资本主义对立。相反,特朗普的吸引力来自于他是一个爬到了资本主义顶端的超人。”此现象反映的无非是家族资本家的兴起——如科赫家族和沃顿家族等——近年来他们不仅聚敛了海量的财富,而且还像自由派和反动主义者一样,表现出了“按自己的形象来打造世界的强烈欲望”。其收获的尊崇在特朗普入主白宫时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他们的神化已经大功告成——“基尼系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弗雷泽说。
在弗雷泽看来,这一深刻的意识形态变迁源自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机制”的更动。以往它吞噬可供吞噬的一切,同时引发了暴动,如今其体系基本上是驱逐性的:以失业与排斥为主,而非强制的同化和雇佣。“进步时代的齿轮以及第一个镀金时代的造物巨匠如今完全颠倒了,”弗雷泽写道,资本主义“自己吃掉了自己”,新时代的精神相应地体现为社会抗议遭到冷遇,而非对横征暴敛的愤怒。
事实上,弗雷泽于无意间已经表露出了自己的悲观心态。“莫洛克的精神遍及全世界,”他总结道,“令人不寒而栗地照亮了由特朗普开启的地狱深渊。”虽然他在全书结尾呼吁人们要重拾解放的梦想,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此类梦想从何而来,对梦想的最终实现也不抱多少信心。在此,弗雷泽与君德斯贝格恰好分别代表灰心丧气的新左一代与桀骜不驯的千禧一代,二者之间的鸿沟愈发扩大了。
代际差异既有政治性,也有社会学意义。不同于前辈艾伦瑞克,君德斯贝格并没有特意去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她原本就没有多少下滑的空间。《我在底层的生活》虽然知名,但艾伦瑞克深受她与同事之间的社会距离的困扰。君德斯贝格则没有这方面的麻烦,她在实行暗访计划前已经是失业状态。在故事里的绝大多数时段,她都睡在自己的车里,并心怀感谢地接受着工友的资助。事实上,她仅仅怀着出版的希望就开始了书的写作——合同是她在Convergys公司做第二份工作期间才签的。“我当时,哪怕最终没有结果,其间起码还能攒个几千元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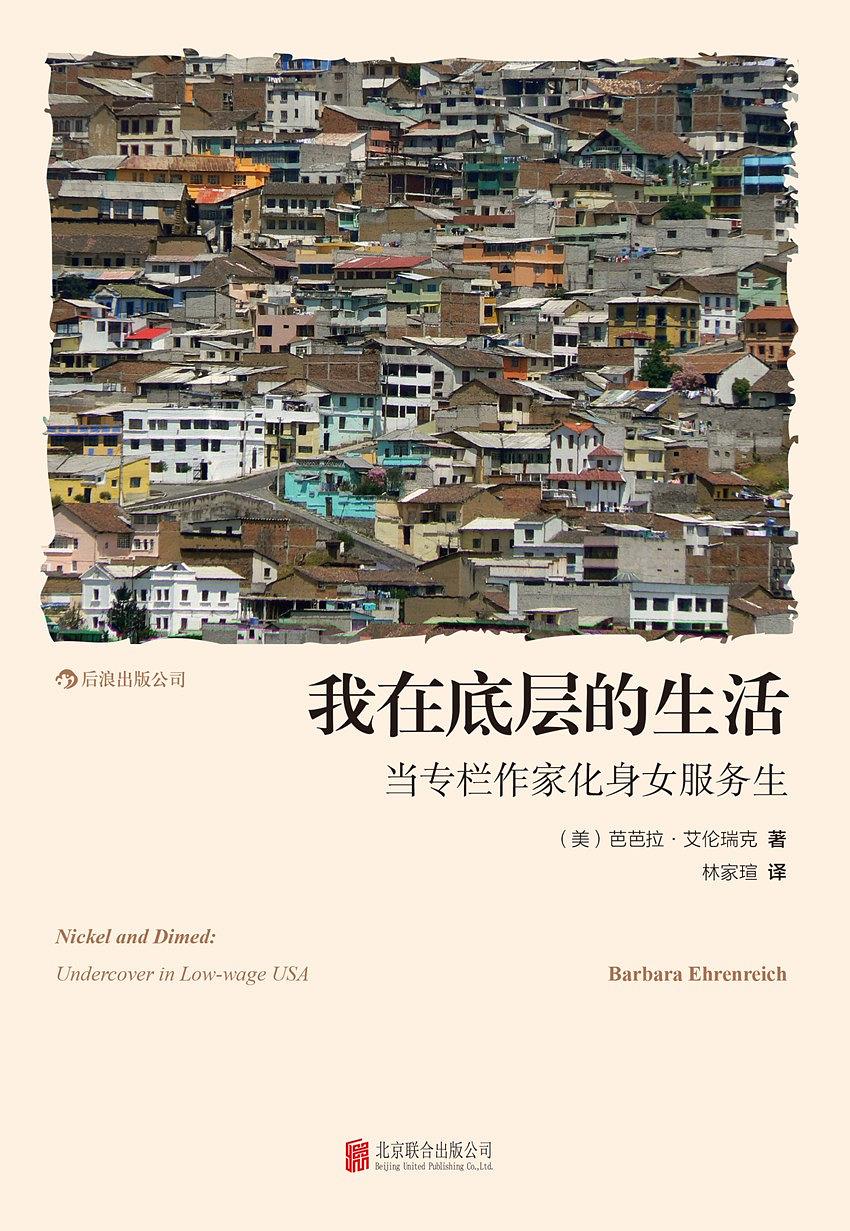
[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林家瑄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4-8
《我在底层的生活》的诞生与此有鲜明对比——该书源自艾伦瑞克与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美国文化名人,哈珀氏杂志主编——译注)一同吃三文鱼大餐时的头脑风暴——这一对比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一度享有铁饭碗的专业阶层在过去二十年里的起落沉浮。艾伦瑞克对踌躇满志的中产这一身份有自我意识,设法重新发现工人阶级的失地,借此向业已麻木的都市中产青年喊话,敦促其觉醒。对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第二代人来说,中产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理解工人的任务不再是当务之急了。君德斯贝格自己就在两个阶层之间游移不定,她推想自己的读者应该也一样。“是的,就是你,这位女士(mamá,西方青年人中的新俚语,意义类似于以前的姐妹、闺蜜之类亲昵称呼——译注),”她在后记里这样写道,以麦当劳员工之间的打交道方式赞扬读者,“你也是个工人……就跟我和杰斯、泽布、坎迪拉、科比、米格尔以及芥末女士一样。”
确切地讲,君德斯贝格的工作地点充斥着弗雷泽所谓的有害意识形态。Convergys公司的职员随时受到监控,以防其“偷取时间”,而雇主却把工人们的时间偷了个一干二净。“亚马逊人”被反复告知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很多人似乎还信了这一套。爱抱怨的同事通常会被打成不懂感恩之徒。“觉得亚马逊不好就去麦当劳呗,你个麦婊,”某条网上评论如此呛道。货仓里的同事布莱尔既对循规蹈矩颇有微词,又想要打破最快分拣工的世界纪录——她希望以这种方式证明人类总是能战胜机器人。如君德斯贝格所观察到的,布莱尔与约翰·亨利(John Henry)是同一类人,这位传说中的大力士试图用锤子和新发明的蒸汽钻头较劲——他确实赢了,累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锤子。
铺铁轨的男人(The Steel-Driving Man)——现实中很可能是个身型瘦小的黑人囚犯劳工——在大萧条之际被人谱成了同名歌曲,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民歌之一。全国的劳工都在和机器赛跑,郑重宣布“我将与锤子同生共死”。约翰·亨利固然受到机器的威胁并最终死于机器,但他仍然胜利了,成为了工人们奋起反抗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符号。历史学家斯科特·雷诺·尼尔森(Scott Reynolds Nelson)在其大作《铺铁轨的男人》(Steel Drivin’ Man)中指出,亨利的传奇经历与无产阶级的兴起形成了共鸣,二者的突出共性便是对新秩序的普遍敌意。
另一方面,你或许能不无底气地打赌说,专车司机、兼职讲师和保姆的工作辛劳,是无法靠把布莱尔与算法赛跑的故事谱成歌曲来打发掉的。布莱尔做的事和约翰·亨利相同,但其行为的意义却发生了颠倒:凸显的是雇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其的拒斥。她是弗雷泽论述的一个典型实例。
鉴于君德斯贝格自己就是个朝不保夕的“新闻民工”,她要发现以及融入暗中涌动于几乎所有工作场所的团结趋势并不难。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总是社会性的。经由泰勒及其后人的一再细分,资本主义的生产愈发需要人们协同工作。无论管理层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工人彼此了解和信任,都无法真正消除此趋势,哪怕这种了解和信任的程度有限。“在反对秒表和大鲨鱼这一点上,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君德斯贝格写道(她在某处扩展性地运用了鲨鱼的隐喻),“我们或许都是凡人,但我们人多势众。”打破弗雷泽笔下的意识形态牢笼的,正是劳动的社会维度。君德斯贝格在书的结束处提出了一项预测:“你将会遇到认为现状残酷而荒谬的人——这种人可以说无处不在……你能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一种比友谊更牢固的纽带。你将会成为某种比自己的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很古怪的一点是,你会因此而感到,与之前相比,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强的控制力。”
君德斯贝格是在初冬去到亚马逊工作的。她写到了假日季的压力,称其为一场可怕的加速、一种白日里的梦魇:她无法控制劳累不堪的身体,无聊、压力和抑郁一股脑地涌来。但事实证明上述这一切并非体验忙碌季的唯一途径。在圣诞节前的一周,她去了一处帐篷村,那里住着一群临时工。大家一同享用迷你披萨,她还带了一些啤酒和曲奇赴会。那里的人们认为君德斯贝格步入了误区——她工作得太拼了。只有当你想要升职但却长期原地踏步的时候才需要提高绩效。一个叫马蒂亚斯(Matthias)的人说,“他们对我们的需要大于他们付给我们的薪酬。”经过尝试,他最近发现最多可以在午饭前省出48分钟的时间来休息,在这之后管理人员才会来与他交谈。“‘整个机构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但这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马蒂亚斯说,“诉诸一套糖衣炮弹式的洗脑话术,‘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打破一切预期!’”
一群暂住的临时工长期休整,围坐在篝火旁嘲讽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都谈不上是革命,但也不是毫无意义。君德斯贝格表示,类似的现象必然是无处不在的。对你自己而言,要明白提高绩效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考虑有人扔了你一身芥末酱还反咬一口该怎么办,都是很困难的。这种压力能轻易把人压垮:莫洛克神不仅强有力,而且令人毛骨悚然。但假神之为假神,就在于它经不起嘲讽,总有一些人能看透本质——其实天天都会有这种事。雇主或许拥有能监视一切的全景敞视装置,但工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也会为每一场罢工埋下伏笔。
本文作者Gabriel Winant是一位历史学家,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有关照料工作和去工业化的著作。
(翻译:林达)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