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你在玩一个游戏。你获得了10美元,你可以将这笔钱与另一位匿名者分享,或自己留着。你会怎么做?“理性自利”(rational self-interest)的经济标准建议,你应该把钱自己留着,毕竟,你并不认识另一个人,他们也不认识你——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是你拿了这笔钱。然而,你却可能考虑过分享这笔钱,可能分出去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如果你的确考虑过,那么你的行为就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所做的大量研究结果一致,那些研究表明,大多数人有着“可预见的非理性”特征。
但尽管调研结果如此,主流政客仍在根据“理性自利”的原则去传递信息。他们会强调,一项政策将如何使选民个人受益,其对公共利益的好处却轻描淡写。就在最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治领导人主张一项碳税政策,他们强调公民将因所得税降低和碳税收入返现而在经济上受益:碳税政策符合你的个人利益,为它投票吧!
为什么政客和营销人员在推广政策或产品时,总是假定人们关注“理性自利”?一种可能是,公众可能比科学实验中所呈现的更具理性。不过,他们也可能因支持另一种规范性判断标准而减损理性利益,即支持“合理性”(reasonableness,常理)。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探索了这种可能性。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游戏,也称作“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作为负责这笔钱的人,你可以扮演一个自利的独裁者,将钱独享。但人们通常会与另一名游戏参与者分享这笔钱,否则“独裁者”就认为不公平。他们以一种“合理的”社会规范而不是“理性自利”原则去指导自己。表面上,“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在拉丁文中,“比率”(ratio)即指“论证 /理性”(reason)。然而,对于道德哲学家而言,该两种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理性”脱离环境地专注于个体,即追求个人目标的实现;而“合理性”涉及个人目标与公平之间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平衡。
外行人也区分这些学术性的标准吗?如果他们区分,那么在诸如“独裁者博弈”等情况中,偏离“理性自利”的行为可能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合理性”的偏好。与此同时,在政治中,(单单)诉诸“理性自利”以获得对于城市项目的支持,可能忽视了诉诸公共利益(而不仅是“理性自利”)来启迪公众的机会。
我们邀请人们玩上面描述的“独裁者游戏”,指令他们理性或合理地行动。“做出理性行为”的指令导致了很大程度上自利的选择,这时大多数人决定不分享或只分享很少的钱。相反,“做出合理行为”的指令促进了更公平、具备社会意识的选择,这时大多数人分享了一半的钱。此外,将自己描述为“理性”的人不太会与他人分享,而将自己描述为“通情达理 /合理”的人则更有可能与他人分享一半的钱。

这种理性决策与合理性决策之间的差异在北美和巴基斯坦都存在,在这些地方,我们评估了银行家、街头商人,甚至偏远村庄中居民的行为。它也适用于包括囚徒困境和公地困境(tragedy of the commons)等在内的经济学博弈问题。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预期“理性的人”是自利的,而“合理 /通情达理的人”则能够实用主义地平衡个人利益与对他人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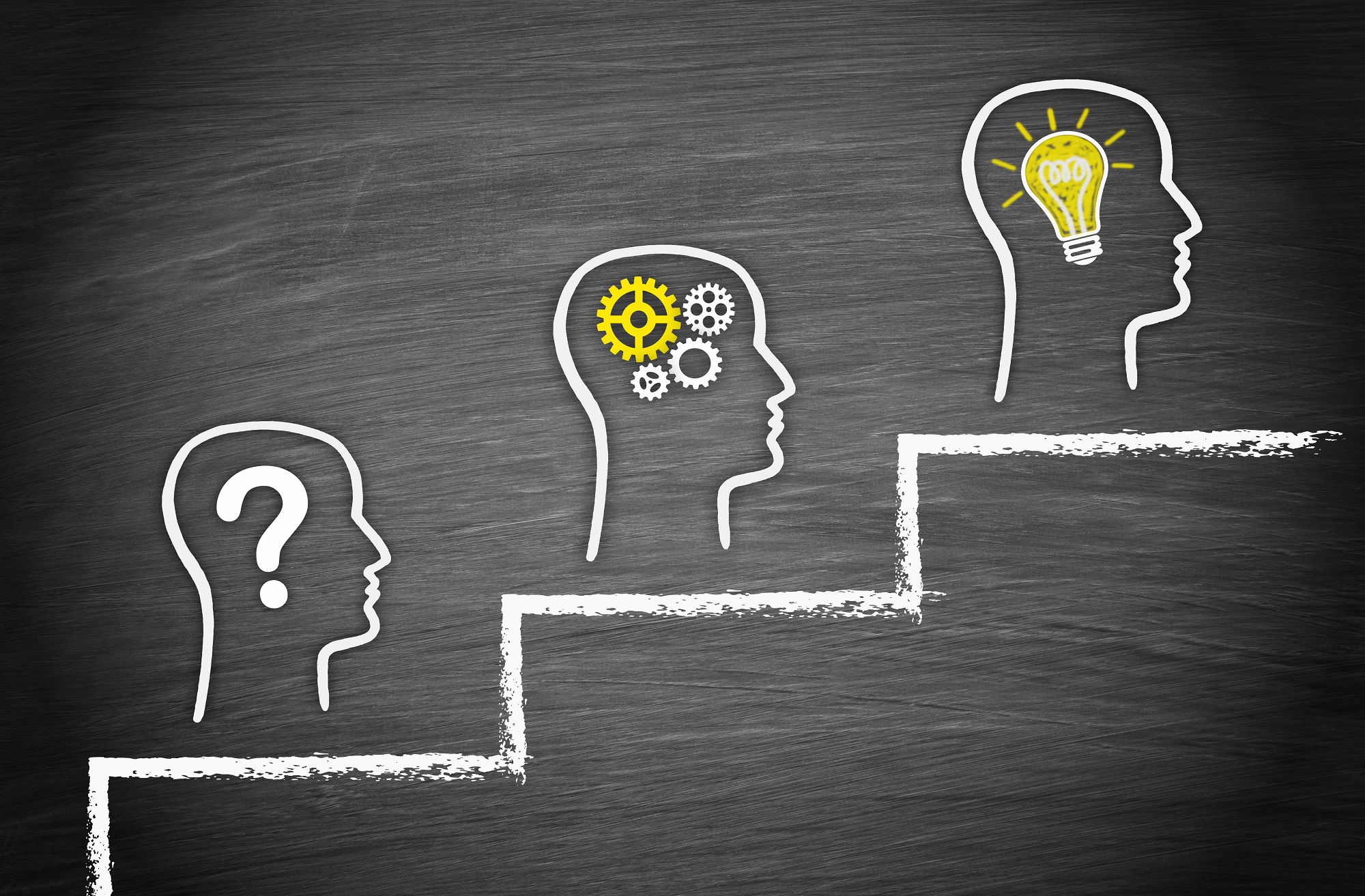
理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差异还扩展到了人们在新闻、电视和书籍中所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涵盖了当今世界口头语言的六分之一。在每种情况下,理性都呈现出了以个人为中心、分析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并与诸如“自我利益”、“主体”和“数字”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相反,合理性则呈现出共有的、务实的、对环境敏感的特征,并与诸如“关爱”、“程度”和“适应性 /和解”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比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更能理解“理性自利”。但尽管了解了怎样才算理性,人们通常更偏好“非理性的合理”行为。换句话说,相比经济学家和主流政客所偏爱的“理性自利”,人们可能会使用另一套不同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大多数人通常视“合理性”为清晰的首选判断标准。这一发现表明,(政客们)有机会基于“合理性”构建更多的政治信息,以丰富公共话语讨论,即通过强调那些政策的公民性、具备社会意识的合理性(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基于“理性自利”的考虑。
例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倡碳税的政客们如果强调,碳税为什么是一种造福后代人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试图说服选民,该税收将有益于他们自己的财政状况),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诉诸公众的合理性意识,还可能有助于为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的社会人群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的工作也给数十年来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信息。我们认为,“人们都无可救药的非理性”的提法是误导性的,并质疑:避免非理性行为的默认方法就是“劝诱”人们做出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吗?我们的研究反倒表明,当“理性自利”违反其偏好的合理化行为标准时,人们可能会选择非理性。
史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等文化批评家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即20世纪后期一场具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破坏了理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场运动主张将经济学家的“理性自利”模型视作可靠判断的唯一标准。而我们的研究反驳了这种指称。“理性自利”的经济学理想状态广为人知,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合理性标准的采纳。
在道德哲学与法律中,理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区别则是深远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它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具有意义。比如,给予现金作为自己配偶的生日礼物是理性的,但是这不合(常)理。让你的父母住在酒店(而不是你家的客房中)可能是理性的,但这也不一定合(常)理。或者,用爱尔兰作家、活跃人士乔治·伯纳德·肖(George Bernard Shaw)的话来说,尽量让世界来适应自己,是理性的,尽管这样做并不合(常)理。
本文作者Igor Grossmann博士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认知科学家,其研究方向为跨文化合理判断与智慧。Richard P. Eibach博士是滑铁卢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专注于研究自我知觉与社会化判断。
(翻译:西楠)
来源:科学美国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