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韩东,男,1960年代生,写作者,题材为诗歌、小说、散文、格言、剧本等等,凡文学类无所不写。也拍摄电影和导演舞台剧。主业或者专业还是诗歌和小说吧。”
在3月7日接受艺术家吴幼明采访时,韩东如此介绍自己。他说自己目前人在湖北,被封闭于某酒店房间内,已经45天没出门了,这一数字比正常的隔离时间14天多出两倍。韩东所在的酒店并不是此次新冠肺炎的指定隔离点,只是刚好将一批住客集中在了一起,因为大部分酒店在疫情爆发后都停止营业了。
韩东告诉界面文化(ID:BookdsAndFun),目前他所在地区的确诊人数已经“清零”多日,但酒店并没有给出何时解禁的声明,他们只能等待。在过去两个月里,无论是患病者、疑似者、接触者,还是其他处于安全状态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隔离。这种经验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或许比疾病本身更为漫长。
身为一个写作成瘾的人,韩东在疫情期间既没有写作的工具,也没有写作的心情。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上频频出现的对作家缺席的指责,以及一系列以描绘和记录疫情为主题的创作。在韩东看来,这些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文学,或者至少不是杰出的文学,它们只是当事人的“及时反应”。站在多远的距离、写什么样的作品以及如何去写,这些都是文学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眼下,我们仍需时间来认识疫情,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应景”而作。

两个“瘾”突然被掐掉:一个是写作,一个是吸烟
我岳母住在湖北,我和夫人这次是来过年的。我们1月21日飞到宜昌,因为岳母家比较小,不太方便,我们就住到当地的一家酒店。后来这家酒店要清空,我们被赶了出来,又在1月25日转移到了另一家条件比较好的酒店。没想到疫情爆发后,其他地方的住客恰好也被陆陆续续集中到这家酒店,于是这里越来越吃紧。最初几天我们还能去岳母家团聚,但到了1月30日左右,就不允许出酒店,也不允许出房间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出去,什么时候能离开湖北也不知道。
关键问题是,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酒店里还住着很多人。我们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微博上看到,通告规定湖北境内各个城市现在还不能开放通行。下面的留言非常多,大家都被憋坏了。我们的情况还算好,是住在酒店里,还有一些人住在亲戚家,另外一些小企业的工人可能真的自身难保。目前舆情很严重,但没有任何办法。酒店只是按照上面的规矩办事,一层层一级级。今天我还去问,能不能出去走一走?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接到上面的指令,到现在电梯还是封着。
住在这里,我们每天测两次体温,上下午各一次,会有人送饭到房间,很有规律,40多天都是如此。早就过了隔离的14天,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测体温。这里已经被定为低风险区,六十几个确诊者全部出院,零死亡,而且已经过去了很多天。我想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考虑到大局,完全听上峰的指令,指令没到,不管舆情怎么样都不能动,另一个就是酒店本身过于谨慎。
我接受吴幼明的采访后,湖北和江苏的文化部门,包括作协、文联,他们都很关心我。后来当地的文旅局局长(或者是宣传部部长)来了,但她来了之后也只能站在门口,大家戴着口罩,把门打开说了几句客气话。她不断问我需要什么?需不需要电脑?有什么困难?还送来水果、蔬菜、牛奶、火锅餐……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这些物资我夫人可以从网上订。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离开,但这确实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就连我们能不能下楼到酒店大堂或者院子里换口气,他们也决定不了。

最开始实行管制的几天,形势很紧张,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私家车也不能通行,所有的商店、企业都关着,就像死城一样。这家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单位,并不是一个隔离点。据我了解,我岳母现在仍然不能出小区,但可以下楼到大院里散步了,可我们还不行,不知道为什么。酒店从来没有宣布过什么情况,我们也问过酒店的住客,没有任何人感染,也没有疑似病例。
我本来心里估计被隔离的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期间对我来讲比较困难的是两个“瘾”突然被掐掉,一个是写作,还有一个是吸烟,这让我非常不适应,但现在也适应了。我想也行,隔离也是一种财富,毕竟这辈子还没坐过牢,坐一次也挺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好身心调节就不错了。每天做操,吃饭,看看手机和电视,但正儿八经的事做不起来。即使有电脑,我也没心情写作,因为写作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前一阵为了消遣,我读了一些何袜皮对案件的分析,读得挺上瘾。另外就是在网上搜一些感兴趣的东西来看。
每天我也会看有关疫情的报道,跟踪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身在其中你会思考、观察和判断,会有很多想法。
至于其他封城、断路等举措,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但不管是哪种观点都很难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件事还在进行。中国虽然好像已经开始收尾,但国际上疫情还在蔓延,最后怎么评定这件事,包括在疫情中各个国家的举措,还是很复杂、很立体的。
恐慌启动了人身上最原始的、恶劣的东西
“身在其中”和“听说”是两种感觉,我就是不知不觉隔离了这么久。吴幼明采访我之后,朋友和媒体都很关心,大家觉得这个事很严重,至少对于我个人是比较严重的。我表弟一开始给我打电话就说:“哥,你遭大罪了。”但我当时想,我真的受了很大的罪吗?当然这很难熬,但还是和外界的想象不同。当我身处其间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明确。
有一点是,我对时间的感觉变了。时间变得很快,每天慌慌张张就过去了。感觉快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新的内容,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所以就一天天重复,“混日子”混得非常快。同时我又觉得时间特别慢,当你把所有东西都忽略,去想象解禁这一天,你就会觉得怎么还不来?在这种参照下,日子过得很慢。这种感觉跟平常生活时不太一样。

我比较典型,就在酒店隔离,但实际上这次不仅是湖北人被隔离,全国人民都被隔离了。有的是和别人一起隔离,有的是自己隔离,有的更惨,比如在车上隔离,因为哪个地方都不收容他。从道义上讲,你当然可以说你是出于自愿——我愿意把自己隔离是为了抗疫。但从心理上讲,没有人是突然自己想隔离,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下。所以全国人民都进行了一场被动的隔离,这种被动的感觉会很强烈——突然有一个不由分说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必须这样做。
我是和我妻子在一起隔离,这会考验夫妻关系。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时刻相处,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就会很可怕,好在我们关系很融洽。不是有很多地方解禁以后,离婚率突然上涨了吗?佛教里讲“怨憎会”,就是说两个人本身性格冲突或者关系不好,但由于某件事必须待在一起。“怨憎会”是八苦中的一苦,如果是这样,可能一个人更好,一个人不过就是孤独感的问题。我们也听到住在旁边的邻居吵架,有时吵得很激烈,好像后来他们又要了一间房。所以隔离会给人的心理造成很多影响——被动的,还有和什么人隔离在一起——这些都是问题。

滞留在外地的湖北人更惨,因为在前期,湖北人到哪里大家都很恐惧。湖北人到一个地方,即便被接纳到最大的酒店,被隔离起来,但只要说你是湖北的,大家都退避三舍。湖北牌照的车在街上一走,大家都像看见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理解(歧视的问题),因为在紧急关头,人启动的是求生本能。在恐惧的萦绕下,人们自保的、自私的本能都出来了。所以湖北各地的人都怕武汉人,全国人民都怕湖北人,全世界人民都怕中国人。之前由于新冠肺炎,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人遭到国际上非理性待遇的报道。我想首先要理解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不去用理性引导,不用文明的、长时间灌输的道德意识去克服,那么危机关头人的本能反应就会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恐慌,因为恐慌是很有传染性的。这次疾病在武汉爆发,一方面是新的病毒我们没有接触过,另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和言论管制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将疫情控制好。突然的封城断路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恐慌,而恐慌启动了人身上最原始的、恶劣的东西,我认为这与此次事件的措手不及和处置方式有很大关系。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种极大的恐慌和“防卫过当”,可能也无法彻底消除疫情,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难说。
在大灾大难面前,文学太小了
疫情发生后,有人指责文学的缺席,其实杰出的文学从来在社会巨变和自然灾害面前就是缺席的。像《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种配合时代的作品非常少,而且它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有限。要求文学去反映社会上的变化,让二者嵌合在一起,这种思路违背了文学的本质。
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文学素材。作家的经历,他的感同身受,可能是写作好文学的一个条件,但是必须离开这个时空。“现学现卖”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可能造就文学的奇观,因为文学的奇观不可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出现。这种及时反应——无论是作为个人、公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要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去对这件事进行高屋建瓴的发言,我觉得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像方方或小引的日记,我觉得很好,很及时,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文学作品。也许他们在遣词造句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看的东西比别人多一点,但是最真实的部分还是他们作为当事人的第一反应,这是可贵的,也是必要的。你可以说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缺席,因为他的发言——不管是科学家、社会名流、政界名流,还是企业名流——会让这件事往不良的方向发展。但你说文学家艺术家不发言是他们的过失,这就是胡扯了。
另外,还有人去写应景的东西,那就更不用谈,我们谁都知道那是垃圾。这些人的心理大家也知道,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只是想借机混一下。还有一部分人身为写作者,没有在大事面前写出东西来,因而感到内疚,我觉得没必要。你有写的自由,也有不写的自由,这是顺其自然的一件事。在大灾大难面前,文学太小了。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说法好像在谴责写诗没有力量。但不是的,只是那个时间太近。文学的声音在一个频道内才会出现,它不是一个无限宽阔的频率。我觉得讨论在什么距离内、写什么样的东西、怎么写,才谈得上艺术性的处理、文学化的处理,这也是文学艺术和现实之间恰当的关系。所以在现有阶段,我们要认识这次事件,各种资讯对认清这场灾难有更切实的帮助,但文学不是用来干这件事的,它不是应景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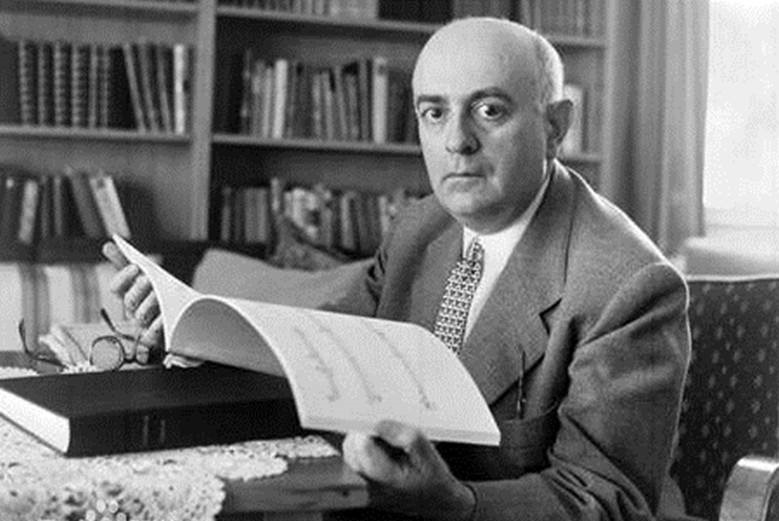
文学的作用不是对灾难的认识,而是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它不是对具体环境的认识——比如地震时,我们就要看地震题材的书,那太直接了——它关注的是人在极端处境下的人性,这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灾难可以引发写作的欲望,但即使写了,也落不到文学身上。你有真实的感受,引起了创作冲动,没有问题,可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思考、描述,甚至是记录灾难,你指望它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我觉得这是冲突的。比如最近出现的“疫情诗”,它的动机是真实的,但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评判,这样的东西十有八九不成立。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诗是一个酿造的过程,需要提取、锤炼、修改,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出来的。
我一直主张短诗,不喜欢看长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写史诗,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我有一个解答:史诗至少是一个个人的纪念碑。譬如庞德的《诗章》、艾略特的《荒原》,我们经常听说这些大诗人的大作品,但恰恰是这些大作品无人问津,除了专家和研究者。大作品对于诗人的文学地位有帮助,就像一篇学术论文虽然没人看,但必须发表到顶级刊物上一样,它是一个指标,一个说明,在诗歌圈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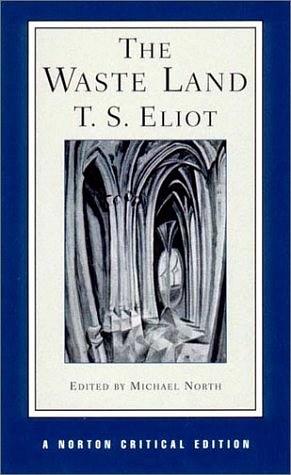
我对诗的个人认识是“少即是多”。与其他文体相比,诗的不同就在于它能量的级别不同。寥寥数行之内,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在这样一个少即是多的艺术里,追求多和庞大没什么意义,因为史诗的功能如今已经被替代了。在最原始的时代,类似《荷马史诗》那种诗,我认为实际上是韵文。在文字比较缺乏的时代,它作为口口相传的一段历史,有韵脚,便于朗诵和流传,所以才有创作的需要。
有人曾说,小说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史诗。有了散文和小说的叙事之后,史诗已经没有必要了。到今天更多影像的东西出现后,小说也走到了尾声。极端一点说,电视剧就是这个时代的史诗。所以我认为诗歌承担“大块头”的史诗的功能是历史的遗韵,也是诗人的纪念碑,对个人的意义比较大。诗人追求“纪念碑”——塑造对自己有意义、对文学史有意义、对专家有意义的东西——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但在我看来,诗人也罢,小说家也罢,唯一的任务就是写杰作,不在乎长短和规模。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