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出版的《鼠疫》中,和今天横扫世界的新冠病毒有所不同,加缪并没有将这个想象出来的瘟疫放到全球视野下。彼时,加缪刚刚从第三帝国笼罩天下的阴云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猛攻下走出来。小说中,灾难降临在了奥兰城,一个“草木不生,没有半点灵魂”的港口城市,“群山环绕,闪着光亮,”这就是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
然而,这本书在今天看来仍然分量十足。加缪没有在救护车和奥兰城感染人数上花太多的笔墨,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个个市民身上。他们同今天的我们一样,都不得不重整生活的秩序,再度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和我们一样,瘟疫对当时奥兰城的人们来说也是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纵观历史,瘟疫就和战争一样频繁,但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看来,尽管如此,每一次疫病的爆发,都能将人们打一个措手不及。然而令人震惊的还不只是疾病本身,小说看似波澜不惊的开篇,以及其中暗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之兆也同样为后文的发展埋下了炸弹。
小说主人公贝尔纳·里厄是一位年轻医生,有着一双黑色的眼睛,眼神坚毅。四月的一个早晨,里厄医生日常出诊,感觉踩上了个软软的东西,不甚舒服——一只死老鼠。后来老鼠不住地涌出,不久后就一波波地堆满了垃圾桶和回收车。然后它们“鲜血喷涌”,发出了“尖声的死亡哀号”。紧跟其后的,便是神秘而致命的人类热病。
医生们迟迟不愿说出这种疾病的名称,尽管里厄医生很明白,这场瘟疫的感染者颈部淋巴结和四肢会肿大起来,但地方长官和当地医疗组织的管理层并没有拉响警报——就怕这是“狼来了”。
奥兰没有鼠疫血清。新闻媒体也谨小慎微,只是发布简报。与此同时,消毒是家常便饭,与感染者接触的人被隔离了。学校空了出来,安置那些医院病房挤不下的感染者。然而生活仍在继续。死亡统计人数在几天内上升到10人,然后超过20人,很快就到达了40。这时候噩耗传来了:鼠疫紧急状态启动,奥兰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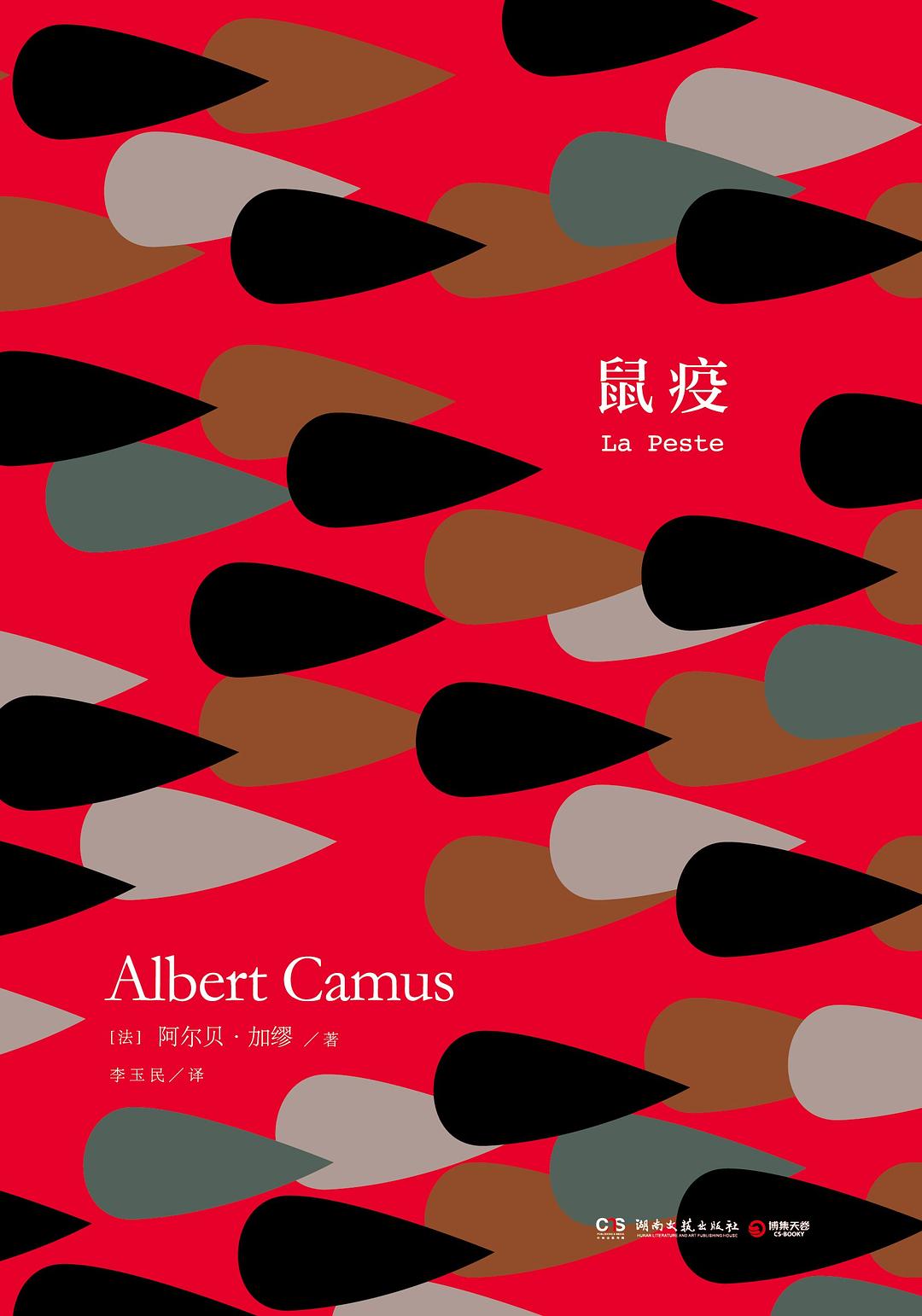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李玉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3
在这个节骨眼上,小说才算是真正拉开了序幕。从不同程度上讲,今天的美国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正在度过小说所写的这一时刻。加缪将这种状态形容为“流亡”。对这位作家来说,流亡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他成年后来到了法国,但这里的大都会对他来说不过是寄宿家庭一样的存在。在《鼠疫》中,流亡不仅有地理意义——人们痛苦地与城门外的世界隔绝,背后更强大的意义是时间长河中的流亡。
人们在这场瘟疫中被迫与过去的生活挥手道别。尽管他们热切希望一切风平浪静,复归平常,但这时候过去突然变得陌生了,仿佛一段事不关己的记忆。起重机骤然失声,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似乎恰是对酷暑作出妥协,人们被困在了脚下的一方土地上。本文的讲述者身份之谜从未揭开,在疫情中保持坚韧,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因为今天活着感到快乐。”
加缪痴迷于各种荒谬之事,比如说被希腊众神惩罚永无休止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鼠疫》中,他用另一种视角,描述了突然悬停的生活,却让其变得生动起来。奥兰城沦为一个巨大的“火车站休息室”,无聊和冷漠席卷而来,但至少人们是活在当下的。卫生小分队急需志愿者,人们自告奋勇。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则疯狂追求着一剂疫苗。一个不知名的人被困在了奥兰,小说叙述者读到了他的日记,并且认为,只有里面的文字才能保证,这一切都不会化作虚无。
回到今天,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人们渴望回到正常生活,但从未停止怀疑——他们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这就像是一种自我谴责。
当地的牧师对陷入困境的羊群布道:“我的弟兄们,这灾祸临到你们身上,是你们所当受的。”这里他并不是在斥责那些公然藐视的人,没有批判那些偷渡禁运品的人,牧师指的是整座城市在鼠疫来袭前的那些罪恶。今天我们也许能从中读出现代之恶——全球化、政治崩坏、世界资本主义。加缪在最后解开了叙事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讲故事的人似乎也在疫情结束时进行宣判:对抗“恐怖”的战役仍是进行时。鼠疫杆菌就如同擦不干净的污点,附着在人性上,“永远不会死亡,不会彻底消失。”
距离第一次翻看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但重读《鼠疫》给了我一种惊喜,46岁死于车祸的加缪在这本书中通过一个病态的语言讲述了人性之善。它可以说是一本救赎的书,让读者即便在绝望时期,也能选择信任。里厄医生和牧师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到底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但对里厄来说,答案并不复杂——当全知全能的神缺席之时,他自己便要履行好职责,救死扶伤。至于邪恶呢,他认为,“恶能让人们升华。”
里厄和城里的更多小市民都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克服了自己的个人欲望,对他人伸出援手。他们发现,个人的快乐可能是耻辱的,而恐惧如果能够共同分担,则不会那么难以忍受。至此,神秘的叙述者选择了见证这一灾难。在小说最后,他表示,自己的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我们在鼠疫时期学到了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本文作者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近日出版了新作《美国银行:创造美联储的史诗般的斗争》(America’s Bank: The Epic Struggle to Create the Federal Reserve)。
(翻译:马昕)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In Camus’ ‘The Plague,’ lessons about fear, quarantine and the human spirit
最新更新时间:04/09 10:37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