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塔利亚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才知道自己怀孕了。要想终止妊娠,意味着她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她的父母双方都无法满足州政府的要求,因为其中一方失踪,而另一方只是偶尔参与到她的生活中。当她按照州里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在堕胎前24小时去诊所检查时,她却误入了真正的堕胎诊所隔壁的“假妇女保健中心”。那里的人竭尽所能劝阻她不要终止妊娠,包括谎称他们会在之后(过了她所在州的最后期限)再为她堕胎,但塔利亚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由于没有能够覆盖堕胎的健康保险,她不得不自费4000美元来做手术。
布里特尼是一名大学生,虽然避孕针没能帮她避孕,但她的日子比较轻松。她只需要走过一群抗议者,他们用涂成红色的洋娃娃零件撒了她一身。旺达琳是一个贫困的非法移民,她的胎儿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遗传病。她需要十几个人帮助她结束怀孕:志愿者司机几次送她去诊所,每次来回需要两个小时(她第一次去诊所的时候,诊所因为多次突击检查而关门),有人留她过夜,还有人帮她支付手术费用。
这些故事和许多其他真实的故事,在《障碍赛:美国堕胎的日常斗争》(Obstacle Course: The Everyday Struggle to Get an Abortion in America)中都有叙述。本书展示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女性,特别是低收入女性终止妊娠的难度。自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Roe v. Wade)案裁决以来,各州和联邦层面已经通过了1200多项限制措施,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自2010年共和党人在各州立法机构中占据主导权之后通过的。尽管部分蓝州——加州、缅因州和纽约州——已经通过了支持堕胎权的法律,但在其他大多数州,获得堕胎权只会越来越难。正如作者大卫·S·科恩(David S. Cohen)和卡萝尔·约菲(Carole Joffe)指出的那样,42%的女性如今生活在对堕胎持敌对或非常敌对态度的州。最近,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流行,几个州已经关闭或试图关闭堕胎诊所,将其认定为“非必要”医疗服务。最高法院将于今年对“琼医疗服务中心诉罗素”(June Medical Services v. Russo)一案作出裁决,此裁决可能会推翻罗诉韦德案,或增加限制使其失去效力。
即使你自认对堕胎问题颇为了解,《障碍赛》也会为你敲响警钟。社会学家卡萝尔·约菲和法学教授大卫·S·科恩以生动易读的文笔,阐述了堕胎女性、堕胎服务提供者、盟友和志愿者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所面临的每一个障碍。堕胎常常被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对待。两位作者介绍了真实的经历,并以此揭示了堕胎女性的勇气、智慧和决心,尽管她们往往被塑造成困惑或自私的形象,而堕胎服务的提供者则往往被攻击为无情和贪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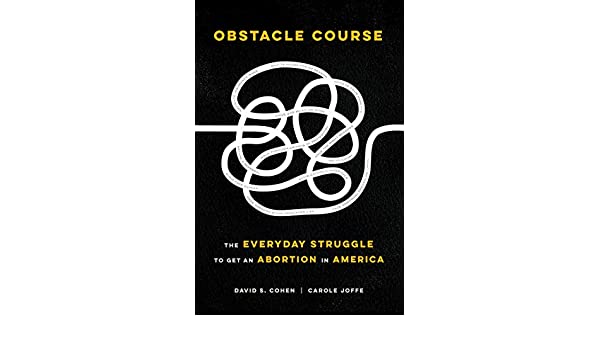
本书描述了许多关于堕胎的迷思,这些迷思塑造了我们的法律,甚至已经悄悄出现在一些捍卫妇女选择权的人的声音中。“父母告知和同意法”很受善意的成年人欢迎,他们认为青少年太不成熟,无法独立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但是,如果像塔利亚那样,父母不在身边,或者父母有困难、有虐待倾向、不能或不愿意帮助女儿,她该怎么办?更何况,如果一个女孩不够成熟,不能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时选择堕胎,又为什么会默认她已经成熟到可以生孩子呢?

还有一个迷思,那就是女性无法确定自己的决定——这也是等待期背后的理由,而等待期不仅会增加手术的成本,并可能因为耽误时间而导致风险。在几个州,医生需要阅读一份旨在阻止患者进行手术的手册。在一些州,这意味着告诉他们虚假的事实,比如说堕胎会导致乳腺癌。
还有堕胎会后悔的迷思。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小组“推进生殖健康新标准”(Advancing New Standards in Reproductive Health)于一月进行的研究发现,超过95%的堕胎女性在五年后依然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
有一种迷思称堕胎服务提供者是无能的,堕胎是危险的。两位作者写道,“堕胎比分娩、输精管结扎术、整容手术、结肠镜检查和吸脂手术更安全。”他们补充说,女性在分娩时死亡的概率是堕胎的14倍,因结肠镜检查而死亡的概率是堕胎的10倍,因吸脂手术而死亡的概率是堕胎的28倍。“总而言之,”他们写道,“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堕胎是绝对安全的。”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迷思,那就是堕胎只是为了方便。穿泳装会很漂亮,可以享受一个奢华的假期,看起来很好看。如果堕胎是这样一件很随意的事情,很难想象每年有80多万美国妇女会忍受如此多的麻烦、羞辱和费用,去做一次堕胎。“女性会翻越滚烫的岩石去找堕胎医生,”一位医生告诉作者。正如《障碍赛》所表明的那样,太多时候,这是她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堕胎与美国的法律:罗诉韦德案至今》(Abortion and the Law in America: Roe v. Wade to the Present)一书中,法学教授玛丽·齐格勒描绘了过去47年来堕胎法的曲折历程,并特别关注支持与反对双方的组织团体。她概述了支撑这场争论的两个理由。一个是关于权利问题:女性的个人决定权与受精卵、胚胎或胎儿的生命权;另一个是关于社会政策的问题:合法堕胎对女性、男性、儿童、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在罗诉韦德案之前和之后,基于权利的争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有利于堕胎权的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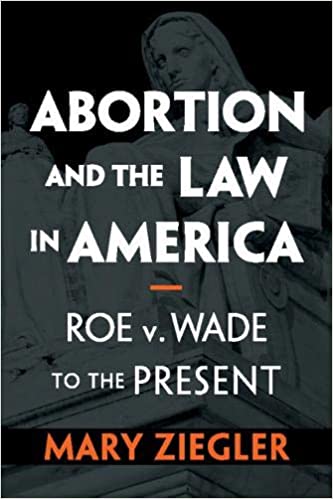
堕胎反对者花了多年的时间来试图通过“人类生命修正案”,该修正案会将胎儿的人格权写入宪法,禁止一切堕胎。关于是否放弃该修正案,将重点放在剥夺以社会政策为由削减堕胎机会,关注女性的安全和福祉、父母的权利和其他问题,这场内部斗争几乎摧毁了反堕胎运动,但最终实用主义者取得了胜利。
虽然他们的目标是绝对主义的——以胎儿权利的名义将所有堕胎定为犯罪,但他们的策略需要循序渐进。如今,法庭和舆论上的争论是监管问题:是否以女性健康为名通过法律,使女性更难堕胎,并在理想情况下迫使诊所关闭。
这种反堕胎策略给堕胎权利团体带来了一个问题。其成员和捐赠者对基于权利的论点——对罗诉韦德案的直接威胁——比起不断一点点公布的反堕胎州法规更让他们兴奋:等待期、有偏见的咨询、通过用昂贵和不必要的规则迫使诊所关门的法律。即使是禁止联邦医疗补助金支付堕胎的海德修正案,也是直到最近才被支持堕胎的一方默许接受。堕胎权支持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民主党总统在位,堕胎权就是安全的。
齐格勒带领读者走过了后罗诉韦德案时代的法律丛林,这是一次令人唏嘘的旅程。堕胎权倡导者在最后一刻赢得了一半胜利,但却为后来的反堕胎胜利铺平了道路。例如,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对堕胎权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它重申了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它也包含了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的“不当负担”检测标准,以决定哪些堕胎限制是允许的。根据这一检验标准,州立法机构不能通过对基本权利造成过重负担或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即为阻碍妇女获得堕胎服务提供了许多途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负担?什么是“不适当”?对一个人来说,任何负担难道不都是不适当的吗?凯西案的判决维持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了堕胎需要父母同意、有偏见的咨询和24小时的等待期。但为什么塔利亚、布里特尼和旺达琳需要通过检验标准才能获得结束妊娠的权利呢?
在《监管子宫:隐形的女性和母亲的罪行》(Policing the Womb: Invisible Women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Motherhood)一书中,法学教授米歇尔·古德温针对法律——更不用说医学、新闻媒体和社会习俗——对女性多种方式的胁迫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那些面对着怀孕、生育和性等问题的有色贫困女性。古德温的观点很激进,她认为,女性的身体被视为国家和男性的财产,而男性在立法者中占了绝大多数,既是法律的起草者,也是执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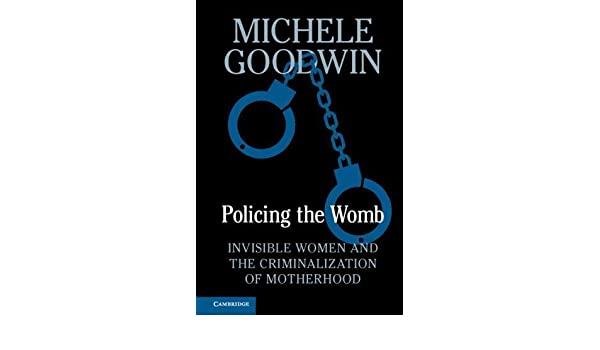
她以一个律师的热情收集证据,结果是毁灭性的。我们了解到,至少有二十几个州禁止移除孕妇的生命维持系统。这本书讲述了马里斯·穆尼奥兹的可怕故事,她已经脑死亡了,怀孕的身体却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里被人为地维持着,甚至妄想在她腐烂的同时,让她生出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我们了解到,有数百名妇女因为怀孕期间的行为而被捕,有的还被关进了监狱,即使她们的孩子是健健康康出生的。妇女仍然被强迫进行剖腹产。斯坦福大学游泳运动员布洛克·特纳在2016年的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中被判强奸罪,但亚伦·佩尔斯基(Aaron Persky)法官只判处了他极轻的刑罚,对于受人尊敬的白人男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对古德温的很多资料都很熟悉,但看到这些资料被收集在一起,依然感到吃惊而愤怒。
古德温告诉我们,不只是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的权利被漠视。她描述了自己在加州奥兰治县一个富人保守女性聚会上的演讲,在那里,一个又一个女性讲述了她被产科医生欺负,要求她听从他的命令,有时还威胁要报警的故事。一名医生以宗教原因拒绝为一名流产的女性治疗,因为这将意味着终止妊娠。“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女性在怀孕期间都有可能受到监视、警察和犯罪行为的侵害,即使在加利福尼亚州,即使是在一个宪法中规定了女性生殖隐私权的州,也是如此。”
在我读过的书里,《监管子宫》对生殖正义的必要性做出了最好的解释,而不仅仅是生殖权利。把重点放在选择堕胎的权利上,并没有触及到法庭、监狱、妇科医生办公室和医院对女性残酷、不公正和厌恶行为的全部内容。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毒品犯罪而迅速将母亲们关进监狱,尽管她们的孩子们深受其害。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尤其是黑人妇女的死亡率仍在上升。这并不能解释在我们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里,为什么在让堕胎变得如此艰难之后,我们给母亲们提供的帮助却如此之少,而儿童高贫困率的现象依旧让人痛惜。
如果你以为美国对女性越来越友好、越来越平等和公正,这本书会打消你的幻想。在某些方面,美国对女性正在变得更有敌意和惩罚性。
本文作者Katha Pollitt系美国诗人、评论家,她的最新作品是《支持:重夺堕胎权》。
(翻译:李思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