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佩服朱迪斯·巴特勒:她不喜欢惬意的生活。秉持现实是一种社会性或语言性的建构这样的观点,她在职业生涯的前一阶段和其他社会建构主义者痛快地玩了一场懦夫博弈(game of chicken,博弈论术语,指各方须轮流示弱才能得到最优解但却非要相互逞强的局面,这里是说巴特勒的建构论立场比同行更彻底——译注),将一切还认为有非语言性现实的观念残余尽数拔除。在之后的生涯中,她又主张特定的某些伦理真理仍值得我们关注。她在最新的文集《非暴力的力量》(The Force of Nonviolence)中提出——尽管她肯定不会说非暴力是潮流之类的大白话——有一些好的理由促使我们去认可一种全球性的非暴力伦理。
社会建构主义使为一种伦理作辩护变得异常困难。巴特勒的立场说到底也会主张“事实”在经过特定文化的语言性建构之前是没有意义的。诸范畴是不稳定的:没有统一的自我,没有人性,没有共享的合理性,也没有任何类型的永久底层(substrata)。以范畴将人类分成不同群体(哪怕借助科学),无非是一种产生偶然的统治与服从层级的方式。如她在自己最著名的《性别麻烦》一书里所言,生物学是一种“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医学-法律联盟,产生了一系列无法被预料到的范畴虚构”。当然,她以将此论应用于男女两大范畴而闻名。没有先在的物质基础,从头到尾就只有“排斥性的”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权力关系。
新书一开头就冒出不少问题,巴特勒企图克服这一张力:宣称暴力是被建构的,同时又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追求暴力。她告诉我们暴力总是“经过诠释的”。一些人认为暴力只包括有意的身体伤害;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还包括心理伤害。还有人认为——这些人很可能读过巴特勒早期的一系列论著——言辞也可能是暴力性的。有时某个政权会给特定的异议群体贴上暴力标签,借此掩盖自身的暴力,诸如此类的做法不胜枚举。在巴特勒看来,我们可借以追溯及确立事情真相的客观基石是不存在的。诚然,她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有犹豫,有时会把形而上学的鸿沟(现实里的鸿沟)说成是认识论上的鸿沟(知识里的鸿沟),一会儿在某句话里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个基石是可能存在的,一会儿又予以否定。例如:“针对非暴力提出辩护或反驳,要求我们确立暴力与非暴力的差异,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并没有得出识别这两者的稳定语义学区分的捷径,在此区分经常为许可及纵容暴力目标与实践的意图所利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换言之:鉴于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分经常会被利用,两个观念之间的区分是不稳定的。对于有人担心此论有相对主义之嫌,她的回答是:“那一困难并不意味着一种混乱的相对主义。”这样差不多还能说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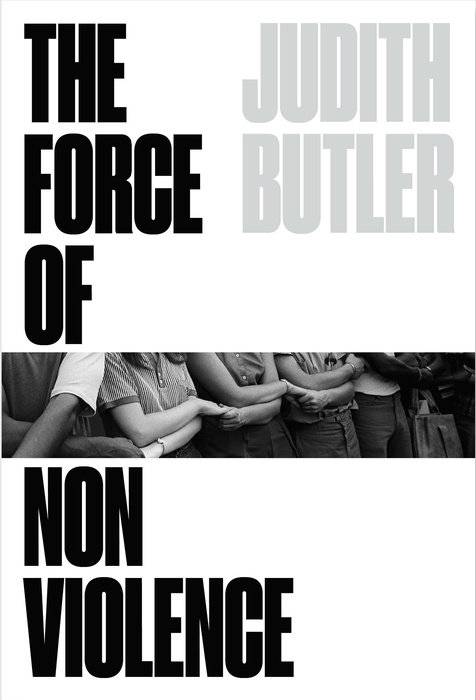
另一个有关伦理的明显问题在于,任何用来为道德原则奠基的有关合理性或人类本性的普遍预设之不可得性(unavailability)。巴特勒试图诉诸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亲自由派的案例来打发掉这个问题——自卫就允许运用暴力——并辨析了当中的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项矛盾是,以自卫之名而施行的暴力是针对自我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the self),并且它可能朝得不到辩护的暴力滑坡,这不无悖论意味。这个论证的要点大致如下:在自卫中出手,需要表明谁是那个“自我”。鉴于我们都是扎根于社会的存在(socially situated self),自我总是大过个人的身体,它还包括家庭、友人等等。细究这个经过扩展的“自我”的诸多界限,要求我们区分出哪些生命“可悼念(grievable)”而哪些不能,但这个区分又是武断的。
至此她的论证结构变得不清晰了。在某些时候,巴特勒似乎想保留扎根于社会的存在这一概念,进而为扩展性自卫(extended-self-defence)辩护。例如,她在《保存他者生命》(To Preserve the Life of Others)一文里说,“我必定会保存这些相互冲突的纽带,若没有它们,则我自己也就不存在了,并且变得不完全可思。”在另一些时候,她似乎又指责绑定的自我(bounded self)这一概念不融贯,诉诸它的话就根本无法为自卫辩护。

巴特勒提出了一项取代有限自卫的新理想:非暴力的“全球性义务(global obligation)”,我们可借助它来疏导攻击性的冲动。这一理想源自于对我们作为社会心理性存在(psychosocial being)所共享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一切生命都具备同等的可悼念性这一理念”的承认。如果这一理念得到严肃对待,那它将鼓励我们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构想“其他”族群或移民:“归根结底,如果一条生命从一开始就被当做可悼念的,那就要有各种维系及捍卫此生命免于伤害和毁灭的预防措施。”犬儒主义者可能会担心这个腔调和老式的普遍道德原则没什么两样——那些巴特勒费了很大功夫来埋葬的东西。他们还可能会质疑,在一个自我及其意志均被地方性环境所建构的世界里,诉诸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针对这两点,巴特勒的回应似乎是,这并不是针对当今的一张有效处方,而是一种“政治想象力”或者“反-幻想(counter-fantasy)”:一幅有关事物在未来将如何被概念化的启发式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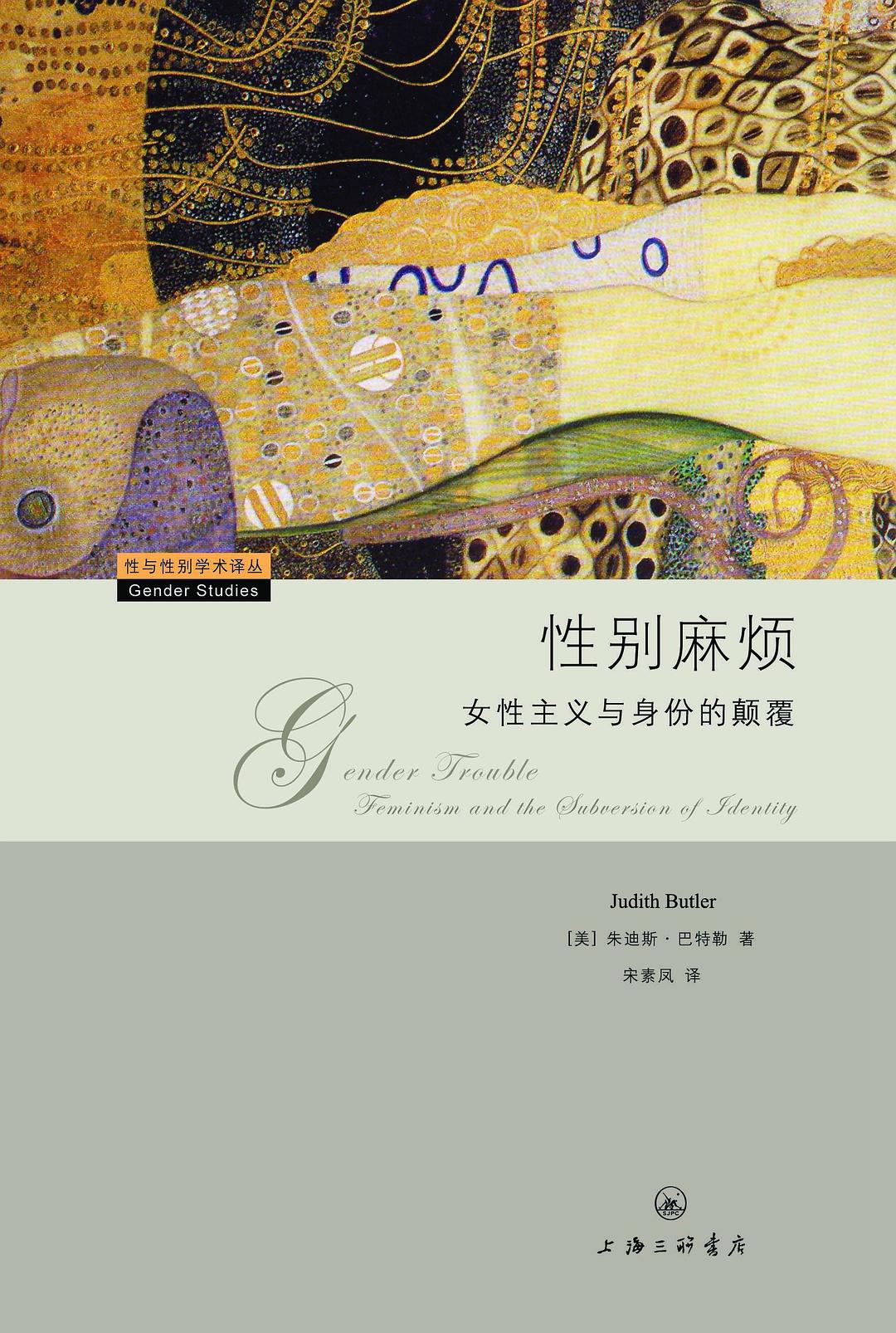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凤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9-1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太清楚这是否就是她所认为的万灵药。早期的批评者已经指出,说某个人是可悼念的,可以有“由他人来悼念”或“由我个人悼念”这两层意思。这颗星球上的每个人原则上都是可以由某些不特定的人来悼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我的眼中都具有潜在的可悼念性。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对其中大多数人一无所知,而我也不会去悼念那些我根本不知道的人。如果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实际上会以及不会去悼念的人这一区分之“武断”,那么答案很明显:它全然没有从爱的视角(perspective of love)出发!这一视角是常人——区别于利他主义的圣贤以及毫无情感的呆子——经常会采纳的。我爱我的家庭和友人,是因为他们是他们,于我而言不可替代。如先前所言,巴特勒意识到了这一隐忧,并试图回避:“虽然可能有人认为我在呼吁每个人面对他人之死,都要为之恸哭……但我想说的是,悼念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甚至于是非个人性(impersonal)的形式。”然而这样说几乎于事无补。
针对特定的框架化(framing)如何“排斥”了特定的群体及未能代表其政治利益,《性别麻烦》与其后的诸多论著里都不乏有理有据、值得赞许的思考。巴特勒精心勾勒出了一种文化上的短视(cultural myopia),即认为只有和我们“相似”的生命才值得悼念,或者一味给其他族群打上“暴力”之类的标签。她在某处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人无法形容或者根本不知道哪些生灵是不应当被杀害的,那他就不可能遵从反对暴力的禁令。”对于许多熟知巴特勒早期论著对当今之深远影响的人而言,此说不无滑稽意味。巴特勒有关人为的男女之分如何造就了有害的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等论述一度吸引到不少追随者,如今这些人拒绝承认女性性别的物质存在(material existence of a female sex)或任何专属于某一性别的需求或利益。当今某些著作里也出现了一些软化的迹象:例如,不再频繁谈及“厌女(misogyny)”,以交叉性的(intersectional)眼光来审视警察对待黑人女性的方式,以及承认“有关脆弱群体(vulnerable groups)的话语……对女权主义人权事业以及关怀伦理学而言都是重要的”。但这套话语转而又被说成是“成问题的”,理由是它“在对待诸群体时,先入为主地将其划分为脆弱或不脆弱的”,并“强化了一种家长主义的权力形式”。
在新书的后记里,巴特勒讨论了拉丁裔美国人当中的“杀女受害者(victims of feminícidio)”,按其解释,这些人——用老式的说法,不管其生理上是男是女——遭受暴力对待的原因在于被“女性化(feminized)”了。说到这里,向来不谈“一般意义上的男性针对女性的独有暴力倾向”的巴特勒再度讲起了精神分析。最近我刚读完克里斯蒂娜·兰姆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战场》(Our Bodies Our Battlefield)——该书详细记录了战争中男性对女性由来已久的强奸、性虐待以及剥削——我觉得巴特勒这种把整个性别暴力的故事搅浑的做法,着实令人难以容忍。
(作者Kathleen Stock系苏塞克斯大学哲学教授,新书《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s)》将于2021年出版)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