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作家、生态学家和鸟类观察家约瑟夫·德鲁·兰哈姆(Joseph Drew Lanham)在《猎户座》杂志上发表了《黑人观鸟者的九条法则》一文。“你需要用望远镜来把那只毛茸茸的鸭子从一大群鹰嘴鸭和环颈鸭中区分出来,”他写道,“你需要带照片的证件来说服警察、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打着手电的保安,表明你不是恐怖分子或者逃犯。”
兰哈姆在克莱姆森大学担任野生生物生态学教授,业余时间一直从事种族与观鸟等课题的写作,2016年曾出版个人回忆录《家园:记一名有色人种男性与自然的邂逅》(The Home Place: Memoirs of a Colored Man's Love Affair With Nature)。今年2月,黑人男子阿莫德·阿尔伯里被两名白人男子杀害,作为对此的回应,兰哈姆最近把这件事加进了他2013年时列的清单,《名利场》杂志不久前将其刊发了出来。
5月25日,在纽约中央公园,另一名黑人观鸟者克里斯蒂安·库珀提醒白人女子艾米·库珀在林区要看好自己的狗,这既是公园的规定也是保护鸟群的需要。克里斯蒂安·库珀录下了她的愤怒反应:艾米·库珀向他疯狂地咆哮,叫来了警察,谎称自己遭到威胁,更反复在电话里强调他是个非裔美国人。克里斯蒂安·库珀的视频很快就在网上走红,可谓是兰哈姆作品的鲜明体现。
5月26日,兰哈姆接受了《名利场》杂志的电话采访,谈到了上述的视频以及自己的观鸟和写作经历。
人们有没有因为2013年的那份清单而向你伸出援手?
兰哈姆:有的。我当时在山边做一些修缮工作。我在那里有间小屋,过去住是为了避世和社交隔离,那里可以看到不错的鸟而且比较凉爽。回来以后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我在脸书主页上发了不少东西,包括精美的鸟类照片、隔离期间在后院观鸟的心得,以及有关阿莫德和布莱昂娜(Breonna Taylor,今年3月被缉毒警察误杀的黑人女子——译注)的社会评论。昨晚对黑人来说意义重大,就好比是最后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不啻为晴空霹雳。昨晚我其实已经发了相关的推文,但把它设成了私密,今天一早起来才把它改成公开状态。我认为,发声和拥有发声的机会是很重要的,不仅要让他人知道你的感受,还要激起他们的义愤——有很多人对这种事也是不赞成的,他们只是保持沉默。有时候人们会向你寻求证据,这回证据就来了。发生的一切已经是板上钉钉,有人利用警察来威胁你,警察俨然成了一种武器。

这就是种种事情的样貌。你不想牵扯进去,但最终还是被席卷。即便我逃去观鸟也仍然会面临问题。我在安全区吗?我观鸟的时候有人会盯着我吗?身为一个黑人,带着望远镜,呆在人们可能不希望其出现的地方,他们会对我有怎样的观感?
观鸟通常被视作某种逃避,你的作品表明这并非事实——人类的诸多问题也会反映在观鸟上。
兰哈姆:能预设此举属于逃避,本就是一种特权。很多预设都是如此。一个黑人观鸟者必须时刻关注周遭的环境和空间,以为你可以随处游荡并且得到接纳,是很幼稚的想法。
我偶尔会和朋友一起观鸟,但我发现自己与鸟儿们独处的时光是最有意思的,能够有某种深度的交融。你的内心里经常会为此斗争。我应该去那里吗?我不应该去那里吗?我是快速通过还是漫步徘徊?你会发现自己有时在心理上几乎就矮了人家一头,以表明自己是不会冒犯的或者动机是纯正的,这种内心交战让人疲惫不已。
此类作品在你的领域里有多常见?
兰哈姆:有人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克莱姆森大学的同事今天刚发了一篇论文,正好谈公共空间中的娱乐与种族(论文作者是克莱姆森大学的哈里森·平克尼和科里斯·奥特莱)。思考这个话题的人并不算多。如果你多读一些类似的作品,关注诸如“失去树林的孩子”之类的问题及其意义——显然,基于社会环境、生活地点、城乡差异等等,对不同的人而言它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种族对此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十分要紧的。一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受任何惩罚,做自己想做的事。黑人享受不到这些,我们没有那种自由。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践行这种自由,就可能会冒犯某些人的观感,有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这其实就可以归结为:冒犯的是对我们应当有何种举止的观感。黑人不应成为观鸟者,或者不能呆在某些空间,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抗争的——我们也一直都在为此抗争。

你曾经估算过,90%的观鸟者都是白人。眼下的一系列新闻也许表明情况比这更糟。
兰哈姆:白人占绝大多数,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爱好。我认识的很多观鸟者也都是白人,我们的共同语言不少,我跟不同文化或种族背景的人打交道的经历有好有坏。但我们一同观鸟的时候也能短暂地超越一切分歧。不过,每当有人打算进隔壁小区观鸟或者去这样那样的地方时,我也会有种恐惧。我可能对那些地方略有了解,表示不赞成去那里。你懂的,我不认为我可以在晚上或黄昏时分自如地在小区里带着望远镜寻找夜鹰。假如我发现某个地方有很多邦联旗帜或者“别惹我(Don't Tread on Me,美国海军旗上的字样,始于独立战争时期,取响尾蛇性格刚烈,能迅速反击来犯者之意——译注)”乃至于特朗普的旗帜,那是百分百不敢去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警示信号。
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在2013年开始以清单形式记录黑人的遭遇?
兰哈姆:《猎户座》杂志的诗歌编辑来电找到了我。我和他们之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交情,他们敢于发表我早期有关种族、观鸟和非洲的文章,可以说体现了极大的勇气。它几乎成了我的发声通道,我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所见与所感。接到电话的那晚,编辑问我是否有兴趣做一个统计性的工作。我平时乐于看这样的统计,但自己没有专门写过,她说,“你可以写一些有关观鸟的东西,或许还可以加入你身为黑人观鸟者的经验——畅所欲言就好。跟着你的感觉走就行。”当时是2013年,特雷沃恩·马丁被害案才刚过去不久。我立马坐下来花了四五十分钟——也可能有一个半小时了——写了一份回复给她。她给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几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的编辑,因为他们会认为我真的可以能那么快就搞定。
我和为数不多的黑人观鸟者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作战”经历。我曾经和一名黑人观鸟者参加过某个观鸟节,几千个人里面估计最多只有五六个黑人。我还记得,当时公交车上的人叫我的时候,喊的是他的名字。我身高一米九,两百多斤重;他才一米八不到,体重一百四十来斤。这些人善于辨识各种鸟类——大部分普通人是看不出这些鸟有何差异的——但他们对两个黑人之间的差别视而不见。诸如此类的事正是我2013年写下的所思所感的一部分。对于我这样的非虚构作家,这是最好的写作经历。我对这些资料了如指掌,几乎不需要做什么调研,因为我天天都在经历。它很自然地就从我的指尖流淌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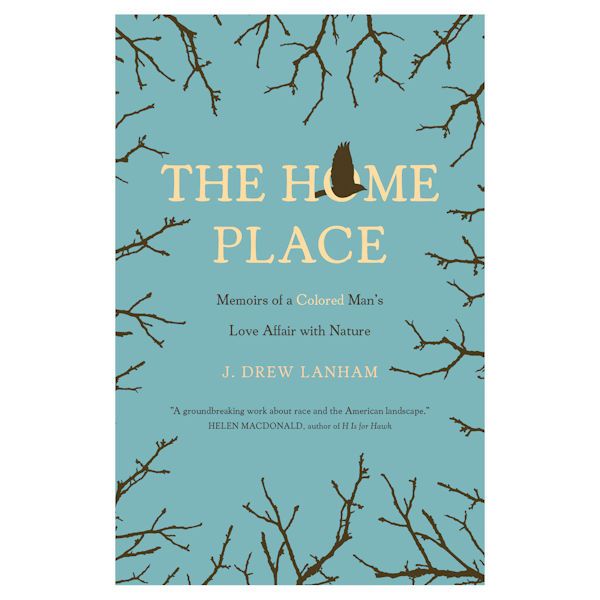
上周六我回到了同一个观察点,这次观察的鸟名叫黑枕威森莺,它的色调以柠檬黄为主,配上背部的橄榄绿十分养眼。黑枕威森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兜帽”,其雄性面部和形似按键的眼部周围的黄毛上生有一圈黑毛,凭这个圈以及动听的鸣叫声就马上能辨认出黑枕威森莺。我花了好一阵子来寻找它,最后找到了,它藏在阴影里自在地唱着歌。这种鸟的确奇妙无比,我开始思考身为一只鸟的艰苦与磨难,这家伙在抵达我所在的地方时已经飞越了上千英里,这是如何做到的?看着它唱歌,我就在想,成为这种鸟一定很酷,它能戴着这样的“兜帽”而不会被威胁、迫害或筛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回到一个可以放心做自己、不必为鸟这个身份而担忧的地方。它在自己的居住环境里完全自如。这是一个颇有禅意的思想时刻,也刷新了我之前秉持的其它一些法则。这是全新的九条法则,同时也是我身为一个黑人男性坐在自家后院观鸟时历经一系列思想斗争得出的启示——布莱昂娜·泰勒在家中被害后,我甚至会怀疑呆在自家后院里是否还安全。
说回阿莫德,追捕这名公民的人们声称:他们在跟随他的时候觉得此人可疑,遂将他拦下来,他拒斥这种私设公堂式的抓捕,继而遭到了杀害。我认为库珀所做的无非是告诉那位女士你的狗违规了,你可以把它牵到某处去,你的狗狗呆在指定地点也会很开心。而她则决定以警察相威胁,原因只在于他是个黑人。
一些网友对我的回复是,这真是太可怕了,你看到那只可怜的狗了吗?我是爱狗之人。我家里也养狗。我对这位女网友说,“是啊,她觉得自己不赶紧把这个男人吊死在树上就会被勒死。她是那样地怒不可遏。她试图把警察用作武器来对付一个黑人男子,她完全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可以坦率地讲,与警车毫无理由地打着大灯跟踪我的情形相比,我在森林或者有可能杀死并吃掉我的猛兽出没的地方散步时,安全感可能还更强一些。我能分辨出这些灯光来自什么车,可能是皇冠维多利亚或者新款的道奇挑战者,它们的行驶风格迥异,这些追猎者和大白鲨在水里的泳姿也是各有特色的。
有鉴于此,对于那些口称“我要叫警察来抓走你这个黑人,告诉他们你正在袭击我,或者你侵害了我”的人来说——最近的种种新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很有可能会碰上警察敲门,要求你证明自己没有做别人指控你做过的那些事。

在那种情况下,鸟儿们就成了某种我必须回归的遥远记忆,观鸟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根基,呆在一个可以全神贯注地观鸟而不必担心有谁跟踪、盯梢或是询问我的意图的地方,我就能获得片刻的宁静。
你是一名诗人、散文家和回忆录作家,而这部作品融合了上述三种体裁。在你看来,这一风格对你而言如此得心应手的原因何在?
兰哈姆:我甚至不清楚为什么法则有九条而不是十条或者十三条,也可能有更多。但我写完九条就感到长舒了一口气,我感到自己在写作过程里是屏住呼吸的。在处理一些冗长的论述时,你会觉得自己几乎停止了呼吸,稍稍吸一口气都会打断思路、影响遣词造句乃至于失去流畅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我不想失去流畅感。有人曾经问我是不是认为九这个数字有某种魔力或者有玄学成分,答案是否定的,九就是九。我不需要更多了。当时我就是想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即刻就停了笔。
周六的过程类似吗?你是否也感到长出了一口气?
兰哈姆:是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必须提醒自己呼吸。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也不是件小事。和鸟儿在一起的时候,深呼吸以及运用腹式呼吸法可以让我更专注于此时此地,长时间聚焦于一只鸟于我而言意义非凡。不只是泛泛地数有多少只鸟,而是驻留于某一只鸟,去观照并且理解它。我会在脑子里预想一些故事,有些故事后来在写作中会用到,另一些故事则单纯有助于与鸟儿相处时保持呼吸节奏。
我在观察黑枕威森莺时是不愿呼吸的,我试图拍一张它呆在阴影里的照片,我担心它时刻可能飞走。我尽力屏住呼吸——并吸收它歌声里的每个音符。这种鸟对我很重要。我不想重复一些老生常谈,但鸟的生命之重要确实让我联想起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它也理应是重要的。我并不想见到一百只黑枕威森莺聚在一起,只想单独聚焦那一只。这一聚精会神、大气不敢出、全身心都投注在那只鸟上——字面上以及比喻上都如此——的时刻,可谓具有某种超越性。拍完许多照片后——它还是在阴影里,光线并不好——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吸收了那只鸟。我终于可以呼吸了,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一切都与我跟其它东西打交道时的体验截然不同。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