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五四时期,冰心、庐隐、凌淑华等女性作家的出现,第一次让女性写作浮出中国历史的地表,区别于古典文学脉络下的“女先生”。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映照着今天我们对女性的理解,而她们对这些形象乃至自我形象的创作,又与男性批评和审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百年已过,当互联网取代报刊杂志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时,女性写作又走到了哪里?
在“成为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活动现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戴锦华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当下中国的女性写作与女性现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多元的现实总是在文学作品中缺席,比如对“拉姆案”的讨论和反思,几乎是由社交网络舆论和新媒体写作来完成,文学创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囿于单一的现实。不过,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之外,张莉窥见了新的言说希望——在脱口秀大会上,李雪琴、杨笠等人的说话方式以及观众的反馈让她看到,新一代的性别观念正悄然发生改变。

与女性生存状态脱节的写作
我们一般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读者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模板,因而可以说,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TA的读者。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女诗人、女词人,也正在于她们以新女性的经历和身份去创造新女性的形象。
张莉指出了这种观点的不足——女性作家对笔下人物乃至她自己的塑造,不是完全自由的,她受制于男性批评家或读者的看法,例如冰心对女学生形象的书写,在1927年以前,几乎是按照她自己的形象。“冰心姐姐的形象是去情欲化的,你看不到她的容貌,但是你知道她的影像,她穿素淡衣服,浅颜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短头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女孩,”张莉说,“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冰清玉洁的,她是作为一个姐姐、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新型女性被大众接受的。”冰心在五四时期受欢迎,是因为她对自己和小说中人有意无意的刻画,符合了当时人们对新女性的想象,到国民革命之后,冰心所代表的美被丁玲、茅盾笔下的女性所取代。


也即是说,读者的阅读趣味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令张莉感到失望的是,今天的女性写作无法与现实匹配,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以及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与现实脱节了。”张莉认为,家暴是一个重要的书写题材,但几乎所有女性作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活动主持人、《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指出,像拉姆所遭遇的惨剧,基本都由新媒体、网络舆论来表述,我们似乎很能想象,现在的作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
被阶层区隔过滤掉的现实
学院派女权、微博女权、田园女权……在女性相关的互联网议题讨论中,这几个词频频出现,似乎勾勒了一条由学院至民间的女性主义传播路径,并且暗示一种由正宗到伪劣的价值序列,经常被用来质疑和贬低女性发言与诉求。戴锦华在对谈中强调,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经由学院路径,而是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有关,一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实践性和社会性。世妇会召开后,全国重要的大学几乎都设立了女性研究中心、性别研究中心,或是开设了女性主义课程,彼时女性文学研究蔚然成风,不再如戴锦华与孟悦写作《浮出历史地表》时那样的偶发零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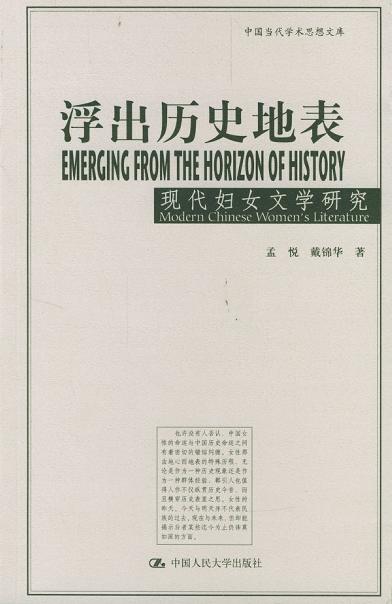
戴锦华 孟悦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7
在戴锦华看来,网络女性主义既不是学院以人文科系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又不是以基层妇女为主体的、有专业人士参加的女性主义,它是经由网络媒介汇聚起来的一批“相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形成的言说实践脉络”;这几个脉络彼此平行,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群体文化在网络上逐渐覆盖、抹除了“基层的、年长的、边缘人群文化”。
最近“假靳东”事件爆出后,引发了很多有关底层中老年女性群体心理需求与状态的讨论。实际上,素材无穷尽、无死角,正是互联网空间的一个特征。这些现实一直存在,但信息被阶层的滤网逐层过滤掉了,如今的阶层差异也要比过去的二三十年大得多。戴锦华认为,在这样的急剧退化和分裂的世界中,“连共情也变为了一种带有梦想性的召唤。”
“今天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空间中发生,”如戴锦华所言,当书写权掌握在非底层女性作家手里时,她们能否共情,就成了能否书写“拉姆”们和“黄月”们故事的关键。有趣的是,在对当下文学界的女性写作抱有批评的同时,张莉说,自己在其他领域发现了新的女性言说方式。她看脱口秀大会时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话语方式发生了一些“隐秘而深刻”的变化,比如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就用一种“底层的、受过忧郁症的女性视角,所谓弱者的语言”,来展现“女性的强韧”,尽管北大学历给她增添了精英的光环,但她的经历能够与大多数底层青年女性共鸣。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