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昨日下午揭晓,作家双雪涛以其短篇小说集《猎人》获奖,获得3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金。其他四位入围短名单的作家林棹、任晓雯、沈大成、徐则臣则获得了两万元奖金。
双雪涛是第二次入围该文学奖,2018年曾凭《飞行家》入围首届该奖项决选。他在获奖感言中称:“《猎人》这本小说集有11篇小说,因为这本书而得奖我个人感到尤其开心。”双雪涛说自己在过去几本书里写了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包括童年少年记忆里的东西,而《猎人》这本书“是距离我内心比较近的一本书,虽然它所用的素材并不是我最熟悉的,但是它确实代表着我这两年所思考的问题和对小说的认识,能够得到肯定对我是特别大的鼓励”。
评委:走出东北是双雪涛的“自我了断”
双雪涛和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近年来被统称为“新东北作家群”。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评委孙甘露称,从双雪涛作品在读者中的反映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使地域在文化上的含义不断增值、不断明晰,同时也不断复杂化。“双雪涛使得东北寒冷、重工业、集体这样一些沉寂的话题,重新又回到文学阅读的视野当中。当然,这远远不能涵盖双雪涛的写作。他所做的努力一直也是很多作家所做的,就是从具体而微的描写中把个人的经验提升出来,使其获得一种普遍性。”
评委之一的苏童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双雪涛早期作品确实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舞台不流动。但是在《猎人》一书当中,除了《杨广义》这篇,其他作品都已经走出了艳粉街,走出了东北。苏童将其称为作家的“新生”和“自我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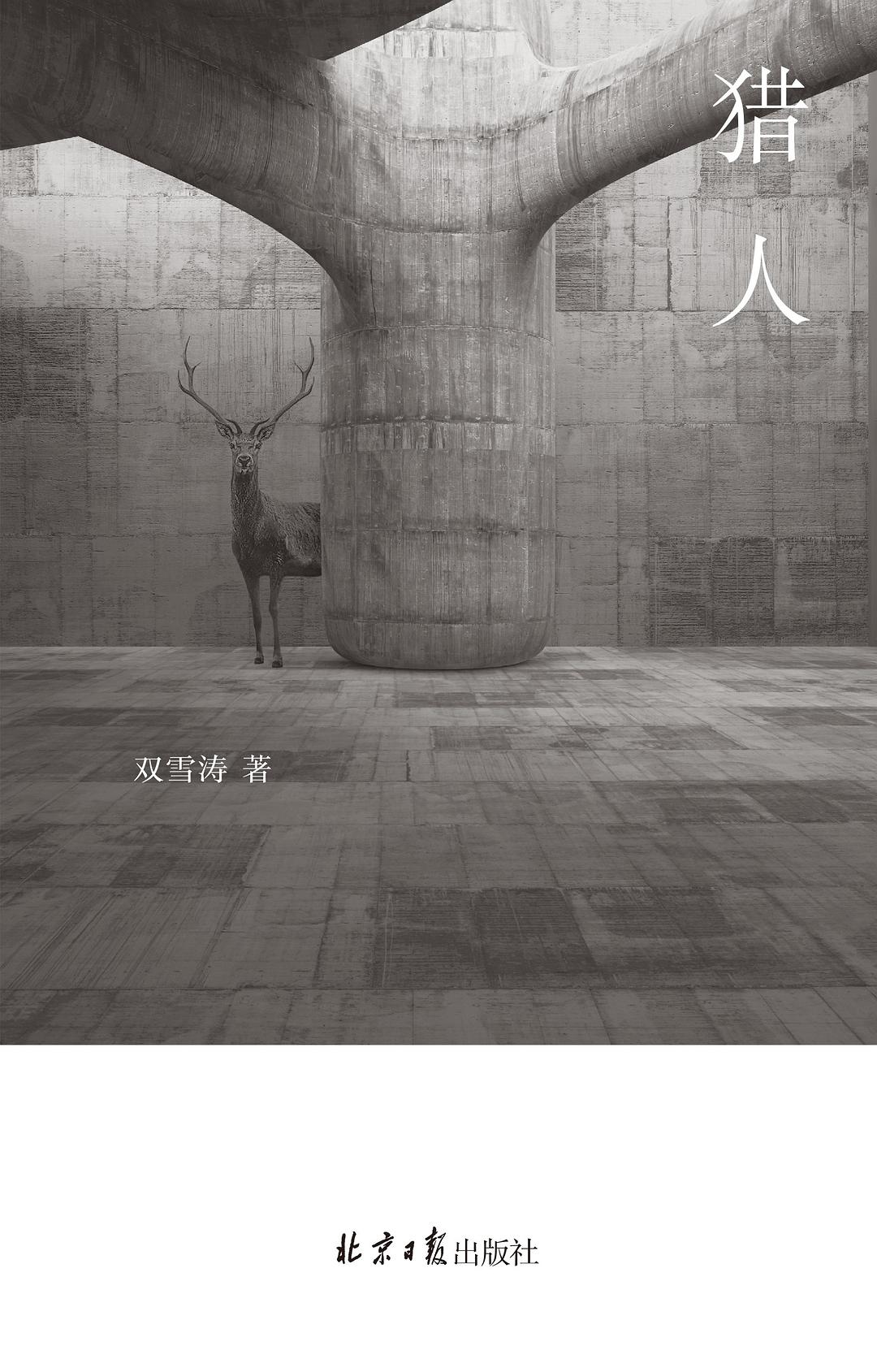
双雪涛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7
苏童把双雪涛的作品比喻为“有伪装的迷彩服”,他向界面文化解释说,这是因为读双雪涛的作品很难判断其文学营养来自于哪里,“他善于伪装和自我掩护,这是好的写作。”双雪涛在活动现场也提到,他很多时候会把自己的想法放在文字的后面。来自台湾地区的评委杨照也称赞了《猎人》“非常纯熟的笔法”,他认为双雪涛的《猎人》和沈大成的入围作品《小行星掉在下午》都是在现实的场景里展开科幻的奇想,成功地在小篇幅当中塑造了集中的悬疑感。但相较而言,双雪涛的想象空间更为开阔,收线也比较纯熟和自然,“双雪涛有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使得他的每一篇都比较平均、比较完整。沈大成有一些好的神来之笔非常非常神奇,但有些地方就没有办法收得那样自在,”杨照在评委意见中提到。
音乐人张亚东也分享了阅读双雪涛作品的私人感受:“我在读《猎人》的时候,夜里常常突然大笑,一个人笑到吓到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笑。”他认为双雪涛的作品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终止式,“非常酷,他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文学叙事停止而停止,一直在我脑子里。我认为我看不懂,然后我觉得我看懂了,然后觉得又不懂,最后又看懂了。”张亚东在评审现场说,“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回旋,这样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触电”:苏童与双雪涛谈小说影视化
双雪涛近年来不仅在文学界得到关注,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摩西》和《刺杀小说家》也相继被改编成电影。苏童的“触电”则更早,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世界瞩目。因此,界面文化向两位作家提出了是否担忧影视对文学形成冲击的问题。苏童回答称,影视冲击不了文学,影视反而改善了很多作家的生活质量。“不要把影视和写作对立,它们不存在任何敌意。文学和电影是亲戚关系,不走动正常,走动也正常。”
在苏童看来,电影创作是以导演为主、以资本为主的集体劳动,而一篇小说通常都是一个人写出来的,完全是个体创作的结晶。“两者本质不同,所以不可能一方对另一方产生威胁。”双雪涛同样认为电影和文学创作本质不同,他说:“给作家一大笔钱不会让作家写得更好,但如果给电影制作者一大笔钱,电影会制作得更加精良。”另一方面,电影是近现代的艺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科技发展也许会对文学的内容上有所启发,但是对文学的生产方式影响不大,所以“它们的亲缘很微妙”。

双雪涛也提到,在张艺谋执导《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年代,“是一大群朴素的艺术家真诚地在做事情。”但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IP等提供给影视的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文学给电影的营养还远远不够。“希望能看到有更多真正的营养提供到电影里。这也是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电影的原因。”
在与影视业的合作过程中,苏童说自己从来不干预影视创作,作家内心还是很希望有很完美的和电影的合作,让小说变成特别有名的电影,但是自己干预之后,电影并不一定能拍得更好,所以干预没有意义。“从世俗意义上说,不干预让我进退可据。拍得好,我乐意承认是我的原作,拍得不好,就可以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苏童说。
双雪涛认同这一看法,他说,有的电影项目有自己成熟团队,有自己清晰的世界观要表达,这时他就不怎么干预。而有的导演认为作家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这时他也会做一些工作。“但没有做编剧,因为那样就让自己没有退路了。”

文学意见:评委谈入围作品
徐则臣 《北京西郊故事集》
张亚东称,徐则臣作品描写的很多东西“是我刻意回避的,不敢去思考的,故意虚化的”,所以在阅读时,“那些我刻意虚化的东西会突然变得很真实,让我不太敢接受。”苏童则用“正装,黑白系,大牌子”来形容徐则臣的写作风格。孙甘露对其处理历史、现实、观念和叙述等各个方面的评价是“非常端正和持重”,他说徐则臣“追随这个世界理性的一面,并且深入其中,同时也以长线的思考使自己获得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他所依赖的线性的历史观使小说这一形式获得价值和经典性的基石”。
任晓雯《浮生二十一章》
张亚东喜欢《浮生二十一章》的语言节奏,“她写专栏,文字受限,所以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节奏。对于我一个外行来说,我突然发现原来方言中文竟然有那么美的时刻。”杨照认为,这部作品和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都是短篇幅写实的作品,但这篇小说每一篇是一个独立人物,人物跟人物之间可以有更深刻或者是更不一样的互动关系,“让他们的人生有一些交错,也许小说就会更加丰富。”另外,因为徐则臣、任晓雯写的都是时代的伤痕,写的是小人物被命运捉弄所产生的许多痛苦,因而有时候会让读者觉得有点沉重。“如果让大家在感受到生命沉重的同时,也有一些心灵的段落或者让我们可以笑得出来的地方,我相信这两部小说都可以比现在表现得更好,”杨照指出。
林棹《流溪》
杨照认为《柳溪》的文字非常特殊和风格化,不是一般小说叙事的文字,而是“接近诗的文字”,其效果一方面在于读者可以摆脱开人物的对话,单纯针对文字来欣赏林棹这部作品,另一方面也会有文字的“后遗症”——首先,因为诗的文字高度浓缩、讲究意象、象征以及句跟句之间的连接,这种文字一不小心就会写得装模装样,或者意象彼此产生冲突矛盾,这样的文字也逼着读者必须慢下来读。评委张亚东也谈到了自己不得不慢下来读的体验。他称,林棹的作品让他一直查字典,但慢慢看下去,一直看到结尾,自己被她的作品深深打动。“我自己忙起来有时候像一个快镜头,根本慢不下来,花时间读她的作品,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急躁、那么暴躁、那么没有耐性,花时间阅读她的作品是一种享受。”
沈大成《小行星掉在下午》
“在我阅读的过程里,文字已经消失了,代之全部都是画面。”张亚东称,虽然那些不同的情节和不同的人物跟自己没有任何交集,但是他“竟然在沈大成的书里一直看到自己,看到不为人知的、并不闪亮的那个自己”,最终他发现,“原来那些不闪亮、不被认知的时刻并不差,甚至比闪亮还要好。”孙甘露则认为,沈大成一直试图从日常世界秩序中摆脱出来,她创造平行世界并为之建立一整套规则。”那套并不存在的语汇是乌托邦式的、讽刺性的,看上去更合心意的世界包含着对人生的失望和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作家具有雄心壮志的一个体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