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可能有数百万人收看奥斯卡颁奖礼,但我却对金酸梅奖感兴趣,该奖表彰“卓著”的电影成就。我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不喜欢”可以和“喜欢”一样有趣的人。虽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对粉丝崇拜和粉丝的赞美,但也有许多内容表达着深刻的“不喜欢”。
为什么深刻的厌恶很重要?例如,为什么《多力特的奇幻冒险》或《绝对证据》是否赢得了金酸梅最差电影奖这件事很重要?几年来,我一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许多对媒体内容的厌恶是简单而短暂的。换个频道,它们就不见了。我即将出版的《生而不喜欢:媒体、观众和品味的力学》(Dislike-Minded: Media, Audiences, and the Dynamics of Taste)一书,旨在探讨何时以及为何“不喜欢”这件事会对我们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相比我们对喜欢之物倾注的关注,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同样重要、有趣和有力量。
“不喜欢”背后的势利
是的,“不喜欢”是一个值得被探讨的议题。在研究“不喜欢”的学者中,论著被引用最多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将不喜欢视为势利。更具体地说,他认为所有的品位判断,无论是肯定某物还是否定某物,都是阶级的表现。他认为,富人可以通过宣称自己有更高雅的品位来证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知道赞美哪种文学、音乐或艺术,可以向其他人表明他们在社会顶端的合法地位。
我认为,布迪厄把所有的不喜欢都看作是势利、把所有的势利都看作是基于阶级的,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了。但他也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不喜欢”往往喊出了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

与女性有关的媒体——如爱情剧或肥皂剧——可能会被讥讽为“小妞电影”(chick flick)或“鸡仔文学”(chick lit)。与有色人种有关的音乐,如说唱,仍然被斥为淫秽,而乡村音乐歌曲往往被嘲笑为听起来都差不多。如此多的“主义”通过“不喜欢”来发挥其作用。

此外,“不喜欢”常常被用作一种方式——不为脱颖而出,而是为了融入。这意味着学习应该喜欢或不喜欢什么的潜规则,并大声宣布这些喜欢或不喜欢,让别人听到。当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时,我们可能足够精明,将这些喜欢称为 “罪恶的快乐”,这既承认了规则的存在,同时也是为违反规则而道歉。
抵制无处不在的强制灌输
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不喜欢不仅仅是一种势利的形式。
我的研究助理们在几年时间里针对200多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采访,受访者在种族和性别方面相当多元,年龄从20岁到70岁不等。一些人是工人阶级,另一些来自上层阶级。然而,当他们感到自己无法逃避媒体内容时,他们都倾向于主动厌恶这些内容。
有时,直接换个频道这种事是做不到的。许多人无法选择工作场所播放的广播电台、杂货店里的播放列表、酒吧里的电视或车窗外播放的内容。而某些节目或电影也悄悄进入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想想冠名“星球大战”BB-8机器人的橙子,或“冰雪奇缘”牙膏,你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如今,人们常常谈论取消文化,但许多消费者无力取消,甚至无法逃避。因此,当人们无法忍受媒介所呈现之物时,它的无处不在就会招致批评或厌恶。

当然,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被一些讨厌的内容烦扰,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受到的烦扰比其他人更多。
一个较少被讨论的特权是控制人们看到或听到什么内容的权力。即使是对于制作人和他们的资助者想要触及的“观众类型”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例如,遥控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的父亲的专属,妇女和儿童在调台方面被赋予较少的权力。商店的播放列表通常是以中产阶级顾客的口味来选择的。有色人种仍然经常被视为小众受众,白人的喜好和兴趣被视为主流。
那些在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权力的人可能会受到更多媒介内容的烦扰和纠缠。每个人转向媒介时都希望特定的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那些较少被满足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那些更经常积极地反对的人。
以这种方式来看,谈论不喜欢是一种抵抗行为——它是一种拒绝让公共空间被与自己没有联系的广告、商品和媒体的喧闹所征服的行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喜欢这件事,就是承认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媒体都在对我们强行输出。
仇恨着观看,陶醉于厌恶
厌恶当然可以转化为愤怒或憎恨,但它也可能以一种更有趣的形式出现。许多评论家在抨击他们不喜欢的对象时,都努力追求一种腐朽的诗意。例如,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的三本书只收录了他最严厉的批评意见。家长们与我分享他们对卡尤(Caillou,加拿大儿童教育电视连续剧的主角,一个爱发牢骚的儿童角色)的不屑时,他们都在嬉笑,而非怒骂。而“仇恨式观看”,或者说观看某样东西时陶醉于你对它的鄙视,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观看方式。
为什么有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们不喜欢的对象,并一直咒骂它们,而非换台或者直接停止收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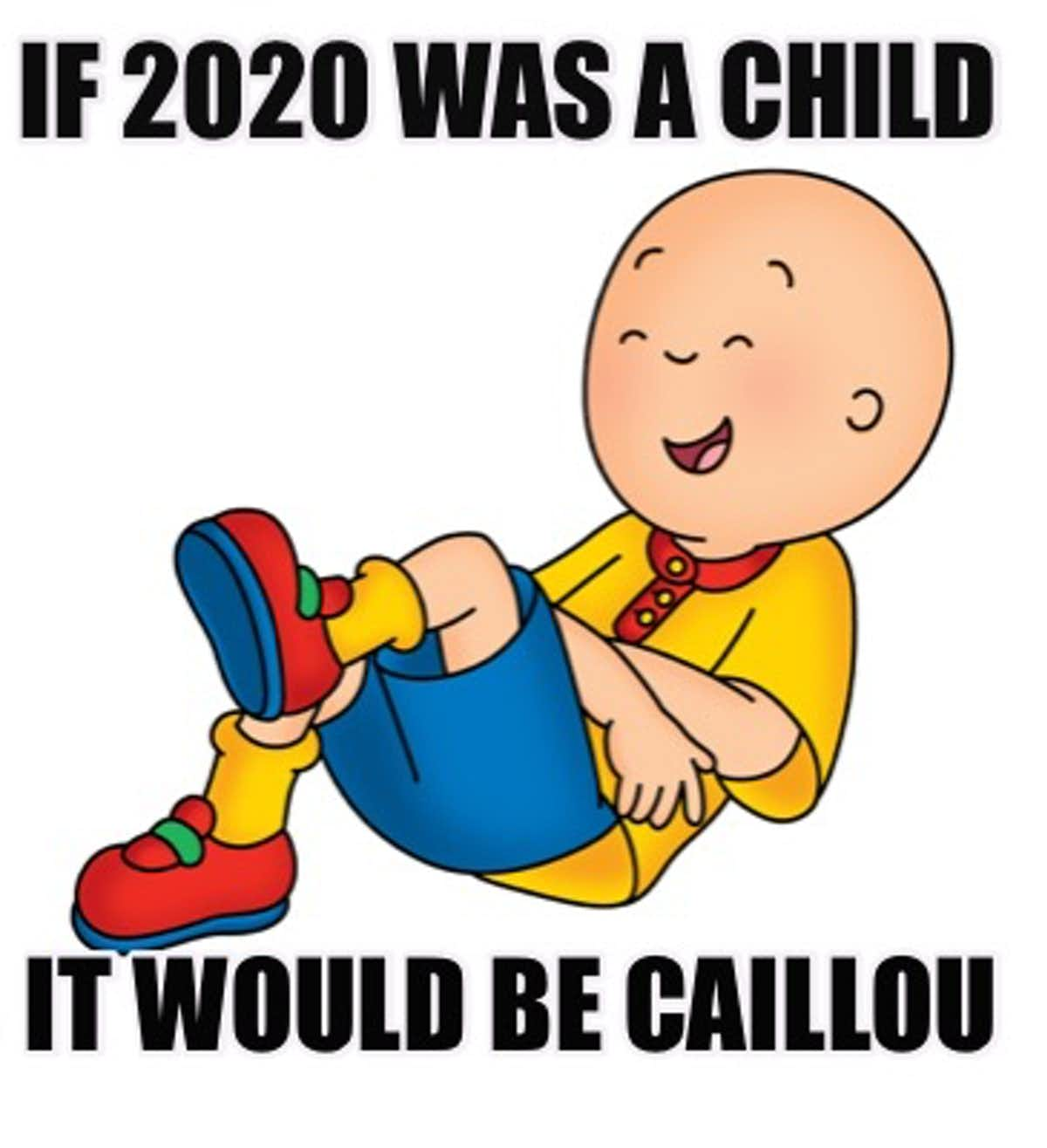
在每个人淹没于种种内容的世界里,陶醉于厌恶可以让我们重新获得控制权。对于厌恶者们而言,让他们近距离接触到他们所鄙视的节目、歌曲和电影,而非试图回避或排斥它们,能让他们成为舆论场上更好的审查官。如果流行媒体经常产生讨论,那么“仇恨式观看者”们就能更好地参与到这其中去。
或者,一些厌恶者会享受他们的不喜欢,并将其作为一种避免某些关系被腐蚀的方式。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个朋友、伙伴或家庭成员坚持要我们看一些违背我们意愿的东西。如果我们并不去讨厌这个节目或这个人,而是简单地拥抱它所有令人讨厌之处,会怎么样呢?
激昂的厌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仇恨和愤怒,它是一种独特的反应。在金酸梅奖颁奖典礼上,没有人会在颁奖台红着脸挥舞自己的拳头。
无论如何,请听从俚语的建议,“不要理会仇恨者”。但是,通过倾听“仇恨者”的意见,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文作者Jonathan Gray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媒体和文化研究教授。
(翻译:王宁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