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政治。20岁那年,聂鲁达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由此登上智利诗坛。几乎在同一时期,他作为外交官的政治生涯也步入正轨。
从1925年起,聂鲁达先是受命前往缅甸仰光担任领事,随后又在远东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旅行。几年间,他先后担任过智利驻科伦坡、雅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的领事,然而,这份工作带来的并非体面与自在,而是巨大的孤独。长期以来,他不停地变换居所,常常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海边,与此同时,他也目睹了众多殖民地地区人民因战争、贫困、疾病而陷入水深火热的残酷现实。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聂鲁达进一步深入公共领域,热切地参与到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通过发表诗文和演讲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这一时期,政治成为了他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征服者、烈士、英雄和普通人的生活出现在他的笔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聂鲁达已前往墨西哥城出任总领事,并访问了美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当时智利的外交部强令他查明移民的种族血统,不允许非洲人、亚洲人和犹太人进入,这让他彻底厌倦了领事的工作。在他看来,“某些南美洲国家本身便是多重杂交和混血的产物,而他们荒谬的‘种族主义’要求却是殖民主义者的遗毒。”在辞去职务、返回智利前,聂鲁达登上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从高处看见了苍翠的安第斯山群峰围绕的古代石头建筑。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某个遥远的年代,我的双手曾在那里劳动过——开垄沟,磨光岩石。”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组诗《马丘比丘之巅》。
1945年,聂鲁达被选为国会议员,同年,他加入智利共产党,但不久便因政治迫害流亡国外。他的诗集《漫歌》就创作于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全书共分为15章,以雄浑的手笔描绘了美洲大陆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组诗《马丘比丘之巅》也被收录其中。在某种意义上,《漫歌》可以视为聂鲁达对自己前半生的一次总结,诗人不仅记录历史,还将对历史的审视与个人的史诗交织在一起。全书从描绘欧洲殖民者未到达新大陆之前,美洲大地的和平与宁静开始写起,叙述了300年来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屠杀和掠夺的苦难史,并一路延伸到作者在流亡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作为诗人的责任。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言:“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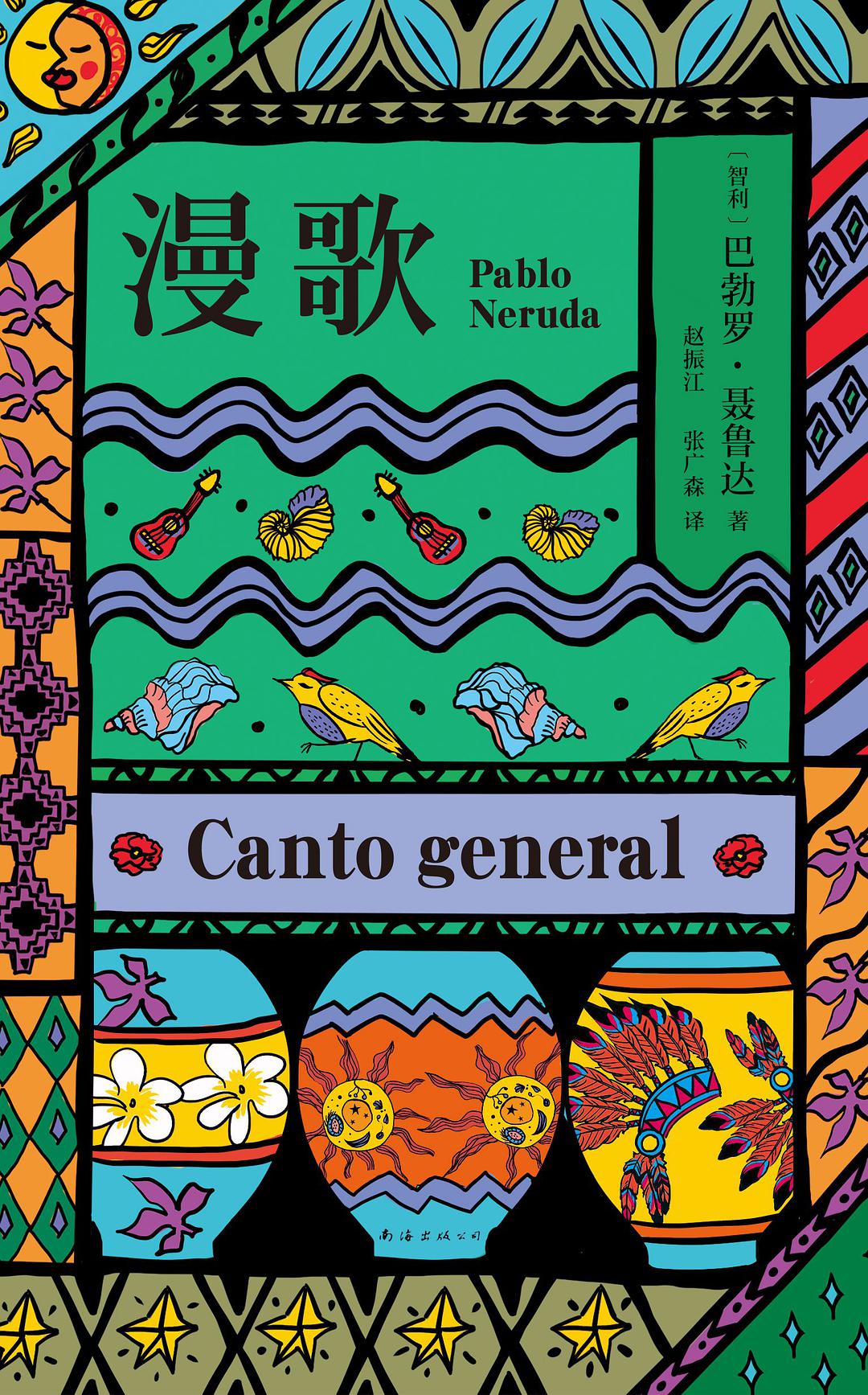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著 赵振江 张广森 译
新经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 2021-06
兽类
那是鬣蜥的黄昏。

它的舌头像投枪一样
从彩虹般的棘状鳞
向绿色挺进,
蚂蚁修士迈着和谐的步履
走过森林,
小巧的羊驼仿佛氧气,
穿着金靴
在褐色宽广的山间走动,
骆马在洒满
露珠的精美世界中
睁开了天真的眼睛。
猴子们在黎明的岸边
编织着一条
永无休止的情爱之线,
将花粉的墙壁推翻,
将穆索蝶群紫色的飞翔惊散。
那是鳄鱼的夜晚,繁衍的夜晚,
长长的嘴巴伸出泥潭,
隐隐约约的甲胄声
又从梦幻般的沼泽
返回大地的根源。
美洲豹用忽隐忽现的磷光
将树叶晃摇,
美洲狮宛似吞噬一切的火
在枝条间奔跑
而森林沉醉的眼睛
在它身上燃烧。
欧亚獾搔着河流的脚,
嗅着寻找洞穴,用红色的牙齿
攻击那里诱人的美味。
在广阔的水底,
巨大的水蛇
宛似大地上的圆环
身披庆典的泥土
笃信宗教而又凶狠贪婪。
危地马拉
甜蜜的危地马拉,
你首府的每一块石板
都染着被老虎
吞噬的古老的鲜血。
阿尔瓦拉多摧毁了你的家族,
捣碎了你星星的尾光,
在你的苦难中为所欲为。
在白皮肤的老虎后面
一位主教来到了尤卡坦。
他汇集了世界开创之日
人们在空中
听到的最深刻的学问,
那时第一位玛雅人
记载了河流的战栗,
花粉的奥秘,
万物之神们的愤怒,
穿越原始宇宙的迁移,
蜂巢的规律,
绿色飞禽的奥妙,
星星的语言,
在大地发展的岸边
收集到的关于
昼与夜的秘密。
智利的发现者们
阿尔马格罗从北方带来微弱的火光。
在夕阳与爆炸声中,他夜以继日地
俯身在这片领土,宛似在一幅地图上。
荆棘的影子,蓟草与蜂蜡的影子,
这位西班牙人紧贴着它们干枯的形象,
将这土地上阴森的战略观望。
黑夜、白雪和黄沙
造就了我的祖国瘦长的形状,
所有的浪花都从它海洋的胡须中涌出,
所有的煤炭都使它充满神秘的亲吻,
所有的寂静都在它漫长的国境线上。
黄金像一块炭火燃烧在它的指间,
白银照耀着阴森星球上坚硬的轮廓
宛似一轮绿色的月亮。
有一天这位西班牙人坐在玫瑰花旁,
身边是油、葡萄酒和古老的天空,
他无法想象这遍布愤怒岩石的地方
是在海鹰的粪便下诞生。
广场上的死者
(智利,圣地亚哥,1946年1月28日)
我来到他们倒下的地方不是为了哭泣:
我是来找你们,来找活着的人。
我找你,找我,并拍打你的胸膛。
从前曾有其他人倒下。你记得吗?
是的,你记得。他们的姓名都一样。
在圣格雷戈里奥,在多雨的龙吉梅,
在朗吉尔,他们被风吹得四处飘荡,
在伊基克,他们被黄沙埋葬,
冒着烟雾,冒着雨水,
沿着大海,沿着沙荒,
从草原到群岛,
其他的人同样被杀戮,
他们叫安东尼奥,像你一样,
像你一样,同样是渔民或铁匠:
智利的肌体,被风刺伤,
被草原折磨,被苦难签了字的脸庞。
在祖国的墙壁上,
在积雪和它的结晶旁,
在绿枝的河流后面,
在硝石和麦穗的下方,
我找到了我的人民的血滴,
每一滴都在燃烧,像火一样。
( 注:是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布尔内斯广场,发生了枪杀游行群众的事件,六人当场死亡。 )
黄金
黄金曾经有过纯洁的日子。
在它的形体重新投入
等待着它的肮脏出口之前:
刚刚成形,刚刚脱离
大地庄严的身躯,
经过火的提纯,
被人的汗水和双手包裹。
从此人民告别了黄金。
那时候,他们的触碰还很质朴,
纯洁得就像祖母绿成形前的灰色璞玉。
那捡拾起未经打磨的金锭的
汗漉漉的手,
好似被无限的时光
浓缩了的泥土中的根茎,
好似土地颜色的种子,
好似蕴含奥秘的强劲土壤,
好似结葡萄的大地。
未受玷污的黄金的土地,
仁厚的材料,属于人民的
纯洁金属,无瑕的矿物,
互相接触,互相无视,处于
不可回避的岔路口上:
人将继续啃凿沙尘,
大地仍是含石的泥土,
而黄金却将借助人的鲜血浮升
直至残害并统治受了伤的人。
诗人
从前,我在痛苦的爱情中
为生活奔波,
从前,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活
为自己保留了一小片水晶。
我购买过仁慈,
我到过贪欲的市场,
我呼吸过最为无情的妒忌之水,
面具与人之间残忍的敌对。
我曾在海滨泥潭般的世界中生活过,
在那里,鲜花——百合花会突然间
像泡沫一样颤抖着将我吞噬,
而在我的双足点到之处
心都会滑向深渊的利齿。
就这样,我的诗歌诞生了,
勉强从荨麻丛中挣脱,
仿佛是对孤独的惩戒,
或是在下流无耻的花园中
摘取最隐秘的花朵,直至将其埋葬。
就这样,好似奔泻于深渠之中
暗藏的河流,我孤独地
辗转于一只只手掌,辗转于人们的孤独之中,
辗转于日常的仇恨之间。
我知道半数的生灵就是这样
躲躲藏藏地活着,犹如
最为偏远的海洋中的鱼群,
而在无边的泥潭里我遇上了死神。
破门开路的死神。
过隙穿墙的死神。
我记起大海
智利人啊,最近你可曾去过大海?
以我的名义去吧,沾湿你的双手,然后举起来,
而我将在异国的土地上朝拜
无尽的海水点点滴滴地洒落到你的脸上。
我在属于我的整个海边生活过,
熟悉北方、荒原的辽阔海面,
还有海岛上的浪花激荡的分量。
我记起大海,记起科金博那崎岖、钢铁般的岩岸,
记起特拉尔卡那汹涌的波涛,
记起养育了我的南方那孤寂的浪花。
记起,在蒙特港或岛屿上,
夜晚回到海滩守候的船舶,
而我们的双脚在串串的脚印中留下火焰,
那是磷火之神的神秘光焰。
每迈一步就洒下一摊白磷。
我们用星辰在大地上书写。
而在海里,船舶滑动着,摇晃
海洋之火的枝条,那是集群的萤火虫,
就好像刚刚睁开眼
复又在深渊中沉睡的一朵无尽的浪花。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 《漫歌》 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