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栏目“编辑部聊天室”。每个周日,界面文化为大家揭晓一次编辑部聊天记录。独自写稿,不如聊天。我们将围绕当周聊天室主持人选定的话题展开笔谈,或严肃,或娱乐,神侃间云游四方。鉴于主持人们各有所好,聊天室话题可能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和社会热点事件,也可能从一口路边小吃、一次夜游散步、一场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开去。
本期聊天室由子人主持,她选定的“一星运动”主题,实际上相关讨论已有段时日。在最宽泛意义上来讲,这个现象的出现源自许多人完全绕开了书影音评论原本的意义——就作品本身给出自己的中肯评价,为其他网友提供参考意见——将之作为实现其他诉求的武器,比如粉丝为了给偶像刷好评养号、抵制某位“争议性”的创作者……
不过这个现象倒也不止发生在中文互联网内,而是“全球同此凉热”。据《时代》(Time)报道,全球最大的图书评分网站Goodreads目前也陷入了“一星水军”(one-star brigades)的威胁。一些作家遭遇网络敲诈,如不支付“封口费”,他们的作品评分就会被成百上千的恶评拉低。报道指出,最容易遭到攻击的往往是新人作家、有色人种作家和在公开场合评论争议性社会事件的年轻作家。
由于Goodreads未能对此引起重视及时干预,特别是该网站在注册时无需验证邮箱让炮制马甲账号变得非常容易,“一星运动”已造成了一些恶劣影响,最脆弱、最容易被噤声的也恰恰是上述这些缺乏资源和行业影响力的作家。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oodreads之类的评分网站已经成为某种“必要之恶”——它已经是图书营销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工具,在每年出版众多新书的情况下帮助读者找到质量上乘的作品,可是水军操纵评分的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此类网站的初衷。将网络上成批量出现恶意差评的现象称为“一星运动”,是因为它往往是一种高度协调性的集体行动。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一星运动”的起源:群体智慧与道德制裁的张力

林子人:作为一位爱读书的人和豆瓣重度用户,我对恶意打差评的现象(其实无脑刷好评也是)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绝,因为它严重违反了评分机制的“神圣契约”,即只有真实不违心的意见才对他人有价值。但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明确,打分机制为什么会被广泛应用。
以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构建的网络评分体系存在的前提,是相信“群众的智慧”。2004年《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畅销书《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首次让这个概念引起人们关注,随后,心理学家做了大量实验。法国心理学家迈赫迪·穆萨伊德(Mehdi Moussaïd)在做了十多个估值测试类实验后发现,无论是让参与者猜测纪念碑有多高还是一个公园的面积有多大,只要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答案的平均值总是能够接近真实答案,哪怕实验中许多个体的答案错得离谱。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1999年微软游戏平台玩家集体挑战俄罗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在那场比赛中,来自75个国家的超过5万名棋手上场(既有业余棋迷也有专业棋手),他们的表现与棋王卡斯帕罗夫不相上下,甚至有时能走出超乎预料的奇招。最后,卡斯帕罗夫走出了64步,仅余三子,才艰难地赢得了比赛。
然而穆萨伊德指出,强大的群体智慧建立在多样性的前提之下,但这个前提恰恰是非常脆弱的。脆弱性的其中一个成因是社交网络中的社交影响力。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小小的暗示就能让大众判断的平均结果偏离正确答案。比如我之前在一篇讲述网络极化的稿件中提到的例子,最早的评论调性(无论是好是坏)会影响后续网友对一篇文章的观感。在评分体系已经被广泛应用(从书籍电影到餐厅酒店)的当下,我们要如何看待它的有效性呢?在有人利用这个体系去实现其他诉求时,平台有能力或者有权利阻止吗?我对此其实没有确定的答案,我甚至有种悲观的感觉,就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判断力,才能抵御恶意差评或无脑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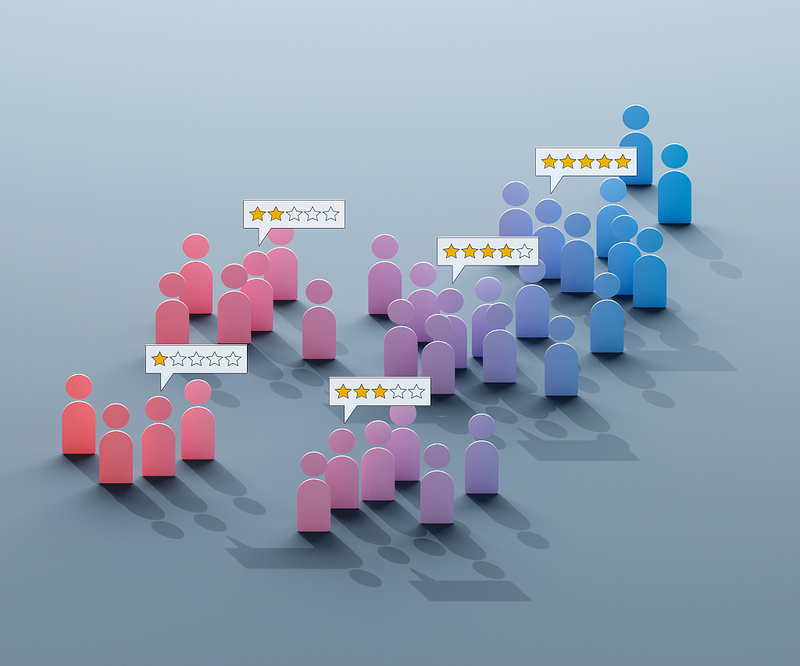
姜妍:关于一星运动,我印象中可以追溯到的“鼻祖”是2013年初在豆瓣上由网友们发起的对李继宏译作的“制裁”。引起网友不满的原因是当时由果麦重新出版的由李继宏翻译的包括《小王子》《老人与海》等在内的一系列名著的宣传语——“纠正现存其他56个《小王子》译本的200多处硬伤、错误,纠正现存其他50个《老人与海》版本的1000多个错误……”于是,另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图书编辑在网络上号召“豆瓣第一次1星运动就从这里开始吧”。随后,这个系列的李译本的得分一度被压低到只有2-3分。李继宏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错误是图书编辑经过比对找出的,比如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里的所有动植物都是错误的,傅惟慈译本中的《月亮和六便士》对可颂的翻译是“月牙形的面包”。
我想这个宣传文案多少是有夸张之处,才会让出版业同行感到极度不适,另外一方面,李继宏译本的《小王子》在市场上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版本。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比如说我们业内人定义一本书的好,和大多数读者定义一本书的好,很多时候是存在偏差的。就像一位作家朋友提起台北市图书馆前一年借阅率最高的五本书中有四本都是东野圭吾的作品时连连摇头。
最早的这次“一星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会认为自己认可的说是“价值观”也好“美学”也好,甚至可能是道德层面的洁癖部分受到了冒犯,于是进行了“反击”。这种“反击”多少形成了某种跨界,可能这本来是一本不管评分高低你都根本不会去看的书,甚至在你点击一星的时候,一样也不会去看的书。我能理解对某个人、某件事、某个行为的厌恶,但是厌恶是不是就要用“一星运动”的方式去进行一种“网络封杀”,这个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内容。
潘文捷:作为曾经参加过一星运动的人进行发言。读了子人多篇关于反智、民粹包括关于网络极化的文章,现在思想终于有了一定的觉悟,格局得到了提升。在这个情况下回想当年,那时候没有说觉得自己是在恶意评分或者灌水,而会觉得自己师出有名,甚至还挺快乐。这个“师出有名”很多时候是认为作者道德有亏,这样来用评分给作者进行“制裁”,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而且参加的时候,你会觉得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种同仇敌忾的氛围里可以说是寻找到一种归属感吧。可以说,很多没有别的表达意见空间的人,在“一星运动”里找到了成为主角的机会。
“一星运动”对我来说特别说不过去的就是——可不可以没看过一个作品就去评论它?一开始我认为不可以,所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去看了某作者的大部分作品,过程是折磨的,结局是后悔的。于是我意识到,很可能不少会给某个作品打一星的人一开始就不是该作品的目标受众。而且我不止一次遇到过在正常的打分情况下,分数和我个人阅读感受全然不同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很难判断网站评分对自己究竟有多适配。还是听听周围的人在读什么看什么,可能会更适合自己一点。
写差评的自由:过于在乎他人的评价,在让我们丧失判断力
董子琪:还记得大学里有次好朋友跟我推荐一本新书,说特别文艺,你一定会很喜欢!那时候已经放暑假在家,专门在市里唯一够文艺的书店找到了买来看,结果读完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同时怀疑起在朋友眼里我的阅读喜好到底是啥,但为了不破坏感情也不要影响我的“批判思路”,我选择了自己写长差评。二十岁写东西,难免气势汹汹又非常自信,标题是“《素年锦时》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它的封面和名字”。谁想到写完,被推上博客首页(这个倒霉博客现在已经倒闭了,所有的文章都找不到了),引来了很多作者的粉丝发表不同意见,跟我经常在博客互相踩踩的好友当然也看到了,在下面留言说,如果觉得推荐不好,为什么不直接说呢,那么信任我的文学“品位”,私下可以交流的事却在在网上写差评。
我也想,为什么呢?好像成了借他人推荐显自己高明的自大狂,可是不也是兴趣来了就想批评一下,难道不可以吗?我希望保有自己的判断,而这种评价如果不那么“社交网络”就更好了。现在不也是这样吗?我猜啊,打分有点像社交宣誓,向友邻宣誓读了什么书,对什么有心得,打星也有点暗暗比拼的意思,打分更低的人感觉赢面更大一些,毕竟更有一点品位的保留,打一星更是“爱憎分明”、“明辨是非”了,可是为什么要和友邻比赛呢?倒宁愿把所有读书有关的状态相关都关掉,就像永远不开社交运动比拼步数一样。
陈佳靖: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吐槽他在网购时的糟糕体验,大意是说,很多商家为了卖商品都会故意去雇人刷销量和好评,导致他在选购的时候没办法分辨商品的质量优劣。最开始商家只是刷销量或者评分这种数字上的指标,他或许还可以通过顾客的真实评论看出端倪,但现在连评论都有很大比例是刷出来的,而且久而久之,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网购的潜规则——你要想先挑再买,就得拿出做语文阅读理解的精神,从蛛丝马迹里辨别真伪。
有人可能会说,商业的逻辑不应该用在书影音的评价上,因为书影音是作品,应该尽量客观地评价其内容。就像子人举的心理学实验的例子,如果大家都是背靠背,在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下(最好还是同一时间)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才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但实际情况总是没有那么理想,无论是“一星运动”还是“五星运动”,背后都有某种明显的干扰因素在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是这项“实验”会产生难以预计的误差。这些干扰因素可能包括粉丝对某明星的崇拜、读者对某作者的抵制、营销公司具有导向性的刷评等等,很难一概而论怎样是可以的,怎样是不行的。但既然是“运动”,它多少意味着短时间内某种倾向的集中聚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实验人员,在我的统计数据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会很谨慎地去考虑是否还可以采纳它。

叶青:和佳靖的朋友一样,我以前常常是听信了点评的分数,去了某家餐厅,或看了某部电影,发现自己吃的、看的仿佛和评分里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豆瓣、大众点评这类点评类软件的评分,其参考价值似乎越来越不靠谱了。
影响评分可信度的有子人提到的恶意差评,也有佳靖提到的水军好评——而且他们的套路越来越防不胜防了。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线下的观影团,一般是在豆瓣邀请你——通常对豆瓣观影标记量有一定的要求,我猜是为了避开豆瓣的反水军机制——免费提前观影,而你需要在看完电影后打分回馈。虽说这些观影团不会强迫参与者一定要给满分好评,但组织者往往会在现场进行语言上的诱导,以及制定类似“给好评者下次中奖率更高”等规定。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刷分行为吗?对很多人来说,打个分就可以免费看电影,似乎是一件无伤大雅的划算事。可我们作为只想查个分参考一下的用户,现在却还要睁大眼睛辨清真伪,这未免也太累了。
让评分失去了本该有的参考价值,这些刷分行为固然令人讨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过于依赖评分了?读书、看电影一定要8分以上的,吃东西一定要吃“必吃榜”里的。也许我们的这种“一切都要是最好的”的心态,也是让刷分行为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赵蕴娴: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何评价文艺作品是件很私人的事情。你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它好或者不好,也可以任性地只说一句“我喜欢”、“我不喜欢”,一个人是否会因为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而讨厌周作人,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一个作家英勇就义而格外看好他的作品,因为一个作家失了节气而对他的东西产生厌恶,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对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无非泄露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但发展为“运动”的评分就是我所不理解甚至讨厌的。不论运动的目标崇高还是卑鄙,正义还是非正义,其手段的粗暴本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从历次运动的结果来看,即便一开始是普通人的“抗暴”和“揭竿而起”,到最后都难免沦为又一次暴力事件,前段时间《休战》引发的豆瓣“一星运动”即是如此。
我偶尔会想,有这么多“一星”和“五星”运动把情绪演绎到极致,喧闹不已,可惜连爱恨都是空心的,没有足够的精神和底气喊出一句“我就是喜欢\不喜欢,你管我”,看来人有时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喜好取向。
“一星运动”与“取消文化”:就事论事不仅是对人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大环境的要求
陈佳靖:文捷提到的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制裁”别人的情况,我个人是很不能接受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评价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它背后可能涉及很多人的贡献。比如,因为讨厌一个演员而去给TA的所有作品打一星时,是不是也伤害了作品里其他演员的利益?即使是某作家独自撰写的书,它的出版也涵盖了编辑、设计师等其他人的参与,如果说在道德上讨厌一个作家就可以打一星抵制他,这对于其他因此受牵连的人是不是不公平?
赵蕴娴:书影音评分,最初的设想大概是“就事论事”,“就作品谈作品”,但我认为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不存在,即使抛开豆瓣这类网站来说,情况依旧如此。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向来不只在艺术这一个标尺上进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它在自身脉络中的历史位置、创作者的政治立场、私人德行,通通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受众打分的因素,究竟哪个因素占大头,或许与更大的时代环境有关。从《包法利夫人》被打成“三观不正”的出轨文学,到最近一次的豆瓣“一星运动”,其实都很容易看出是什么样的标准在修整大脑和生活。以前我比较乐观,相信在时间的冲刷下,这些浩浩荡荡的运动终将会被压平为薄薄的一层,我也很好奇,数据将如何留存这些痕迹,后人又如何评述,但最近变得没这么乐观了。
黄月:在2021年的今天,当“一星运动”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旋风刮到一起,事情似乎变得更难说清楚了。不仅仅是读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作家或名流的不正确话语、不得体(甚至违法)行为为其作品打一星,连文艺文化圈内部也出现了各种抱团的反对、抵抗、战斗,去年《哈泼斯》杂志公开信之后我们也都已见识过结成阵营、互相批判的阵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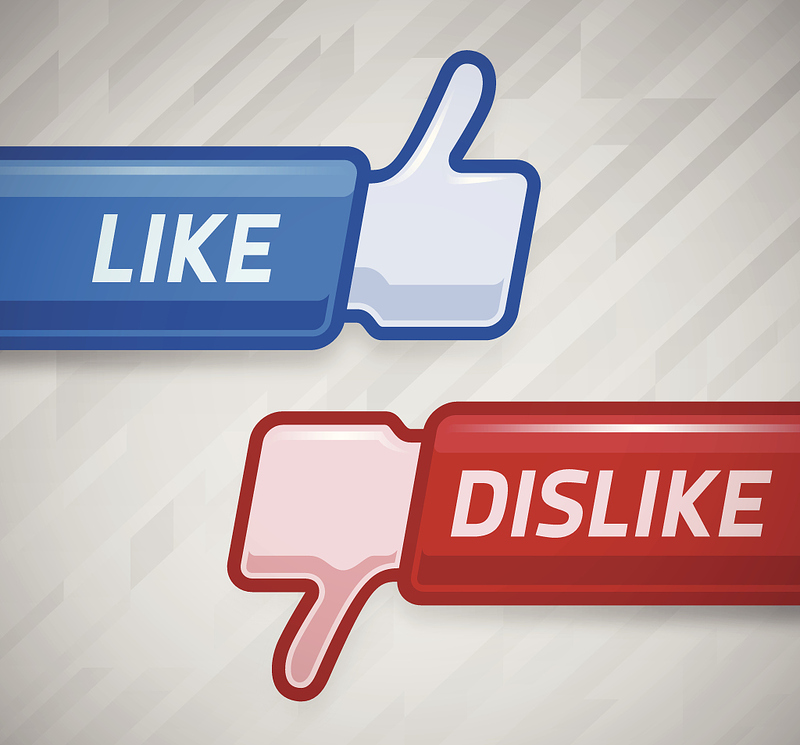
打个比方,以J.K·罗琳为例,如果说她在跨性别的议题上表态有问题,相当不正确,那么是否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就应该被一星呢?在吴珊卓出演的最新美剧《英文系主任》(The Chair)里,一位英文系教授在课上讲到梅尔维尔与霍桑的通信,学生问的却是:“梅尔维尔不是家暴狂吗?”该怎么办?通过给梅尔维尔的《白鲸》打一星来鲜明反对家暴?将梅尔维尔开除出美国文学史?大学教材在梅尔维尔的章节之后注明“反对家暴,此处我们仅探讨他的文学”?这当然还是作品与人品能否分开看的老问题,就事论事也许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更大的文化、法律和政治环境的要求。
今年6月,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在她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题为《这是败坏的》(It Is Obscene)的文章,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社交媒体和取消文化或许有所启发:
“社交媒体上的这代年轻人对持有不同意见是如此恐惧,以至于自己动手夺走了自己思考、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曾经对一些告诉我他们不敢发推的年轻人说,他们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审读自己的推文,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话可能会招来各种攻击。善良意愿(good faith)的预设已经死了。重要的不是善良本身,而是摆出善良的样子。我们不再是人类了。我们现在成了天使,整天盘算着如何把别人排挤出天使的行列。愿上帝保佑我们。这是败坏的。”
姜妍:在作家唐诺的新书《声誉》讨论民主的篇章中,他引用了英国阿克顿爵士的历史名言——“你讲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保证你讲话的权利。”唐诺写道:
“这揭示着一道‘思想/言论’自由的极生动底线,也透露出我们对一个多样化世界的必要护卫暨其期待,即便这个多样化世界时时具体地冒犯到我们,让我们极不舒服。根本上来说,多样化世界对个人来说往往不是真正的目标,这里有着人高度节制的不得已成分,来自于人足够丰硕的历史经验,简单说,个人寻求的是玉而不是石头,只是玉来自于石头。”
当然,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实践,以及面对当前世界的种种实况,唐诺没忘记在之后加上一句,他更喜欢作家比尔·布莱森的改写——“你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下去,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保证你有当个十足混蛋的权利。”
【互动】对于“一星运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有什么话题是你想听编辑部一起聊聊的?欢迎给我们留言。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