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期主持人 | 陈佳靖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栏目“编辑部聊天室”。每个周日,界面文化为大家揭晓一次编辑部聊天记录。独自写稿,不如聊天。我们将围绕当周聊天室主持人选定的话题展开笔谈,或严肃,或娱乐,神侃间云游四方。鉴于主持人们各有所好,聊天室话题可能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和社会热点事件,也可能从一口路边小吃、一次夜游散步、一场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开去。
本期聊天室由佳靖主持,她想要讨论的话题是“精神卫生”。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在人们常规的观念中,良好的精神卫生(也称心理卫生)状况就是没有精神疾病,实际上,这并不是精神卫生的全部定义。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羸弱,而是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关注精神卫生,意味着我们应当超出精神疾病的范畴去考虑整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在理想状态中,个人应当能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能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为社会作出贡献。
如今,预防疾病、强身健体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但心理健康却时常被忽视。与躯体上明显的病痛相比,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也更加隐蔽。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社会的迅速变化、工作压力大、性别歧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而一旦人的心理陷入反常状态,患上精神障碍或精神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就会受到破坏,以致于无法进行正常的家庭和社会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精神障碍患者中年轻群体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世界上约有20%的儿童和青少年有心理健康问题,而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柳叶刀》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包括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等,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是患者抗拒治疗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天然地将精神疾病患者视为“疯子”,在社会生活上排斥他们,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身心负担,延误病情。事实上,个体的精神卫生状况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如何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真正从日常生活中重视心理健康、预防精神疾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考虑的。
年轻人的焦虑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惶惑
陈佳靖:从世卫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目前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不断上升,而15-29岁人群受影响十分明显。可以想象,这个年龄层的群体正处于升学、就业、婚恋等压力的高峰期,很多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烦恼接踵而来,一旦不能调节好心理状态,得不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积极引导,很可能会持续陷入焦虑情绪,进而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障碍。
很多研究也指出,如今的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大家对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开始意识到主动治疗的重要性了,另一方面也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过去古人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像是某种不变的规律,但对于现代人而言这已成为一种奢侈。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我们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白天做不完的工作留到晚上做,晚上本应用来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又从睡眠里挪用,最后“黑白颠倒”成了常态。事实上,今年美国就有一项新研究指出,昼夜偏好是抑郁症的潜在风险因素,如果一个通常在凌晨1点左右睡觉的人改在凌晨前睡觉,睡同样的时间,他可以降低23%的患病风险。
林子人:佳靖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让我想到《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的话:“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现在供人休息和恢复精力的时间实在太昂贵了,以至于从结构性的意义上说,它们不可能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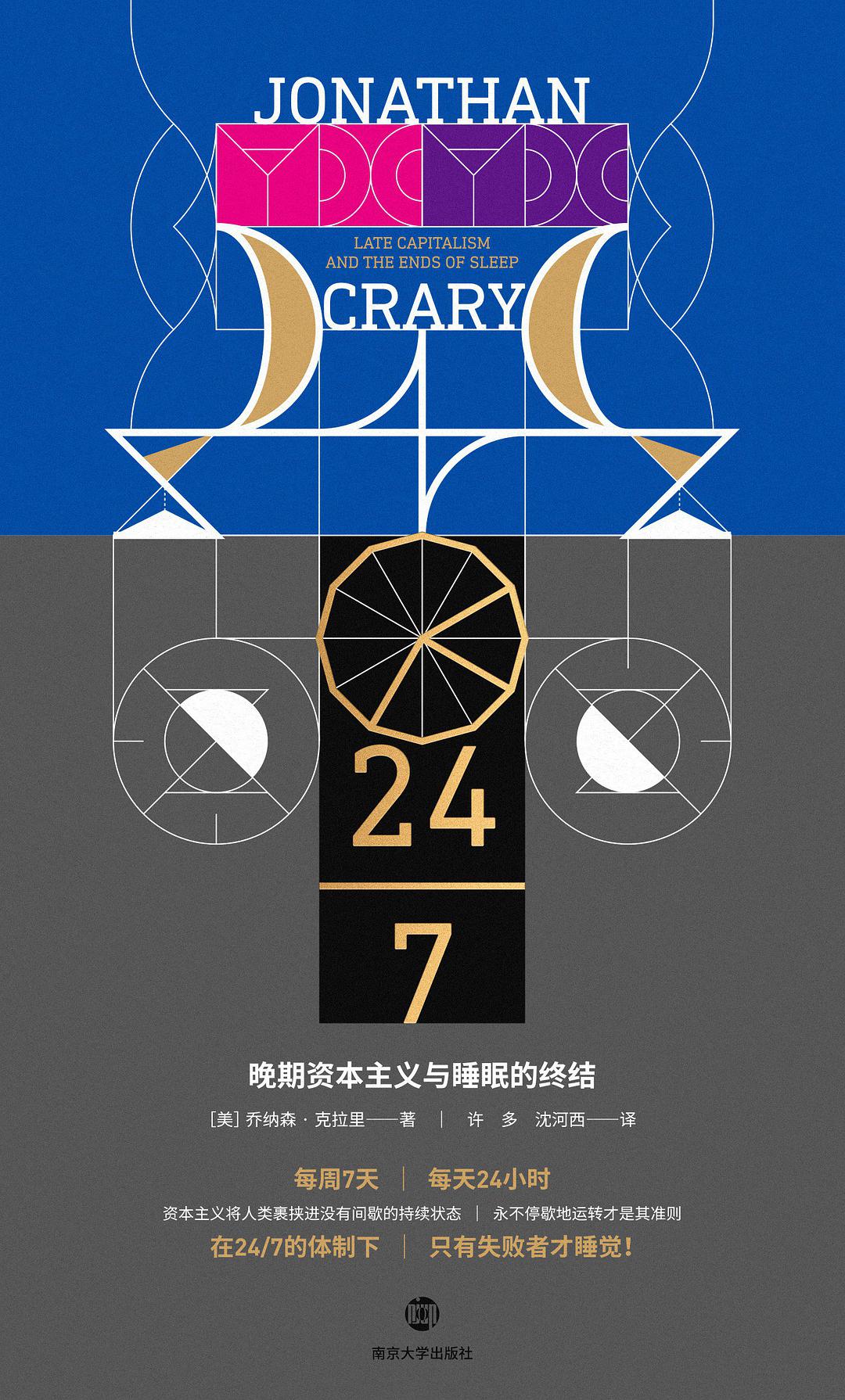
[美] 乔纳森·克拉里 著 许多 / 沈河西 译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05
在我看来,年轻人的焦虑归根结底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惶惑:长久以来我们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价值观正在被颠覆,劳动回报率远远小于资本回报率,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雇主与员工共同进退的社会契约被打破,我们发现雇主越来越将员工视作负累而非资产,动辄以“削减成本”的理由优先抛弃员工,这让“低性价比”工作者(身体素质不佳、年龄偏大、或需要生育的女性)的职业前景岌岌可危,也将更激烈的竞争和重重压力强加给职场幸存者;鉴于职业和收入是决定当代人生存和身份认同的最重要因素,公共生活的紧张状态也会影响到私人生活,特别是在社会以企业为中心、不承认“人的再生产”的价值及其所需的成本的情况下;而“适者生存”“自我担责”的意识形态又在不断规训我们苛责自己……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很难不焦虑吧。
董子琪:我想通过年轻人参与最多分布最广的社交网络来把焦虑具体化。有阵会喜欢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做“网络民族志调查”,就是看知乎的高赞问答,虎扑的步行街问答,最近也观察了一下据说最富裕的小红书,选择这些地方是因为我想知道比我年轻的、与我不太一样的、生活中甚至没有交集的人,是如何讨论问题的,会有什么新鲜术语迸发出来。
这个“偷师”的过程当然是很浪费时间的,在不断地重复刷帖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虽然担心的问题不同——比方说知乎担心的可能是年薪百万无法留在一线城市,小红书焦虑的是老公失业了我还能不能继续全职,虎扑步行街可能是家里资产一千万什么水平——但问题的角度往往都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的,其中通常涉及一些代际冲突,包括70后是不是占据了社会的红利,老人有房子是房东、年轻人一无所有给房东打工值得吗这样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指向也相当趋同,那就是我如何衡量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时候金钱的指标是最通用的。存款、资产、公积金,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大家要一项项地掰开看,对照胡润榜看自己是否能属于城市的百分之十。
在浪费时间的同时,我告诉自己,之所以“学习”这些,是为了占据更多的社会调查资料,了解不同人群的生活,从金钱指标攀比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风向标。这些提问是不是特别势利、市井、物质主义,但人们真的是欲壑难填吗?还是说对物质的在乎有着精神的诱因?想起前阵阎云翔所说的,在当下中国,连接家和国的是物质主义:私领域中通过消费主义实现家庭的梦想和幸福非常重要;物质主义也能将个体划入不同的阶层,帮助人们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通过拥有多少财富,住在什么地方,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的方式,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逛熟了中国当下主要的网络社区,会对这段话非常认同。
接续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物质主义能够连接家与国,或许能让人们短暂地感到焦虑缓解,因为人天然需要感知到自己的位置,但这种单一追求赋予的身份认同,最终是充满焦虑的。用事实来说话,上海本地论坛宽带山上站在胡润排行榜上海前百分之十里的人,发明出了一个术语叫“哭穷划胖法”,这个意思就是用哭穷的方式炫耀,现在也越来越多在知乎和小红书上看到。如果说人们寻求身份认同的目的是没错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难点又在哪儿呢?
一个人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开口寻求帮助
潘文捷:好像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并且会成为当地的一句俗语,吵架时就可以骂对方“你是不是x院刚跑出来的”!今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月饼还成为了网红,因为谐音“精神病”。可以看到,辱骂对方有心理疾病至今还是很有杀伤力的举动,这也成为很多人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的原因。中学班上一位同学,成绩永远前三但是私下里每次考试前都会紧张到呕吐。我劝说她去看学校里的心理医生,她想去又不愿意去。于是我本着好奇心加上助人为乐就先去了一下,并且转告她里面的情况,就是聊聊天医生给你做点笔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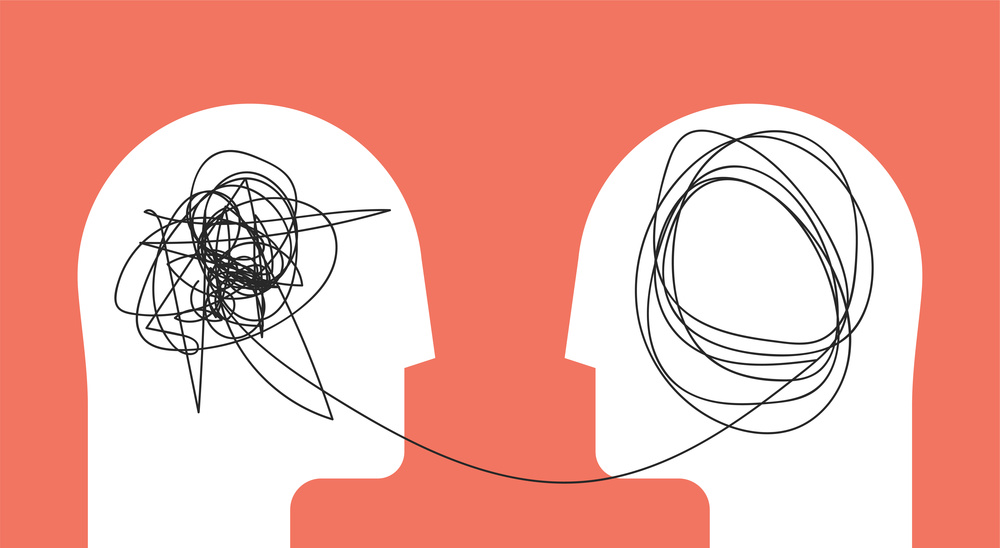
我是不会看气氛的人,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污名化一件事,我都觉得无所谓。但是很多人会在意这些。在《纽约时报》2011年一篇对韩国抑郁症的报道里,朝鲜大学教授、心理学家Kim Hyong-soo就说:“如果感到抑郁,韩国人就默默忍受,等它过去,因为那些去看精神科的人会感受到一辈子的羞辱。”那些寻求心理咨询的人经常去私人诊所,甚至以现金支付,这样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社保上就不会显示这些记录。在这种背景下,后来韩剧出现了一波浪潮,2014年的《没关系是爱情啊》,2020年的《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2020年的《恶之花》等都以精神疾病为主题,帮助改变了一些社会上的偏见。
除了影视作品可以帮助改变以外,更多的阅读也会让人们理解精神疾病。之前看了《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产后精神疾病康复者的自白》,讲述在现实中,10个新手妈妈中就有8个会在产后几周内经历痛苦的挣扎。得产后抑郁症乃至产后精神病的大有人在,但是人们却似乎很少公开讨论这些事。好在作者的丈夫和家人自始至终都坚定地陪伴着她,她也及时获得了来自专业医生的救助。医生告诉她,得产后抑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运气不好。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而作者本人的感悟则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开口寻求帮助。国庆期间还读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讲述心理治疗师诊室里发生的故事。给别人当治疗师的医生本人和男友分手之后几乎崩溃,也给自己找了一位治疗师。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她逐渐发现在痛惜分手的表象之下,内心深处让她恐惧的真正事物。如果想要解决问题,不发现问题、承认问题的存在怎么行呢?听听这些病人和专家的呼吁!“开口寻求帮助”、“你该找个人聊聊”,所以从你我做起,鼓励你周围有担忧的朋友勇敢地去寻求帮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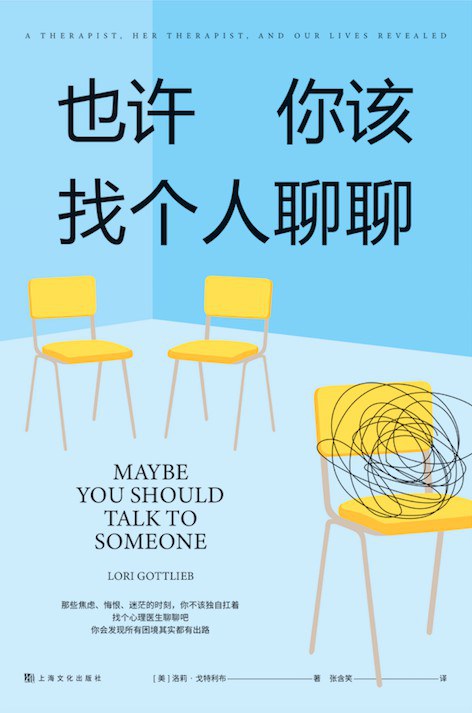
[美]洛莉·戈特利布 著 张含笑 译
果麦文化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07
叶青:不管从数据还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看,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确实不少。2019-2020年的时候我得过抑郁症,也陪好友去文捷说的“每个城市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看过,还在那里遇到了也是来看病的学弟。怎么身边这么多人有精神问题,难道真的是人以群分吗?那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想通了:因为这是一件很正常、普遍的事情,我们只是生病了,就像每个人都有可能感冒发烧一样。
陈佳靖:世卫有一项数据的对比:抑郁症和焦虑症这两种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1万亿美元的损失,尽管如此,全球政府用于心理健康的医疗支出中位数仍不到2%。在中国,除了高发病率、低就诊率的现状之外,当前精神科医生的缺乏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地区诊疗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个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了解相关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预防精神疾病,如有不适就及时去医院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采取相应治疗手段。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当出行和人际交往受限,生活中充斥着疾病与死亡的信息时,保持健康的心态本身就成为抵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赵蕴娴:我对“精神卫生”、“精神疾病”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有时候想再学习一下,但总是越看越糊涂,有一次抱着请教的心态去采访一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没聊几句就被震住了,她让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比如分不清什么叫问题什么叫疾病,再请教临床上如何判断,对方也以“太复杂和你讲不清”为由拒绝了。我相信如果自己是患者的话,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对待,但这种把一切状态截然对立起来、无视他者声音的做法,不正是很多人感到郁闷、抑郁、痛苦、孤独的原因吗?老人向年轻人求助时有过这种体验,孩子向大人、普通人向专业人士咨询时,都可能被以各种方式吓回去。了解精神卫生知识和及时自我评估很重要,但还有一部分努力需要由别人来完成。对亲人、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当他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先去听他在讲什么,尝试理解这种感受,而不是以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去否定。
前媒体人陈瑜后来转去做儿童及家庭心理咨询,她在采访时说,以前做新闻关注事实,而心理咨询关注的是感受,它就是主观的,没有什么客观可言,这挺冲击我的,就算想让一个人通过认清现实的方法来减轻心理痛苦,是不是也可以讲究下方法和时间,不要捏着“事实”和“客观”的旗帜耀武扬威?
患者家属和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值得关注
黄月:有时候感觉我们所有人是坐在同一艘船上,在漆黑的海上航行,焦虑和抑郁就像风浪,持续打湿或弄疼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更残酷地,将他们拖下水去。这风浪无止无休,没有人安全无虞。最近五六年,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被风浪击中——有人在不同程度的抑郁中挣扎,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更可怕的电击,反复试探停药是否可能、一般的工作和社交是否可能、稳定的亲密关系是否可能;也有人在抑郁和躁狂两极之间摇摆,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家人无法相信这是疾病而不是“作”而自己主动住进医院,试过偏方,试过辞职,稳定快乐的状态犹如走钢丝一般,甚至来不及体会,便好像又要被黑浪拉下船去。还稳坐船上的人,多数不是良医,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披一条毛毯,鼓励他们继续接受正规治疗,拉住他们的手不松,反复倾听安慰,别失去希望,别沉没下去。
姜妍:在我印象里,蕴娴应该是组内记者在稿件里关注弱势群体、残障人士最多的人。在关注这类群体人员的时候,她的稿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平视的视角。在对比如儿童、听障视障人士的采访中,她都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换位思考能力。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篇稿件是自闭症关注日时对一位自闭症患者母亲的采访,通过这篇稿件我们会更多知道一些自闭症家属的辛酸,比如作为母亲照顾26岁的自闭症儿子,连出门上厕所都是难题。如果母亲去上厕所,谁来在外面照看儿子?生活社区里又有没有可以让患者家属稍微喘息的空间?社会系统的支持程度,以及患者身边人的感受其实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视角。
我自己接触过好几位抑郁症的患者,有几位是前同事,其中还有一位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对我来说的一个困惑是,在同事或者朋友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比如工作或者我们正常的交往时,我应该怎么处理?比如作为编辑,我遇见过有不止一位抑郁症的作者或者记者在截稿之前消失不见的情况。这就让我同样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我是应该立即拿备稿填上版面,还是应该继续等待?再比如曾经的一位好友在确诊前后和她交往让我有极大不适感,在后期有种自己要被她无穷黑洞吸光能量的感觉时,我选择了远离。我相信精神疾病的患者给身边最亲近的人带来的困扰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在越来越多关注精神疾病群体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分出一部分关注以及社会系统的支持给到他们身边亲近的人群。

叶青:开口寻求帮助很重要。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温柔、体贴患者的医生,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都十分理解支持,对我的恢复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但我也同意姜妍所说的,亲友们对精神疾病患者并没有无下限关怀甚至是容忍的义务,这个过程极其耗费心力,且往往是单方面付出,见不到成效的,难免会让人挫败。像是我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的劝导开解是对的、出于善意的,但是我就是做不到,也听不进去,有时甚至觉得厌烦,起到反作用。
此外,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值得关注,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了解,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或者因为对精神疾病的恐慌和误解,否认自己生病的事实,最后常常就是让自己和家人都活在痛苦中,互相折磨又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了解、正视精神疾病,多沟通,帮助他们获得专业的支持和治疗。
黄月:叶青提到的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之前蕴娴在稿件里探讨过儿童抑郁症的问题,老年抑郁也正成为我的准中年生活的关切之一。北京的一些医院里设置有老年抑郁科,在我老家那边,虽然我怀疑奶奶有抑郁倾向(她表现出来的只是脾气大)并希望能带她去做做检查,但在很多人连降压药都无法保证按时服用的地方,抑郁问题太不重要了,尤其是老年人的抑郁。似乎这种病的存在不仅没必要,甚至不可能。长寿已是喜事,谁能扒开表层说破其背面是精神的病痛和怕死的恐慌呢。
我有一位朋友的姥姥正在北京接受正规医院的老年抑郁治疗,药物让她的忧虑失眠症状有所缓解,但治疗只是一个开始。定时定量的服药、复查、配药等等程序,对于年轻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已是重负,何况是对于一个平时不住在北京的老年人,她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支持,幸好晚辈不辞辛劳,提供了周全的照料与陪伴。当然,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有其生物机理,但面对它的无力无奈以及无法包容和切实帮助,也常常让人觉得,它好像一只爱变得稀薄的世界里茁壮成长的魔鬼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