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经典电影《茜茜公主》中,巴伐利亚公爵之女茜茜远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茜茜和匈牙利贵族一同起舞的场景成为奥匈两族关系转折的标志,并促成了1867年奥匈帝国的诞生,她也因此被加冕成为奥地利帝国皇后兼匈牙利王后以及波希米亚及克罗地亚王后。尽管电影被不可避免注入了后人对帝国时代的浪漫想象,但我们仍可从茜茜的故事一窥近代帝国内部多元且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帝国政府如何“统治不可统治之地”,以应对多元社会纷争。
帝国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而是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历经成功的征服、殖民与政治操作的结果。在帝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国,还是俄、奥这些传统的大陆型帝国,都面对着族群冲突难以协调的局面。郑非援引美国东方学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帝国内部不断激化的政治冲突在划清社会界限的同时,也将地方社群不断“民族化”,结果便是不同群体在语言、宗教和族性之上构建出各自的身份认同与情感。
尽管帝国时代早已远去,但是其遗留的矛盾和危机仍然牵绊着现代民族国家。从早期族裔飞地与宗主国的冲突,到如今的全民公投、疫苗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很多社会问题仍在以族群问题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要如何理解中心与边缘、分歧与冲突?民族的划分方式会加剧国家内部的政治化吗?群族的边界是否一定指向冲突与分裂而非弥合与团结?民族主义作为西方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用和解释?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的青年学者郑非,立足于比较政治和族群研究,重新思考了“帝国的统治之道”这一历史问题。他业已出版的《帝国三部曲》前两卷《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为读者提供了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想象前现代帝国的视角。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郑非进行了专访,试图以思考帝国的崩溃帮助现代民族国家避免策略建构的失当,以及帮助21世纪的多民族国家理解自己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体会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
01 分歧与冲突是合乎自然的常态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前现代的帝国,尤其是古代帝国与近代帝国的区别?
郑非:美国著名东方学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说道:“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古代帝国的界限和近代帝国的界限不一样。古代帝国的界限需要考虑征服地区的自然资源、战略意义,及本地族群既有的组织结构、军事技能等;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条件的进步,帝国征服不再受地域限制,但是需要考虑“合法性”这一统治难题。
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就有了成为新帝国的潜力,但是它的实际扩张却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因为它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宪法事实上是否容许领土扩张;如果有,以什么形式、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通过哪些体制、机制;新领土上的管理机构是否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受到同样的宪法限制;结构性原则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获得领土和进行管理的方式等等。

[美]拉铁摩尔 著 唐晓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
这里发生的问题是,古代帝国的整合往往是靠某种人事吸纳政策,但是近代帝国要整合,仅仅靠人事吸纳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国,还是奥、俄这些传统的大陆型帝国,都遭遇到了我在《帝国的技艺》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帝国压力”。一般说来,当近代帝国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帝国的统治者们就会日益觉察到中心的约束——一方面,帝国统治者在核心区的统治日益需要依赖一套被大众认可或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帝国中心的人群中也会提出“帝国属于谁”的问题(帝国属于哪个阶层、什么集团、为谁牟利),从而对帝国提出要求,要求帝国为他们所用,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将迫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在各人群间做出选择、弃卒保帅——这些压力和约束古代帝国是不会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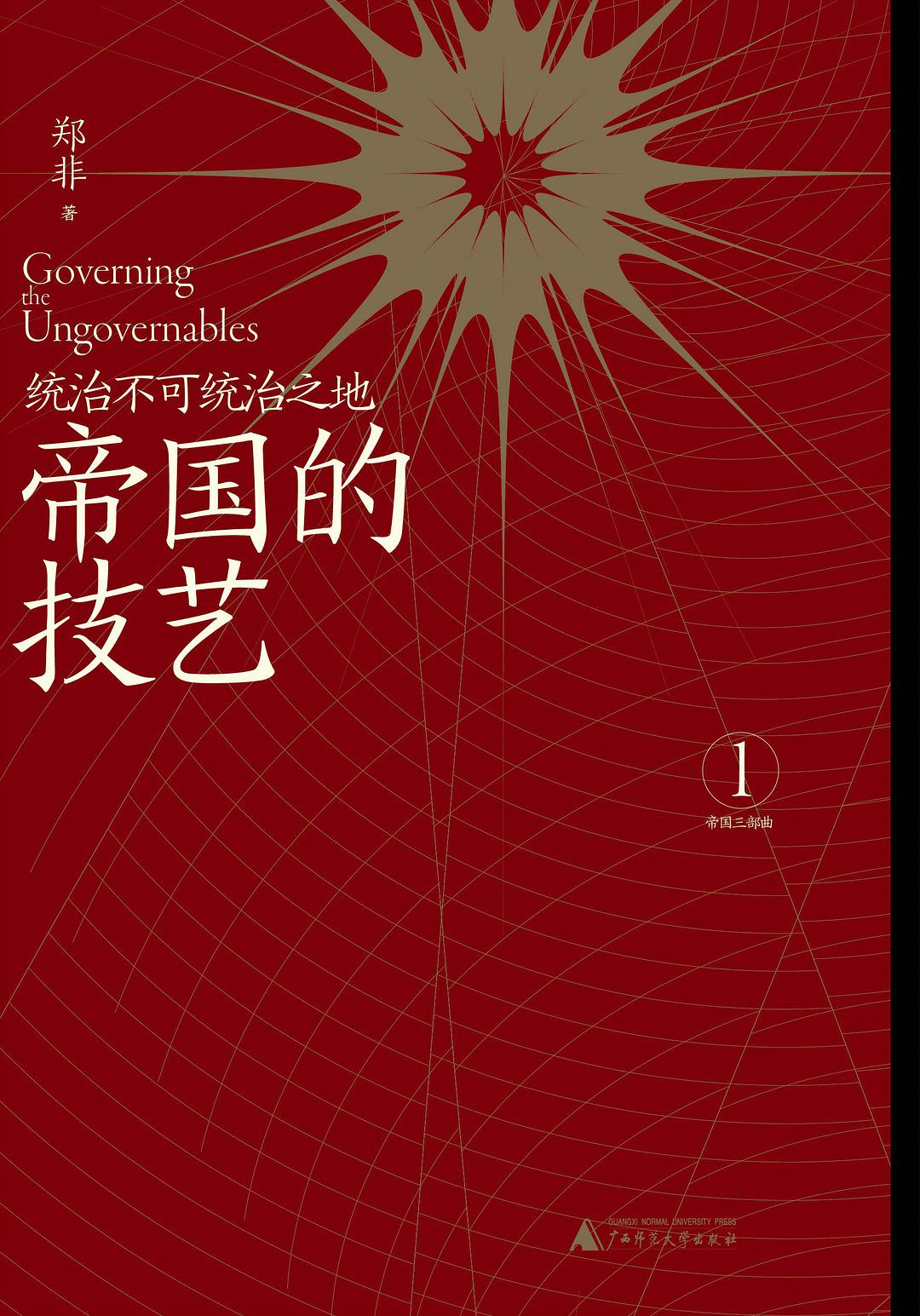
郑非 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1-1
界面文化:你基于对近代帝国的研究提出了几个假设,其中一个是“帝国构建模式本身是复杂的,并不一定是一个由帝国中心出发对边缘区、社群进行管制的同心圆”。我们怎样借助“同心圆”理解近代帝国?
郑非:我很喜欢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柏克的作品,他论述美国革命的许多观点我都耳熟能详。比如他有一次在论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时说道,“统一”与“一致”总是暂时的、相对的 ,“分歧”与“冲突”才是合乎自然的常态。如果我们从这种冲突观来看待帝国内部关系,当然就应该先去看有什么政治程序来调解、控制这种冲突。中心-边缘的冲突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区间的,一种是社群间的。这两种冲突有的时候合一,有的时候则可以分离。帝国政治结构的制度化水平,和帝国的社群关系处置思路就是为了对应这两种不同的冲突。
帝国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引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说法来解释,即帝国边缘的团体、个人地位也可以很不一样,有些边缘人能够参与帝国中心/本部和主权当局的决策和资源分配,有些则只能旁观,甚至遭到公开的歧视和剥削……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中心/本部有着中央集权政府、差异化的经济和共享的政治忠诚,而边缘地区则有着软弱的政府、去差异化的经济和高度分化的政治忠诚。
在鄙著所涉及的英、法、奥、俄四个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等级式、从内向外管制的同心圆,等级与管制似乎不可兼得。无论是什么帝国,似乎都要在某种程度、领域获得边缘地区和社群的配合。在传统的大陆型帝国,如奥、俄,对边缘地区通常都要持某种特殊优待政策,实际上也允许多头林立。在海洋殖民帝国,如英、法,尽管母国对属地要有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优势,但也没有同时实现这两者。英国人宁愿同殖民地之间保持某种社会距离,其代价就是其殖民地本土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不受干预。法国人管制的厉害,但却对政治平等非常的看重。
因此,我认为以目前的研究来看,帝国内部一定是多中心的。
界面文化: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提到:“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在帝国内部的边缘地区,各族群空间之间的“空间间隙”或叠合的民族边界在帝国管理结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郑非:已故美国社会学家罗杰·古尔德在《起义者的认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参与认同/身份(participation identity),即“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抗争活动中对特定的规范和工具性呼吁作出反应的社会认同/身份”。简单一点说就是,人的身份/认同千千万万,具体到特定一件事上,触动人们去行动的那个认同/身份就是所谓“参与认同/身份”。
这种参与认同/身份看起来是个人从不同身份/认同中选择而来,实则是有一道主客观夹杂的过滤机制。古尔德对此过滤机制的解释是:首先,具体的抗争与冲突要能够合理地用该身份/认同与他者的冲突来解释;其次,被动员者要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觉察/体验到该身份/认同所代表的那个共同体。在关键事件发生时,那种社会关系网契合的最完美的身份/认同将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动员力。从这个角度讲,古尔德并不主张那种预定的结构主义,而是认为,在人的行动中,身份/认同是根据环境不断重建的东西,并不遵循任何预先确定的路径。
古尔德的这个解释同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以及王明珂的“族群边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人都强调认同的可变性,它区分敌我的功能,以及其对环境、事件的依赖。巴斯曾在研究中指出,人们过去所普遍相信的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社会隔离和语言障碍在各人群之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与其说各人群像一个个孤岛彼此隔离存在,倒不如说各人群像大陆板块一样彼此碰撞、渗透。在这些大陆板块上存在无数细小的裂缝,人们完全可以任意选定这条裂缝或那条裂缝作为一块大陆的边界。所以,族群是一个自我归类过程的结果。王明珂也对族群边界论有过精彩总结,他认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
我们常常谈到帝国边缘地方的民族主义对帝国形成的挑战,但事实上,帝国边缘的民族主义更类似于某种参与认同的唤醒,是帝国内部先在的冲突赋予了民族边界以重量,而不是反过来的。比方说有人将美国革命归结为美利坚人认同、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出现。在18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新人群的存在,已经被人们所意识到(或者创造出来了)。但是这种“美利坚”认同在当时是否同英国认同有冲突,是很难说的。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指出,美利坚独特感的形成丝毫没有妨碍北美人对英格兰民族及其民族认同的忠诚,二者反映的并非分裂的忠诚,而是位于同心圆上的忠诚。两者并不矛盾,正如一个家庭成员、一个城市居民或一个国家公民之间没有矛盾一样。所以其实是革命形势让美利坚民族主义浮现出来,成为一种动员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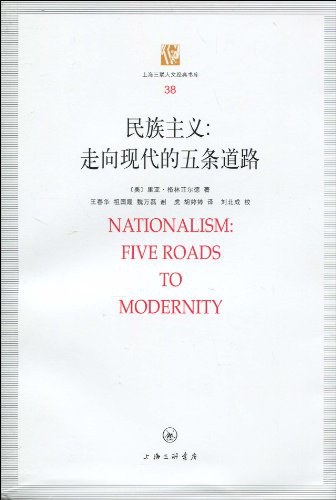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王春华 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
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成功的帝国里,各民族的边界都应该在沉睡中。它在那里,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帝国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冲突可以用它来解释。
02 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之间不一定存在无法弥合的区隔
界面文化: 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前提,民族、族裔、族群等涉及群体划分的词语复杂且容易产生歧义,你如何理解他们的区别?
郑非:一般来说,民族和族群的区别是民族有更多的政治民主主义,族群更偏向于社群(community)概念。我们其实也尽可能避免使用民族这个词,避免国家内部的政治化。所谓的族裔其实是一个自我分类的结果,是当人意识到自己有类别后情不自禁对这个类别投入认同情感。这种心理认同和情感投入足以让人产生政治冲动和政治行动,在合适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族就会出现。
从参与认同的角度,意识到自己的类别不过是第一步,还需要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外人的不同。他们能观察到在自己的类别中间存在着大量的社会联系,这个社会联系本身使得他们与外人之间产生冲突。因此,单纯对民族识别是不足以产生民族主义的。如果要产生民族主义,至少还需要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斗争,并且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使整个社会碎片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才会产生。
界面文化: 你曾提及族群的边界是被发现的,那么这种群体的划分是否帮助了民族主义者建立和加强族群之间的边界?
郑非:从哈布斯堡王朝以语言作为区分标准的实践来看,分类除了唤醒民族意识之外,确实起到了加强社会隔离的作用。要着重指出的是,分类本身只是指出族群可被观察到的一个边界,要让这个边界具有政治分量,需要环境让这个边界里的人同时感到处于同一个不利的政治处境之中才行。这时候他们彼此观察,发现自己确实存在某种社会联系,确实面临相似的外部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分类本身并不能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内部民族主义的兴起负完全责任,但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界面文化:基于中心-边缘的话语叙述,你认为在帝国统治下这二者是否存在社会凝固性?即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迈克尔·赫克托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内殖民主义”概念,意为限制边缘地带人民向上的流动性。
郑非:当赫克托提出“内殖民主义”概念的时候,他所比拟的对象就是“外殖民主义”,国家的主体人群对待自己的边缘人群同一个殖民帝国对待其殖民地没有区别,中心人群凭借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占据社会等级的上游,边缘群体只能屈居其下。
但是,赫克托主要是从英国经验来给出这个判断的。法国人在法帝国的统治上,从表面上看,其实要比英国更“自由帝国主义”。比方说在1881年5月5日,法国著名的共和主义政治家甘必达在纪念废除奴隶制(1794年)的宴会上发表演讲,提议为“海外法国”干杯,并说道:“人权宣言没有根据肤色或等级来区分人……正是这给了它以庄严与权威……它并没有说‘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而是说‘人和公民的权利’。”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阿尔德里奇也指出:“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殖民政策的概念是‘同化’,这项政策旨在消除殖民地和本部之间的所有差异,赋予它们与本部相同的行政、财政、司法、社会和其他制度,给予其居民充分的公民权利,并迫使他们承担与法国公民相同的义务。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使成为海外的小法兰西,或许,在时机成熟时,将非洲人、亚洲人和岛民变成不同肤色的法国男人和女人。”尽管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将这个同化政策实施下去,但是有部分实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描述道“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个漆黑的黑人或者一个眼睛细长的中国人挎着胳膊走进最近的小旅馆时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巴黎,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出身?”这种情形在其他欧洲首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在帝国统治中,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之间不一定存在无法弥合的区隔,要看环境与治术。
界面文化: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为大众所广泛关注的概念。对于前现代帝国及其内部族裔的探讨,以及帝国中心主动进行弥合差距的尝试,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跨国“流散社群”和分离主义运动?
郑非:《帝国的技艺》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过去我们常常把帝国中心-边缘紧张关系产生的原因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在很多场景中,与其说地方民族主义是紧张关系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紧张关系的结果。坦率地说,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发明的产物。比起文化、血缘,政治冲突在促进人们的民族认同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帝国中央,边缘地方差不多总是比较弱小和组织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势力强有力的支持,或者是在帝国被极大削弱、面临崩溃之际。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开始就寻求自治和独立,而是希望进行改革、获得尊重、分享权力,不管这是出于利弊分析、强弱对比,还是传统与习惯如此。一般来说,是事态的发展逐渐使他们激进化的,是政治冲突本身逐渐划清了社会界限,从而“民族化”了这些地方社群。民族主义往往是帝国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帝国矛盾的原因。
到了大众政治时代,帝国中心的人们对帝国提出了要求,他们既要求在帝国内实现族群等级制度(即帝国的利益分配向核心族群倾斜),又要求上下一体,认为帝国应该加强对边缘地方的管理,以便更有力的汲取。这种做派很显然违背了过去一切的帝国历史教训。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帝国本部的制约,实际上使得“帝国企业家”治理帝国的成本大大增高,这才是帝国衰退的根本原因。因此,对帝国来说,最危险的威胁来自于帝国的本部人群,而非边缘地带的挑战。
从这两个历史经验讲,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发生分离主义运动,第一,最好不要第一时间就去看少数族群在宗教、文化、社会或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他们与主体民族的差异,觉得消灭特殊与差异就能消灭分离主义运动与倾向,而是要去看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特殊与差异被动员起来的;第二,要理解,对国家统一造成最大威胁的往往是主体人群的封闭心态,而不是边缘人群的挑战。

郑非 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1
03 并非想要探寻真理,只是证明不同的存在
界面文化:你曾质疑“今人研究帝国,多半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感,想在古代找到应对族群政治的良方”的观点。在你看来,帝国统治结构是否能为今天所用?
郑非: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人对帝国意味着什么自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大家一般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又强大又广袤(广土众民),那么这个国家就配得上帝国这个称谓(不管帝国用在此处是形容词还是名词)。学者可能对帝国的定义要更挑剔一些,觉得强国未必就是帝国(尽管强国常常以帝国自诩),还是从广度上来考量更合适。
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中是这么说的:民族国家高举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国则承认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驱逐以求一致,而帝国则海纳百川,自觉维持其属民的多样性,实施多重治理,从而凸显其属民的各自差别。作者自述,他们就是想抛开民族国家成长的主流叙述,去描述这个更古老、更持久、更多差异/多元化的政治实践,描述它如何在内部力行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它与其地方代理精英及其人民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学习,帝国观念以及统治的策略。

[美] 简·伯班克 著 柴彬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不能说错,但是在古代,很难说有什么族群政治,或者说族群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在这里,我指的是人们在古代也许会有简单的民族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是否超越了其他认同,是一件很可疑的事。相应地,在古代,实施多元差异统治几乎是统治者下意识的做派,也不是特别费力。
界面文化:大众对于帝国的关注好像集中于大英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或是当今已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加拿大等原殖民地,我们始终在基于西方语境中“帝国”概念理解古代世界,你如何看待帝国史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
郑非:“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是一个要不得的东西,它会局限人们的视角与认知。但是反过来说,为了推翻“西方中心主义”,就要搞东方版本的“帝国”定义,或者只去做非西方的帝国研究,我也会觉得这是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因为我想,所谓某某中心主义,大概指的是仅从一个地区的历史经验出发去认识世界。那么反此中心主义,就不能仅仅说由此经验产生的认知就是偏颇的与不公正的(我们最多只能说这种认知未经检验,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也不能只是找到另外一个地区的历史经验来否定前者认知的真实性。我们完全有可能是在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都是真理的一部分。
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不分东方西方,有个好用的概念先拿过来用,用的时候不分东方、西方检验之,这样可能会做成一个更好的历史研究吧。
界面文化:古代中国是否为“帝国”,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获得定论。西方帝国史研究是否能启发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对中国古代史(边疆史)的宏观思考?
郑非:新清史研究就是西方学者在用多元帝国政治观来看待中国历史的结果。我一直认为复旦大学的姚大力老师是边疆史、民族史领域中最棒的学者,他能够博采众长,既掌握丰富的多语言与多区域的史料,又能够接受新的视角与理论。他对中国边疆史的理解,既突破了原有的汉族中心观,又能够指出西方学者眼光与学识的不足——由于其经验,过分地重视王朝中的民族因素。
正如我刚刚讲的,尽管民族主义是个西方的概念,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用。我们可以借某个地区的经验总结所得,进行更多的检验。我并非是想要探寻真理,只要能让大家意识到不同的存在就够了。
界面文化:《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是三部曲中的前两本,第三本《帝国的未来》主要是关注什么方向?
郑非:我在撰写《帝国的失败》过程中,思考把片段的历史分析延伸到更广大的世界中间,于是写就了《帝国的技艺》,用英、法、奥、俄四个不同的帝国对原先从某个案例演变出来的模式进行检验。从逻辑上看,《帝国的技艺》首先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式,将近代帝国依据正式/非正式、吸纳/隔离两个纬度进行分类。《帝国的失败》是在某一个片段中间对这个模式的检验,而《帝国的未来》则是关注当前多民族国家所得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比如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三个规模很大、历史源远且人口复杂的国家。更具体一点,以俄国为例,从俄罗斯帝国到前苏联,再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其实有一条逻辑线索可以将它们串联起来,这就是我想在《帝国的未来》中呈现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