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高迪是一只来自坦桑尼亚贡贝的雄性黑猩猩,1974年的某天,当他在树下进食时,被其他派系的雄性黑猩猩们突然袭击并折磨致死。这一殊死搏斗被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记录在1996年的著作《雄性暴力》中:
“高迪慢慢地抬起身子,他在恐惧和痛苦的尖叫中,看着那些折磨过他的家伙们离开。他的脸上、身上和四肢都有骇人的伤痕……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70年代,兰厄姆成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的一名研究生,并开始了关于坦桑尼亚黑猩猩的研究项目。他发现,黑猩猩群体中充斥着这样的暴力事件,它们的人类后代继承了这一进化遗产,表现出相似的雄性暴力倾向。然而,兰厄姆同时发现,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倭黑猩猩——却与黑猩猩截然不同,它们喜欢拥抱和嬉笑打闹,这也解释了人类本性中的和平倾向,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乎更喜欢合作共赢而不是彼此攻讦。

人类更接近暴力的黑猩猩还是友爱的倭黑猩猩这一问题,导向了“人类善恶悖论”,并可由此总结出截然相反的道德伦理系统,就像著名的“霍布斯V.S.卢梭”争论那样——霍布斯的追随者认为自然状态下人注定会走向相互伤害的境地,卢梭的拥护者则深信人人内心深处皆善良。
时至今日,这一争论的结果还远未尘埃落定。我们或许都从《自私的基因》或《乌合之众》这类书中隐隐感到“人性本恶”,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也曾提醒过我们,种族灭绝可能是人类从动物祖先身上传承的特征之一。而在号称“反历史潮流”的著作《人类的善意》中,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作为坚定的卢梭派认为,好战并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自从人类学会了定居和进行农业耕种,就失去了游牧民的和平基础,转而过上了争夺资源与土地、互不信任的生活,“智人作为一个物种,被强行从天然栖息地中拽了出来。”

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但答案也许在问题之外。在写下《雄性暴力》的几十年后,理查德·兰厄姆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注定是既善良又邪恶的混合体,我们为什么会进化成今天的样子?
追随着这一问题,兰厄姆写下了新著《人性悖论: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从侵略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一直论证至军国主义心理学的进化基础。在书中,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攻击: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前者经常伴随着愤怒和恐惧,男性群体中的“性格之争”和名誉谋杀就属于此类;相反,主动性攻击是有计划性的,不会伴随太多情绪。

在兰厄姆看来,前者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大幅减少,后者不断增多,这就是解开人性悖论的钥匙。他谨慎地提出了假设: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趋势,是由于男性弱者们组建了联盟,开始有部署性地执行死刑,以驱逐极端暴力的个体。于是,那些容易情绪化的反应性攻击者就被自然选择筛选了出去,这一过程就是人类的“自我驯化”,类似的驯化也发生在倭黑猩猩身上。不过,倭黑猩猩的驯化是由雌性团体驱逐暴力雄性才得以完成的,对于人类来说,掌权的显然是雄性联盟。当单个首领的有限权力变成了男性联盟的绝对权力,并发展出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专制形式,这带来了更强的合作能力,使具有善意的个体更易存活,却也为大规模战争、屠杀与权力滥用提供了条件。
日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了理查德·兰厄姆,他谈到,人类智慧和文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产生了消极的结果。不过,兰厄姆对于未来仍怀有信心,他觉得,如果驯化之路继续向前推进,人类会变得更加团结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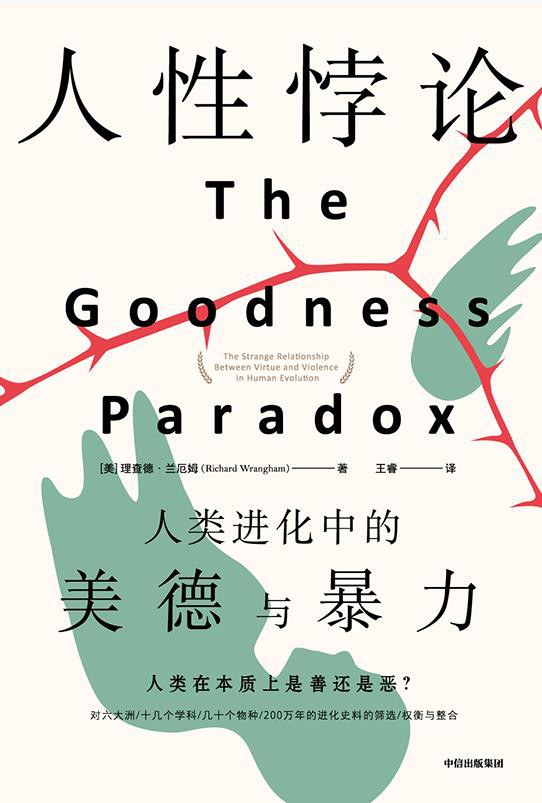
[美] 理查德·兰厄姆 著 王睿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6
界面文化:1996年出版的《雄性暴力》描述了人类从其猿类祖先那里继承的暴力倾向,并指出人类的战争比黑猩猩们擅长的“突袭”更为复杂。你的新书《人性悖论》将重点转移到了人类的自我驯化之路,以及这种驯化与复杂战争的关系上。从第一部著作到现在,你是如何发展你的研究想法的?
理查德·兰厄姆:在写完《雄性暴力》之后,我开始关注一个迷人的问题:为什么倭黑猩猩不像黑猩猩那么有攻击性?要知道,这两个物种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不仅看起来相像,而且生活在差不多的栖息地。我意识到,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差异就像是狗和狼的差异,倭黑猩猩显然是从类似于黑猩猩的祖先进化而来的,这表明它们经过了一种类似驯化的过程。
于是我发现,从我们的祖先海德堡人到智人,或许也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一思路所提出的人类进化理论是全新的,所以我必须谨慎地考虑它究竟是否成立。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想法的论文草稿,并花了近20年尽可能仔细地审查这个论点的证据,最后发表在《人性悖论》中。

界面文化:你长期关注人性中的善恶悖论问题,在2010年的一篇题为“在爱与战争之间挣扎的两极猿(Bi-Polar Ape: Torn between love and war)”的采访中,你与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著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等)、弗兰斯·德瓦尔(荷兰著名心理学家、动物学家,著有《万智有灵》《黑猩猩的政治》)就此进行过讨论。十几年过去了,学界对这一问题是否取得了共识?
理查德·兰厄姆:让我很惊讶的是,一些科学家——比如弗兰斯·德瓦尔和罗伯特·萨波斯基(编注: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到现在仍然认为,人类特征中的善良合作是进化性和适应性的,但人类的邪恶却不是进化的产物。我和史蒂芬·平克都同意以下观点,即自然选择对于人类心理中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都有影响。
那么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变成这样?这就是《人性悖论》的内容——我们要如何解释人类既“善良”又“邪恶”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已经得出了受生物学证据支持的答案:大概在30万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出现死刑,那些有冲动杀人倾向的人被死刑筛选出去,留下的是具有互助美德的人。
界面文化:史蒂芬·平克在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指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而理性作为“善良天使”之一,能够帮助我们远离暴力;但是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正是理性的计算和官僚社会使大屠杀成为可能。你会如何回应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
理查德·兰厄姆:我并不觉得这两个观点是对立的。人类的智慧和文化让我们设计出了越来越巧妙的工具、社会实践和各种机构。我们一方面以此让自己更安全,另一方面也以之剥削和利用彼此。令人宽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生活总体上是趋向于减少暴力的,不过,力量占上风的个人或团体对一个较弱的群体施加暴力的威胁并没有被消除,它仍然蛰伏在我们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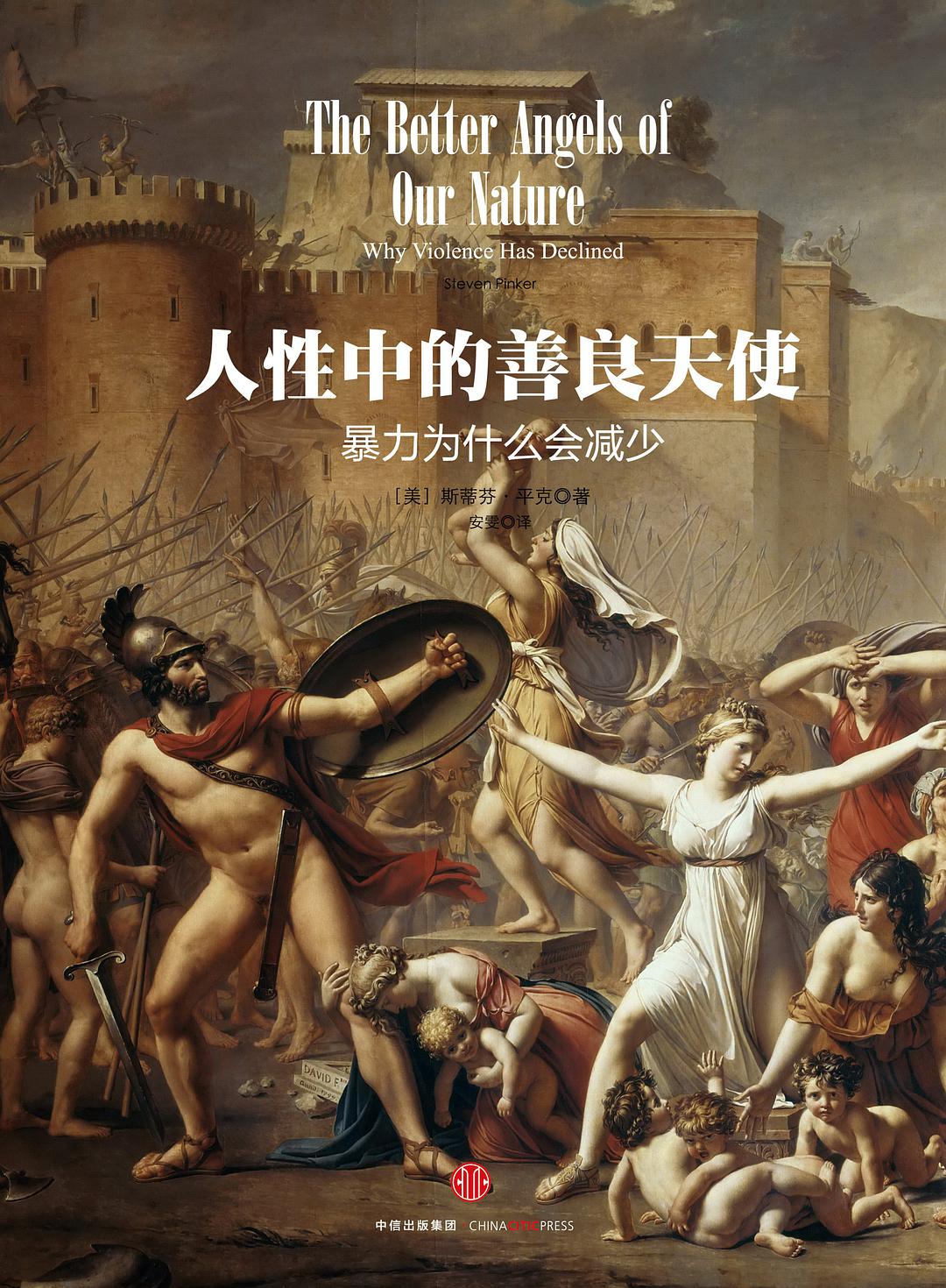
[美]斯蒂芬·平克 著 安雯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7
界面文化:我们会在电影或剧集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角色甚至于观众会被自私的变态杀人犯“吸引”,很难说清这些残忍而同时具有魅力的角色到底是“好”是“坏”。这是否说明某些进化力量仍然在我们体内发挥着作用?以及,善与恶的道德区分只是人类的发明吗?
理查德·兰厄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以道德是非划分行为确实是人类的发明,我在《人性悖论》中描述了人类是如何成为“道德的物种”的。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男性长者联盟”,他们会共同行动并领导社会,这种联盟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尽管领导方式各有不同)。在小规模社会中,男性长者会处决“坏人”(那些行为上不受欢迎的人),保护“好人”(那些行为受认可的人),因此,自然选择就会有利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如果说我们对暴力的精神变态感兴趣,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惧怕,而不是钦佩。在过去30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精神病患者已经从一种典型的人格变成了一种罕见的、令人害怕的人格类型。
界面文化:通过死刑杀死暴力的个体,从而促成智人驯化这一观点相当有趣。但是也有人说,早在人类进化的概念出现之前,“人类是被驯化的”这一观点就已经被提出了。这些早期的观念是如何启发你的研究的?
理查德·兰厄姆:人类被驯化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并且在19世纪初由伟大的德国体质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大力倡导。我对人类可能是被驯化的这一想法产生兴趣后,便着迷于发掘这些早期的研究。
在布卢门巴赫和其他学者所处的时期,还没有产生进化的概念,所以他们认为是神圣的造物主让人类驯化了自己。考虑到当时的人并不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这些学者还能坚持相信人类驯化的观点,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了,这是一个更扣人心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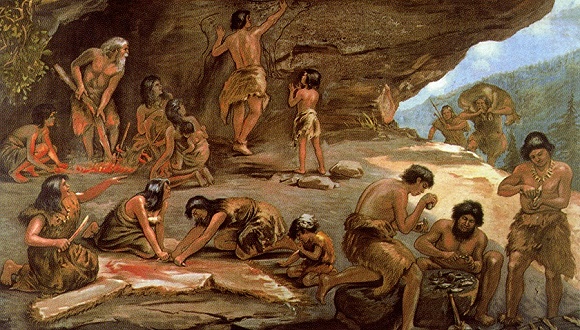
界面文化:在猿类和人类的行为模式之间建立联系应该很有挑战性。一方面,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能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提出假设;但另一方面,猿猴确实是人的近亲,在基因层面与我们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在观察它们时,你是如何平衡这一点的?
理查德·兰厄姆:野生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研究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攻击行为来说,我们必须谨慎地依照具体发生的行为来做出定义,比如,攻击性追逐的量化标准可能是“持续时间3秒以上、追逐距离大于5米”。评估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时,需要根据它们在一起的时间、彼此相隔的距离来统计互动次数。通过这些程序,我们就能在个体、群体以及物种的层面进行仔细的比对。而且我们发现,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数据往往比人类数据更容易量化!
界面文化: 在《人性悖论》中你提到了语言的两面性。与猿类不同,语言为智人带来了合作,而尼安德特人无法在认知上传递生存所需的文化知识;但另一方面,语言也让暴力变得更有计划性和破坏性,这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更加突出,比如政府会在战争中利用谣言来混淆视听。如果人类变得既合作又分裂,我们还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吗?
理查德·兰厄姆:这的确是人类行为的一大悖论。在过去的5万年里,我们从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以较低的人口密度散布于各地,发展到现在的大型、联系密切和人口众多的社会,这一成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合作能力比破坏能力要更有效。但现在我们面临两个巨大的风险,一个是我们的武器如此强大,另一个是长远来看国际竞争体系显然是不稳定的,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的风险,就必须让位给更多的合作。
界面文化:女性经常担忧于来自男性暴力攻击,但有些男性可能会感到不理解,疑惑于为何暴力行为要和性别因素直接挂钩。但是从你的作品我们了解到,男性暴力确实有进化方面的基础。通过证明这一点,男性暴力是会得到约束还是更肆无忌惮?例如,睾丸激素水平高的男性被认为更有阳刚之气,有些人可能以此作为施暴的借口。
理查德·兰厄姆:我相信对于这些观点的教育很重要,但我估计很少有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会仅仅因为知道他们的进化基础而抑制暴力倾向。在我看来,进化科学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男人的暴力,而不是以他们能够被教导为由而轻视了这一点。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能成功走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社会发展出了保护弱势群体和惩罚侵略者的机构。
界面文化:事实上,仍有很多暴力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虽然远远少于黑猩猩),比如大规模枪击事件和街头斗殴,这意味着人类的自我驯化之路还未结束吗?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驯化”的未来吗?
理查德·兰厄姆:我认为确实可以期待这样的未来,自然选择会继续反对具有反应性攻击的人,正是这类攻击造成了社群内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暴力倾向的人的生命通常更短暂,也更碌碌无为,有些人死于斗殴,监狱里也到处都是暴力人士,并且,蹲监狱有可能会导致生育数量下降(虽然我还没找到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如果人类这个物种能存活下来,自我驯化的程度应该会在几十万年内持续增加,直到我们成为更团结善良、非竞争性的个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