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过去,东亚各国的商贾使节哪怕语言不通,也可以只凭着一纸一笔,用汉文进行“笔谈”。因为东亚各国曾在历史上共享过相似的文化,而汉字恰巧是其精髓所在。一言以蔽之,东亚的世界曾经是汉字的世界。
在《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中,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由这一主题出发,通过分析使用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探讨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日前,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吴光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围绕东亚与汉字的问题展开了探讨。
同样是汉字,读写各不同
金文京在视频连线中谈到,汉字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来源与核心,因此古代中国邻近的国家、民族、地域借用汉字,读汉字写的书或者用汉字写文章,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莫大影响。“大家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邻近国家既然使用汉字,就应该属于中国文化圈——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训读的做法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现了,指的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读汉字的意思,比如日本人把“山”字读成yama,古代朝鲜人读成moe。这样一来,同样是汉字的书,可是发音、读法都和中国不一样,各国写的汉文也跟中国人写的汉文有所不同。既然读法、写法、文章都不一样,那么各国以此发展出来的文化甚至世界观,自然也与中国有所不同。

马场公彦也表示,中国经典的古典文献是东亚世界的共同文化财产。同时他也看到,这些文献通过训读的方法引进日本,可能会发生一些误会。《论语》和“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可以通过训读来阅读,但对于白话文献却行不通。一般日本知识分子阅读的是儒学经典和历史的正史,但不阅读野史和白话文献,“他们译介的所谓东亚共同文化就是儒学,这其实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但容易被误会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全部精华。”
刘晓峰认为,金文京、马场公彦谈到的发音“漂移”并不奇怪,这种“漂移”在古今都会出现。比如中原音韵学中,宋朝、明清和现在音韵都不一样,地域上也会产生差别,比如东北和上海方言完全不同。他也看到,汉字在东亚圈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声音出现漂移甚至遗失,但字义传达方面具有某种共通性。汉字承载的最核心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方式也有类似之处,比如孩子从小就要学《论语》。刘晓峰认为,东亚各国有不同的部分也有共通的部分,这两部分相加才是“历史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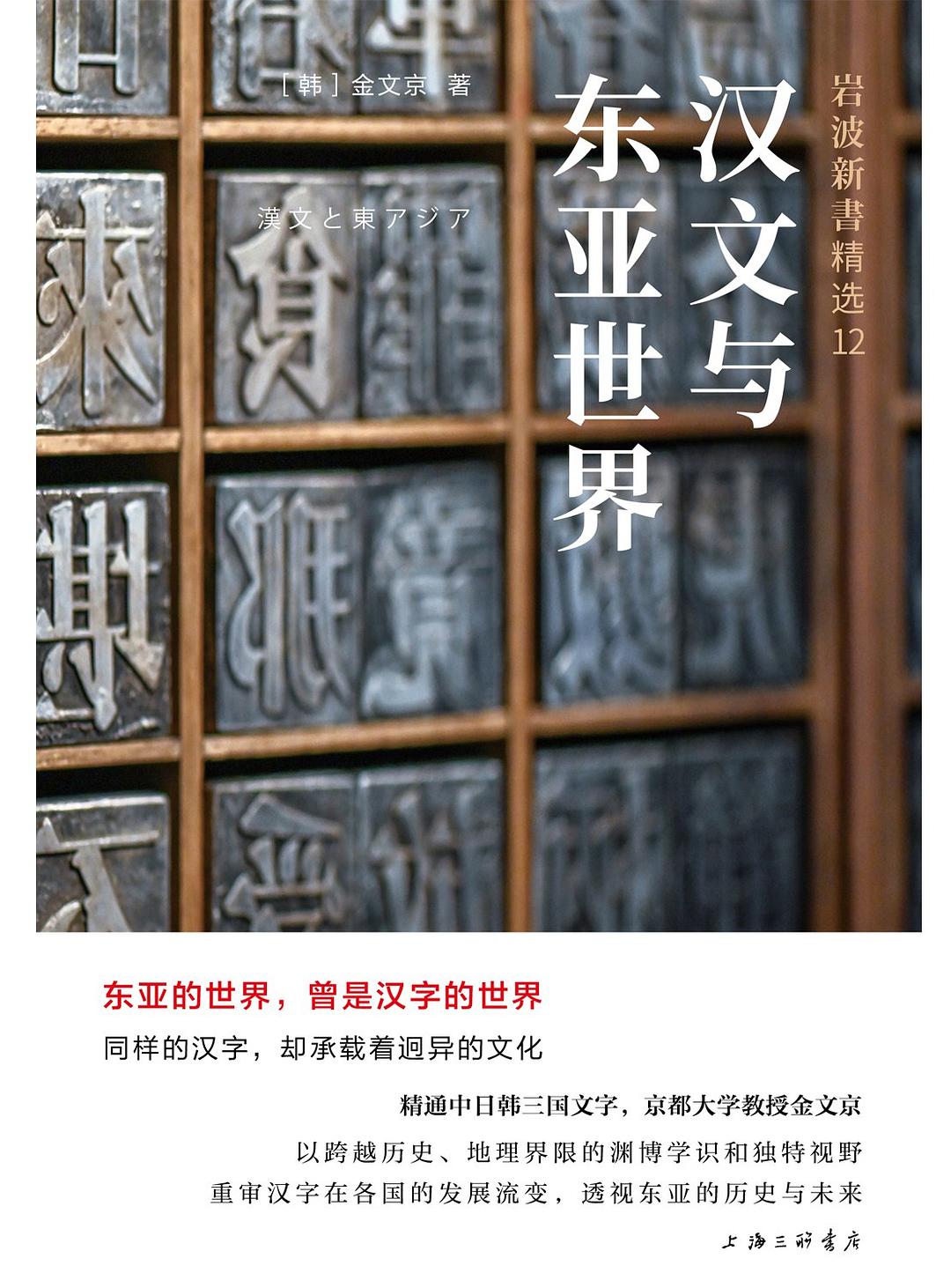
[韩] 金文京 著
新经典·琥珀 | 上海三联书店 2022-10
在共享文化之上竖立民族国家界限
因为汉文在各地的发音、读法有很大差异,没有办法成为口头语言,所以汉字文字圈里的各国人士沟通时需要通过笔谈的方式。金文京在书中提到,不仅文人之间如此进行沟通交流,外交事务也是如此,比如清朝时期越南和朝鲜的使节在北京见面,或者朝鲜通信使去日本和日本文人交谈,无不用笔谈的方式。
宋念申在活动中提到,所谓笔谈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19世纪后期,当现代外交进入到东亚世界,当时大量的中日朝的官员和学者还是用笔谈的方式来进行谈判和交涉的,中朝之间的条约也仍然由汉字书写。然而,古典的共享文化价值也正是从那时起逐渐受到冲击——日本的外交官在欧美学习到新的外交语言之后,要求使用英语进行谈判,条约以英文文本为最主要版本,双方解释不同、需要参照时也要用英文文本,“从这个时候开始,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树立在东亚本来共享的文化上。”
他谈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及周边国家对汉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南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很早就废除了汉字;朝鲜半岛在20世纪的主要时段倡导了谚文运动,使用自己的拼音文字,之后有一段漫长的谚汉混杂时期,1949年以后朝鲜半岛两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待汉字的政策,北方彻底废除了汉字,南方坚持使用汉字很长一段时间,到今天也已不太常用。
在中国,钱玄同等一批学者认为汉字是进入现代化的障碍,主张废除汉字,使用拉丁化、罗马化的文字;同一时期,在东亚最早完成了现代化的日本并没有废除汉字。宋念申认为,在现代化起步不太成功的中国和朝鲜,想要与传统划清界线的做法,其实展现的是面对现代化的无所适从。

文化的边界远远大于民族国家的边界
在活动现场,吴光兴讲了一件趣事:晚清大员张之洞不喜欢当时梁启超的做法,认为他喜欢用日本名词,随后幕僚提醒他,“名词”也是日本词呢。
回溯历史,吴光兴称,有两件事对中国人今天使用的汉文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是佛教译入中国,二是日本词进入中国。他说,中国双音节词半数以上都是从佛教译出来的,如果把这些词汇拿掉,“中国汉代以来的文化和学术会不复存在”;而如果把日本名词摘除,我们也会很难沟通交流。宋念申也指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的词都是由日本发明的,日本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世界,之后又变成东亚世界普遍接受的词汇。例如,“经济”这个词最早是日本翻译“economy”得来的,现在,中文和朝鲜文也全部使用“经济”一词,尽管书写方式各不相同。
所有文化都是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强调我们有一个本原,这个本原是最真实的、最本质的,后面所有加诸的其他外来的东西都是非本民族的。但其实,那个本原并不真的存在。”宋念申谈到,韩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去汉字化运动,但用官方政策褫夺文化的已有属性是非自然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把韩国文化自身最重要的一部分抹去了。由于韩国19世纪之前的官方史料基本都以汉字书写的,如今韩国青年学者研究朝鲜历史还要重新学一门外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这种文化共通的视角也为我们在今天理解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刘晓峰曾经参加过一个国际研讨会,会上,一位中国学者证明某个韩国的东西是中国老祖先发明的,一位韩国学者抱怨称:“你们总说这个是你们的,那个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我们还有什么?”他还注意到,在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中国人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才是正宗的端午节。而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此事,刘晓峰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跟我们一起过端午节的有几个?伊斯兰教国家过吗?基督教国家过吗?非洲国家过吗?能够一起过端午节的,都是跟我们中国有非常深的文化渊源的。”
“文化的边界远远大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刘晓峰认为,中国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在文化上应该更有胸怀,多想想“我们这些共同拥有过汉字文化传统的人,怎么创造一个本地区更美好的未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