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1日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辰。在《蔷薇花与十字架》的《群魔的献祭》一文中,作者杨不风就陀氏在《群魔》一书中关注的核心议题——价值虚无主义展开了谈论。“上帝死了”之后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拥有宗教信仰传统的欧洲人的困境。放在当下来看,“不再有任何确定的价值,不知道一种善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任何对于善好生活的希望。我们可以否定一切,包括自己”——这样的问题无疑是更加严重的,这是陀氏至今能够击中我们的原因之一。
《群魔的献祭》(节选)
撰文 | 杨不风
听着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来讲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情。自从几个月前读完《群魔》(我所读的译本实际上译名为《鬼》),这支变奏曲刚刚响起时的那段旋律就常常在脑间回响,为我带来稍许的平和与安宁。现在打算写些关于这本书的东西,也刚好有机会再次聆听这支曲子。不过,舒缓的前奏总会过去,激烈、急促的变奏会将一个个音符挤压成奇形怪状的褶子和折皱,在它们叠合的缝隙里隐藏着让人窒息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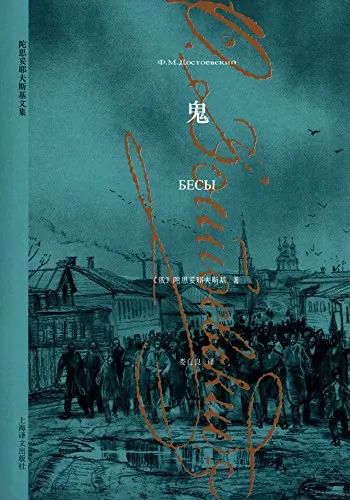
[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娄自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显得不太符合时代趣味。生活如此惬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让人沉重、悲痛的东西?纳博科夫显然更投大众所好,也更时尚。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对语言的天才式驾驭,以及离经叛道的主题,很容易吸引人们的好奇心。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岂不是自找苦吃?甚至是,自虐?纳博科夫本人也对陀氏没什么好感——当然他对许多举世闻名的文坛巨匠都瞧不上眼——说陀氏是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不过写些三流侦探小说,又笨拙又丑陋。
老实说,陀氏的文笔远远算不上一个语言大师,他的意义更多的在思想和心理层面。一位德国先生对我们说,19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大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类似的话也可以在加缪那里见到,他断言:“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20世纪法国文学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在他的办公室里,仅有的两幅肖像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那位德国先生对我们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我用了“震撼”一词,另一位朋友则说“疼痛”。很早之前也听一位朋友转述过一个看法:“心肠太过柔弱的人最好不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心硬如石的人或许又读不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这次读《群魔》,已经没有几年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时那么投入。那时,随着情节的起伏,焦灼、仇恨、凶残、兴奋、狂热、抑郁、绝望、忏悔、喜悦、安详,种种情绪会将人卷裹进去,在此之后,一条暗流总会翻腾而上,涌出心灵的波面。《群魔》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段思辨性的叙述。这些部分也就是尼采阅读《群魔》后所做的几段摘录。摘录作于1887—1889年尼采居留尼斯期间,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斯塔夫罗金自杀前给罗莎的信件的片断,其他三部分分别命名为《关于虚无主义者的心理》《无神论的逻辑》和《作为民族属性的神》。其中,前两部分涉及基里洛夫的理性的自杀观念,最后一部分则是沙托夫的带有斯拉夫主义色彩的神学信条。每一个因《群魔》而不安的人,都会胶着在这四个片断上。
或许还需要补充一段,即1871—1872年《群魔》在《俄罗斯通讯》连载时被编辑卡特科夫要求删去《在季洪那里》一章,后来这一章以《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为名单独出版。这部分讲述了斯塔夫罗金接受沙托夫的建议,拜见居住在城郊的季洪大主教(这个人物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都以18世纪俄罗斯的圣季洪大主教为原型),向他忏悔早年在彼得堡荒淫无度的生活。在那里他强暴了11岁的少女马特廖莎,当他看到马特廖莎将投缳自尽时,斯塔夫罗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静静等候了40分钟。从此之后,他便以一种自我惩罚、自我毁灭的方式寻求宽恕,但他又不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宽恕,尤其不接受基于信仰的、来自基督的宽恕。他出于一种高贵的自傲,首先便是自己决不宽恕自己。他告诉主教,要发表一篇自述,坦白所有这一切。主教劝说他,更大的牺牲是放弃这一自傲的举动。斯塔夫罗金的回答很奇怪:“我若是听您的,就会有个归宿,就会养儿育女,成为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假日还来到修道院。”斯塔夫罗金不可能真诚地忏悔,在这里可以听到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在一篇短篇小说结尾处的回音:“即使下地狱,也不忏悔。”这是面对世界上和人心中的罪恶发出的对人类所有罪行的控诉,而被告是造物主。
德国先生后来有些奇怪,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是“上帝死了”之后的问题,是欧洲人的困境,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人似乎没道理有这类焦虑。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准确回答,后来想想,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定义的“虚无主义即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同样是:我们不再有任何确定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我们也不知道一种善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没有任何对于善好生活的希望,我们可以否定一切,包括自己。
《群魔》刻画的,是早在19世纪的俄罗斯就已然出现的价值虚无的背景下,以斯塔夫罗金为核心的一群虚无主义者的群体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临终前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中,总结了虚无主义者的特征:“这类人不守安分,不满于任何持存之物,不相信自己的故乡和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力量,彻底否定俄罗斯,也否定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否定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整个知识阶层,这个业已脱离了我们民众土壤的阶层)。这类人不愿与自己的民众同胞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确实真诚地为这一切所折磨。”(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讲授课中的《欧洲虚无主义》一章开头曾引用了这一总结。)不能简单地认为陀氏在对虚无主义者进行批判,虚无主义不是文化现象,而是形而上学的必然运动;不存在批判虚无主义这回事情,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只谈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斯塔夫罗金在陀氏晚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演变为伊凡这一角色,正是借伊凡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后来每一个思考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的思想家都不得不面对传说中提出的问题。为人们所知的是,陀氏为整部书的章节划分花费了三个月时间,而创作这篇渎神(还是颂神?)之作只用了三个星期。深谙俄罗斯精神特质的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19世纪60年代一名虚无主义者正是从他的无神论中造出他的神性绝对物的。”
从20岁起就被《群魔》纠缠的加缪在相隔一定的历史距离后,做了更普遍、更感性的描述:“这些灵魂不能够爱,又为不能爱而痛苦,虽有愿望却又不可能产生信仰,这也正是今天充斥我们社会和我们思想界的灵魂。”并且坦承:“他们同我们相像,都有同样的心灵。”加缪将《群魔》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基里洛夫的自杀逻辑“谁如果仅仅为了战胜恐惧而自杀,谁就证实了人的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谁就立刻成为上帝”成了《西绪福斯的神话》的核心。

在小说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一种复活的期待(《罪与罚》和未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以类似的情景结束)。通过教育了群魔的教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临终忏悔,陀氏讲述了《路加福音》中的一个故事:附身于病人的鬼被驱逐出去,附在一群猪身上,猪群奔跑,落水而亡,病人坐在耶稣身旁,已经康复。通过这段经文,陀氏表达了《群魔》的主题:当虚无主义导致人的一种彻底败坏而自我毁灭之后,人将获得新生。虚无主义的群魔使自身成为对新生的献祭。这一逻辑在尼采思想中的对应物是极端异化后对超人的呼唤,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具体规定为“无救之为无救,正指示了得救之路”。
再回头说说这本小说的译名。小说的德译名是Die Dämonen,也被解释性地称为Geister。Dämonen是一个源于希腊语的词,指人神中介的精灵,在基督教传统中则用来指称撒旦及其附庸诸魔,而在德国18世纪古典主义运动时期却又成了天才的代名词。Geister的词根为“精神”(Geist),一般译为精灵,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副标题就用了此词,即“一本献给自由精灵之书”(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娄自良先生译作“鬼”,大概更多地考虑的是那段《圣经》经文中的意思,但就全书而言,似不如“群魔”妥帖。

杨不风 著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2018年
来源:三辉图书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