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游行。欧洲媒体也是一片哀声,卫报社论称特朗普的胜利对全世界都是黑暗的一天,还有评论称特朗普当选相当于三个"Brexit"(英国退欧)。本文首发于10月12日,作者的分析颇有深度和预见性,因此重新刊载与各位分享。
人们通常更习惯用故事来思考,而非事实、数据或图表,并且故事越简单越好。自由主义的叙事(the Liberal Story)已主导这个世界多年,这一故事简单而富有吸引力,但现在正面临崩解的命运。然而,唐纳德·特朗普来了。
自由主义叙事声称:只要我们推动政治及经济体系的自由化及全球化,等待着我们的就是人间天堂,或至少所有人都将享有和平与繁荣。根据这个故事——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它,只是细节上略有不同——人类必然要向一个实行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球社会迈进。
然而,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个故事的主线逐渐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人们还期待遵守全球化的规则能够令他们的境况得到改进,如今却突然开始担心自己被骗了,担心这一体系并非对他们有利。“阿拉伯之春”已变成“伊斯兰之冬”;莫斯科、安卡拉和耶路撒冷的威权体制正在抛弃自由民主的价值,拥抱大国沙文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即便是身处西欧这座最为坚固的自由堡垒的人民,也开始有些三心二意。
如今,这股幻灭感正在席卷美国,而正是美国曾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叙事推向全世界,有时甚至拿着枪推行。美国公民们失望于多年来的承诺及保证(未能兑现),在这种幻灭之下极有可能将特朗普送入白宫,建制派政治精英们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和震惊。

人们为何对自由主义的叙事丧失了信心?一种解释是,它确实已经沦为了骗局,自由主义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是暴力与贫穷,而非和平与繁荣。不过这种说法很容易被反驳。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人类目前所享受到的和平与繁荣之程度显然是史无前例的。在21世纪初,因暴饮暴食而死的人其数量超过了因饥饿而死的人,老死的人超过了因流行病而死的人,死于自杀的人比因战争、犯罪及恐怖主义而死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另一种解释则是,人们更加变得关心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了,而非沉湎于过往成就中。当你告诉他们“你们已无需像祖先们一般遭受饥荒、瘟疫或战乱折磨”时,他们并不会认为这是某种恩赐。相反,人们会列举自己的债务、失望以及永远不会达成的梦想。对一个刚刚失业的工人来说,并不会因了解到“我至少没有死于饥饿、霍乱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稍感安慰。
失业工人当然有理由担心他们的未来。自由主义的叙事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都鼓励人们抱有较高的期望。二十世纪下半叶,每一代人——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休斯顿、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都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高的收入所得。然而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考虑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某些破坏性技术成果的影响,年轻一代能够保持原状就已经相当幸运了。鉴于人们已不再相信现行体制实现其期望的能力,即便现今的和平与繁荣已属前所未有,他们仍然会产生幻灭感。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停滞不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人们其实更担心政治权力的流失。全世界的普通公民都感觉权力正在离自己远去。由于各国都较以前更加依赖资本、商品及资讯的全球流动,无论是英国、希腊还是巴西,甚至包括美国政府,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可以塑造自己国家未来的力量。此外,身处21世纪,许多重大问题是全球性的,我们传统的国家组织体制已难以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尤其威胁着各国政府及普通公民手中的权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各种可怕的后果,例如狄更斯笔下悲惨的的煤矿、刚果的橡胶种植园等。政治家和公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将进步的列车推到更加良性的轨道上。时至今日,我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与蒸汽时代相比没有太大改变,但科技方面却已迎来第四波革命。技术革命大大地超过于政治进步的速度。
互联网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如今,网络对于日常生活、经济运行和安全都至关重要,但在其诞生之初,它的设计规范和基本功能可没有经过什么民主程序——你曾经就网络空间的形态投过票吗?网络设计者早年做出的决定意味着,如今的互联网成了一个自由的、没有法律的领域,它侵蚀国家主权,无视国界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它破坏了隐私,并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巨大风险。各国政府及公民组织已就如何有效治理互联网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政府的慢速无法跟上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可能见到更多的类似“互联网”的革命,技术会悄然无声地影响政治。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不仅会彻底地重塑经济及社会运行的方式,也会重塑我们的身体与心智。然而这些话题在目前美国总统选举中几乎不被提及。(第一场电视辩论当中有提到破坏性技术,但都是围绕希拉里的“邮件门”在谈,除此外在讨论就业岗位的减少时,两名候选人都没有提及自动化的潜在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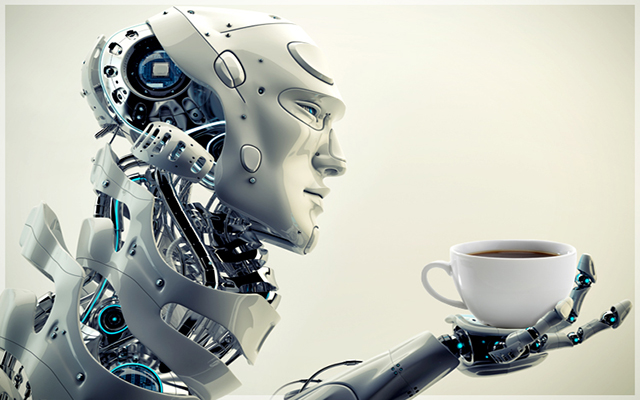
普通选民可能不理解人工智能,但他们可以感受到民主机制不再能赋予他们权力了。在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事关民众及其后代未来的重要决定既不是由欧盟官僚,也不是由华盛顿的说客作出的,而是掌控在工程师、企业家及科学家们的手中,这些人甚少意识到他们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并且他们不代表任何人。然而,选民们看不到他们,也无法向他们表达自己,所以只能尽情地抨击。在英国,选民们想像他们的权力已流向欧盟,于是投票支持脱欧。而在美国,选民们则想象“建制派”垄断了所有权力,于是决定给这个体制致命一击,以证明自己还有说话的份儿。特朗普因此成为了最佳人选。正因为特朗普令主流精英感到匪夷所思,选择他乃是普通选民证明自己在这个体制中仍然保有一些权力的理想途径——如果把这个“权力”的范围限定在制造混乱上的话。
这已经不是自由主义叙事第一次面临信任危机了。在它取得全球性影响之前,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它就已经遭受过一次阶段性危机。当帝国的权力政治阻断全球追求进步的步伐时,第一波全球化及自由化进程就终结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当中。这就是所谓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时刻”(即奥匈帝国皇储,其被刺杀成为点燃一战的导火索——译者注)。然而自由主义仍然挺过了这次冲击,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长,诸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国联及“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指代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文化亦随之兴盛——译者注)即是其明证。
接下来就是“希特勒时刻”,在1930-4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的风头看起来几乎不可阻挡。它指责自由主义否定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导致人性堕落。这套理论的鼓吹者声称如果所有人都被赋予同等的价值和繁衍机会,那么优胜劣汰就将失去效用。真正满足适者生存之要求的人类应当是出类拔萃的,不进化为超人,人类就将灭亡。不过,自由主义最终证明了自己更适合生存。

在20世纪50-70年代,凤凰涅槃的自由主义面临着自左翼的挑战,姑且称之为“切·格瓦拉时刻”。法西斯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叙事软弱而堕落,社会主义者则批评自由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无情的、富有剥削性且种族倾向严重的体系的遮羞布。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自由”意味着“财产”。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产和上层阶级所坐拥的财产和特权的掩饰。你有居住的自由,但你根本付不起房租,有学习你感兴趣的专业的自由,但无力担负学费;有去你想去的地方旅游的自,但你买不起车,那自由又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人们视自己为独立的个体,这阻碍了人们团结起来推翻压迫着他们的制度,从而使不平等延续下去。
鉴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许多来自左翼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至1970年,联合国已有130个成员国,仅有三分之一是自由民主制,而这些国家大多又是老牌的殖民帝国。看起来,自由民主制就像是年迈的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俱乐部,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世界其它的地方,甚至对本国的年轻一代也没有。
很大程度上核武器挽救了自由民主制。根据北约所遵行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ral assured destruction)原则,即使苏联仅用常规武器发起进攻,也将遭到核武器的全力反击。在这道可怕的盾牌后,自由民主制与自由市场经济在最后的堡垒中保住了阵地。西方人享受着性、毒品和摇滚,并享受着洗衣机、冰箱与电视。没有核武器,就没有披头士,没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没有遍地开花的超市。不过,到了1970年代中期,尽管核武器仍旧存在着,但未来属于社会主义。1975年4月,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军直升机从西贡美领馆的屋顶上救走最后一个美国人的画面,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美利坚帝国已开始陨落。
但事实上崩溃的是共产主义。在1980-90年代,自由主义的叙事再度爬出历史的垃圾箱,洗净全身并征服了全世界。超市被证明比古拉格远为强大。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叙事的适应性及灵活性超过了任何一个对手。通过吸收对手某些最好的理念及实践(例如政府资助的教育体系,医保及福利体系),它战胜了传统的帝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到1990年代初,思想家与政治家均宣称“历史的终结”,自信地认定过去所有的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已获得解决,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乃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在斐迪南、希特勒和切·格瓦拉之后,现在我们面临着“特朗普时刻”。不过,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像像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那样具备一套连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特朗普时刻”乃是一场虚无主义的滑稽剧。特朗普没有意识形态的主张,而支持英国退欧的人们也并未对未来有什么完整的筹划。
从一方面看,这也许意味着自由主义目前的信任危机没有以前那样严重。说到底人们还是不会否弃自由主义的那套叙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替代品。他们或许会狠狠敲击这个体制,但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他们还是会回来。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许会“往后看”,从其它的叙事当中寻求庇护,如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叙事,尽管它们在20世纪逐渐边缘化了,但从未被完全放弃。而这也正是中东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抬头。然而,这些思潮尽管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但诸如“伊斯兰国”这样的运动严格来说也并不成为自由主义的替代性选项,因为它也没有为我们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
当人工智能在许多认知性工作中超过人类时,劳动力市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由大量的在经济上变得无用的人群组成的新阶层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纳米科技及再生药物的兴起对亲密关系、家庭和退休金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当生物科技令我们能够进行精心“设计”婴儿时,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人类社会将会发生什么?你无法在《圣经》或《可兰经》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原教旨犹太主义者或是基督教基要派也许能够在席卷世界的科技与经济风暴中提供某种确定性,但要挺过这场海啸的话,你同样也需要好的地图和强壮的舵手。
这一点对如“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请将国家交还给我们”(Give Us Back Our Country)等口号是一样。你可以建一堵墙把墨西哥移民挡在外面,但不可能挡住全球变暖;你可以让英国脱离欧盟,但不可能断绝伦敦和全球金融流动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抓住已经过时的民族或宗教认同,那么全球体系将很快在气候变迁、经济危机和技术破坏的冲击下崩溃,而19世纪的民族主义神话或中世纪的虔诚既无助于认识这些问题,也无助于解决它们。
英国退欧、特朗普的崛起,令主流精英一脸惊恐,他们希望大众能够恢复理智,及时地回到自由主义的轨道上来,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但现在这一波信任危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对付过去,因为自由主义叙事背后的自由主义道德信条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传统同盟正在逐渐消散。自由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如此具备吸引力,乃是因为它告诉政府和民众无需在“做正确的事”与“做聪明的事”之间左右为难;保障人类的自由不仅是道德律令,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英法美三国之所以繁荣,就在于它们的社会与经济高度自由化,如果土耳其、巴西或中国也想变得与它们一样发达,就必须遵循同样的路径。在大部分情况下,令独裁者和军政府不得不改革的理由主要是经济上的,而非道德论证。

然而,在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全球变暖,以及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性作用,而自由主义的叙事对此似乎并不能提供很好的应对方案。在算法和机器人面前,普罗大众似乎丧失了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保障人类所享有的自由或许仍然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但仅凭道德辩护就足够了吗?假如珍视每个人的自由及希望并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政治精英和政府还会坚持它吗?大众对未来感到恐惧并没有错。就算唐纳德·特朗普败选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会有这样一种直觉:即现有的体制不再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也许是对的。
无论谁在大选中获胜,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任务: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安定催生了二十世纪的各种新生意识形态一般,即将到来的生命科技与信息技术革命也需要我们具备全新的视野。在《人类上帝: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这本书当中,我对正于硅谷中逐步形成的新兴意识形态就有所考察。假如自由主义的叙事承诺了全球化与自由化将会带来拯救,那么这套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则承诺大数据算法将带来拯救。只要有足够的计量生物学数据与充分的计算能力,一项外部算法将能比我们自身更加了解人类,而民主选举与市场经济——与那些威权独裁者与顽固不化的宗教领袖一样——则将逐步成为过时的事物,就如同之前的锁链甲和燧石刀一般。
目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专家呼吁在儿童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算法(例如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一名人工智能导师),或用算法对抗肥胖症(你的手机能够为你分析出合适的食谱),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物联网将会处理它们)。进一步地看,算法的广泛运用可能会带来正反两面的潜在影响,从良性的,到令人悚然的,到彻底异托邦的影响都有。我怀疑那些硅谷专家们是否已对这一发展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有充分的思考,但至少他们在思路上是新颖的。当人类变得对全球性的巨变不够敏感,当旧的叙事崩溃留下一堆空白时,我们就需要开拓新思路——并且要快。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仍处于幻灭与愤怒的虚无主义时刻,人们已丧失对旧的叙事的信任,并尚未建立新的叙事。这就是眼下的“特朗普时刻”。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