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8月,Bob Dylan出版了他的第32张录音室专辑《Modern Times》,名利大丰收。论电台及听众接收度,这张作品一举冲上美国及7个白人国家的排行榜冠军,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典等流行音乐大国也至少占第三名;计销售,头两个月它在全球就卖了4百万张。评价上,有4个权威性的专业杂志给了满级分;以吝啬锐利闻名的评论界大佬Robert Christgau也难得地赞以最高等级的A+,再次确认他是最伟大的摇滚乐创作者,说此专辑“散发着年迈大师的老练祥静以及知天命后的从容”。在滚石杂志2012年出版的“摇滚乐史最佳500张专辑” 中,它列名第204;发行仅仅6年,获致如此高的历史地位,亦属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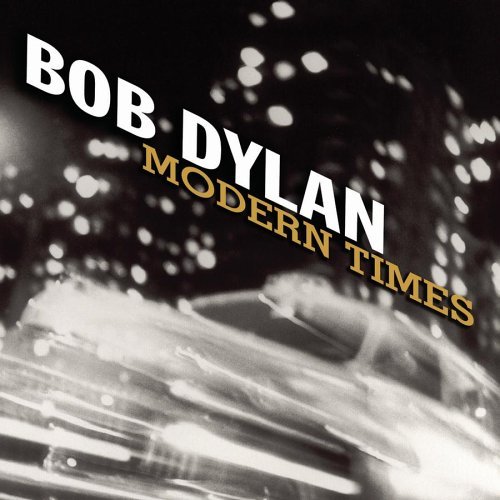
这张专辑真正令我吃惊并引发思考的,是它另一项更有趣的成绩: 作者以65岁创下美国排行榜冠军的最高龄记录。不管创作或演出,摇滚乐是个高度耗损精力的行业,一年老三岁。1976年,英国的前卫摇滚乐团Jethro Tull发表第9张专辑时,团中主要的创作者Ian Anderson感到一种别扭的心理状态: 一方面,他们功成名就,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回报;另一方面摇滚乐风格演进的速度飞快,十年不到,68年创团时号称前卫的音乐形式现已显得迟暮西山,而生理上,他们连中年都还不到——Anderson当时才29岁。他诚实面对这种尴尬,把专辑定名为《Too Old to Rock n’Roll: Too Young to Die!》,不无自嘲之意。因此,Bob Dylan的65岁已远非高龄,简直是人瑞级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创作者,他的成功通常会被归因于天分,然而65岁第32张专辑!除了天分与不懈的努力,不能不追究他的方法。
虽然号称西方民谣百年一遇的天才,整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Bob Dylan长期陷入创作方向上的困境,期间产出的11张专辑,排行榜及评价均属中庸之作。从1997年《Time Out of Mind》专辑开始,他逐渐回归并精磨早年的手法。众所周知,Bob Dylan的创作基础,是对于美国白人民谣与黑人蓝调的临摹。与Bob Dylan同世代的文化研究者Lewis Hyde统计,1961至1963年间他有50首作品是对美国经典民谣的再诠释,占了当时作品量的2/3。临摹传统,在60年代美国民谣复兴运动中蔚为风气。但Bob Dylan在纽约还受到欧洲左翼前卫剧场的影响,使其酝酿出以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及疏离美学为核心的思路与表现手法,接合且极究了美国40年代的民谣参与社会运动精神,进而凸显了他的独特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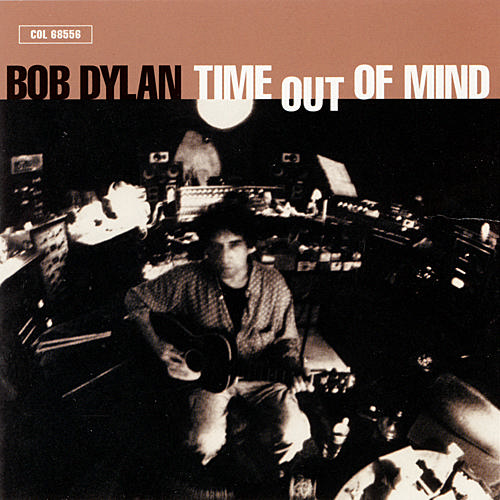
到了《Modern Times》专辑,Bob Dylan卸除了意识形态负担与形式焦虑,此时他对于民谣资产的再利用手法,舒缓中益趋精妙。专辑十首歌中,有明显再创作痕迹的多达九首,不过已非早期针对一首曲调的单纯操练。此时他已臻信手捻来的境界,大多只取撷前人作品的一小部分词、副歌、主奏吉他或贝斯的旋律,加以变化、糅和、发展,甚至加入自家以前作品中的某些元素,或在一首多人演绎过的曲子中掺进新的玩法。又像是生化科学家,只要从生物体中取出细胞或基因,便能培养出活跃的演化新种。他的脑子像一间内容庞杂的传统音乐档案馆,他蹲踞其中,或编辑或挪用或重组,得心应手。而且,大师无一注明出处。
剽窃、不尊重原作者?专辑发行后,种种指控、怀疑纷至沓来。

Bob Dylan一向敬重他的灵感源头,但这回他却反之。我暗想,他之不标明元素身世,会不会是出于对《版权》 这种私有化意识形态以及由之而起的司法诉讼的无言抗议?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民谣音乐史上,民谣的演绎与承传从未涉及《版权》。版权,与其所衍生的概念《创新》,大体是西方工业革命——特别是在科技产业兴起后,为了确保投资获利与维持竞争优势而固化的观念。流行音乐的工业化,势必造成版权概念的法律化,进而对这种即拿即用、民谣先锋Pete Seeger所谓的民谣过程(Folk Process)形成干扰。Bob Dylan全然不甩版权与出处,也许正用以宣明他重返民谣传统。
对于这种档案管理员式的再创作技法,Bob Dylan倒是从来不避讳。他自谦不擅长写旋律,他的构思方式是在脑子里选首歌,在生活中不断聆听、对之絮语,到了某个临界点,词曲发生变化,一首新歌于焉成形。这除了显示既有作品的搜集、品味与再创作是一体多面外,还指明: 一位音乐家再怎么天才,都不可能拥有无尽的形式创造力,除非他懂得与传统对话,接续前人的演创,并从中提炼写作灵思。一位在六七十年代引领时代风骚的民谣歌手,暮年之际尚能再添风华,所依恃者,正是愈磨愈有味的再利用技术与艺术。
很难想象,相似的这条民谣路,十四个世纪之前,杜甫早已出色地走过。
二千一百五十几年前,汉朝第七任皇帝刘彻下令成立乐府,除负责为宗庙外的祭仪与舞蹈制定音乐,还职司民谣采集。这一道行政命令,影响了日后大部分汉语系民谣的词句架构,说得时髦一点,形塑了中国的民间音乐面貌。历史上,汉武帝刘彻不是第一个设立音乐专职机构的皇帝,他所设立的乐府也不是第一个搜集各地民谣的官署。但是,较诸前朝,刘彻的乐官们所采集的民歌出现大量的奇数构造: 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乃至九言。而且,相对于诗经,乐府民谣在文体上更趋向于叙事化,语言上更加反映平民大众的质朴,内容上更立体地呈现劳动者的爱憎与苦难。

从西周末期到汉初,中原经历了几个大变化: 一是生产方式更加远离狩猎采集,趋向定居化的农耕文明;二是世袭的贵族政体逐渐失衡、裂解;三是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与大举移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解体与再结构,当然会反映在民谣的多样演变上。但对于官定的乐府民谣,这只是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汉朝的奠基者刘邦为南方农民出身,自然乐于引入楚声,改造宫廷音乐。及至汉武帝,更广征天下民谣,不仅是向平民进行文化输诚以厚实统治合理性,更藉各地民意以提升其治理上的警觉度。
另一方面,乐府化的民谣更具备了政治正当性,从而对文人的社会认识与写作产生示范作用。比起诗经与楚辞的呆板二言构造,乐府诗的奇数结构更富变化与节奏感,更适于表现深刻的情感、复杂的情绪、冗长的情节,以及变动的人际关系、社会观与生命哲学。来自民间的歌谣经过训练有素的文人官僚整理后,又向下普及民间,影响民间的歌谣创作,如此往返。在杜甫写下第一首诗之前,在官方的背书与机构支持下,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与平民的民谣创作之间不断地交流与互渗,延续了整整八百年,形成世界文明史上罕见而进步的文化生态。
二
1918年2月,五四运动前一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刘复、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常惠等人,着手征集各地歌谣。他们的征集方式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既非诗经、乐府时代的文人寻访,也非西方现代的专家采集。受他们感召,北大校长蔡元培号召全校教职员、学生协助搜集全国近世歌谣,并致函各地报馆、学会及杂志,请其广为宣传。用了近七年的时间,他们回收到11000多首来自24个省区的民谣。
这是史诗般的行动!想一想,有多少人受到鼓励,启程回返童年与故土。他们客观而恭谨的采访态度一定让识字无几的母亲又惊又喜,而母亲一开口,他们豁然见识到绵长的记忆之河;他们可能翻山越岭或勇敢地跨过身份的尴尬,采访传说中的民谣能手;他们之中可能有人发现,民谣原来是集体流传与个人创作的神秘结合。还有新的态度与想象;在学术机构与文化运动者的助力之下,他们以族群文化采访者的身份,再度亲炙了早年听而不闻却直入灵魂深处的民谣。
同等重要地,是从这批民谣的汇整与研究中,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者梳理出近代中国的人文地理,并以新的视野审视中国古文明。譬如,考古学家董作宾从中发现了45首同一个母题的歌谣,至少涵盖12个省区。董作宾是杰出的甲骨文学者,有着深厚的考古学、文字学及语言学等方面的素养。搭衬着如此丰富的知识背景与罕见的专业配组,使得他的专著——《看见她》,成为有趣、启发性极高的民谣研究经典。他认为这类歌谣应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在陕西三原,人们如此“看见她”:
你骑驴儿我骑马,
看谁先到丈人家,
丈人丈母没在家,
吃一袋烟儿就走价。
大嫂子留,
二嫂子拉,
拉拉扯扯到她家;
隔着竹廉望见她:
自白儿手长指甲,
樱桃小口糯米牙,
同去说与我妈妈,
卖田卖地要娶她。
对照其他各地以“看见她”为动机的民谣,一幅民谣的旅行地图便生动活现地展开了。沿着水路交通,它们在路上骑白马,到了水国就撑红船。随着地理、风俗与语言的差异,每个地方的“她”有着不同的容貌、装饰,描述上各有春秋。领会了民谣所呈现的美妙灵思,董作宾不禁赞叹民谣之为文艺,“是一种天才的表现,……虽寥寥短章,……皆出自民俗文学家的锦心绣口。”

董作宾的赞叹颇能说明当时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翻转: 民间歌谣素为传统文人所鄙夷,现反被高举至学术殿堂,视为艺术珍品。再加上鲁迅、胡适等代表新时代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国民教育、国语文学的高度呼吁搜集、整理各地歌谣,许多大学者遂纷纷投入。董作宾乃针对民谣于地理空间上的横向迁徙,另一位学者顾颉刚则专注一地区的民谣于时间轴上的纵向演变。
呼应这场新文化行动,顾颉刚对自己的故乡江苏,展开了民谣的搜集与分析工作。1924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32期,之后并出版专册。顾颉刚差不多动用传统国学研究的全部专业,科学又热情地面对家乡的歌谣传统。集子录有百首歌谣,顾颉刚为之注解与考据的态度无异于面对四书五经,对当时的老学究而言,其荒诞程度绝对胜过用物理学研究童玩。更启人神往的,是他的诠释往往精妙地展现了常民观点;譬如在一首题为“摇大船”的童谣中,顾颉刚注道:“凡儿歌言摇船者,均系手接手推挽若摇船之状时所唱。”
从民谣出发,并把握常民的生活观点,顾颉刚还帮现代读者还原了诗经中的民谣本色。譬如在《甲集》的《附录》中,顾颉刚讨论了《野有死麕》这首诗。其第三段,诗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顾颉刚比较类似动机的江苏民间情歌,如《甲集》中的第68首——“轻轻到我房里来,三岁孩童娘做主,两只奶奶嘴子塞,轻轻到我里床来”,推断它原是描述男女交欢的情歌。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女要男慢慢来,不要弄乱她身上的配巾,不要惹狗吠叫。而朱熹却说此段是表明女子“凛然不可犯之意”,硬把女性的怀春说成贞烈。因此,顾颉刚揶揄道:“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真正进入民谣的脉络后,顾颉刚很清楚地辨识,在诗经的注释中,儒家道学是如何凌驾诗学。
从诗经的诗学讨论中,顾颉刚几乎要触及民谣的心灵。同样在《附录》中,他重新审视朱熹对诗经分析方法“六义”之一“兴”的定义。兴者,按朱熹界定,先言他物以引其所咏之词也。放到现代文学,“兴”接近具有逻辑性的联想。而朱熹及历代的注家常从道德观点出发,解释“兴”的逻辑。譬如,诗经首篇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熹如此解释“兴”的作用:“雎鸠,水鸟……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不相狎”,因此淑女不仅匹配君子,且他们相处“和乐而恭敬”,像水鸟“情挚而有别”。

加上其他类似的例子,顾颉刚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兴”作为分析方法,常有适用模糊之处。以“关关雎鸠”为例,美学上其实更接近“比”,但进一步细究又不太像是严谨的比喻。其二,诗经中民谣属性明显的诗篇,如出自国风篇者,似乎不全然能套用伦理逻辑。关于后者,顾颉刚以其所搜集的江苏童谣,指证历历,譬如“萤火虫,夜夜红;亲娘绩苎换灯笼”、“一朝迷雾间朝霜;姑娘房里懒梳妆”等,不胜枚举。事实上,日后的研究也阐明,“反逻辑”、“去逻辑”甚或“调侃现实逻辑”是民谣的通性之一。环顾世界的民俗学发展,要到1962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1908—2009)发表《野性的思维》一书后,我们才逐渐知道,这些看似无逻辑可言的初民神来之笔,仍可透过分析,窥探人类的心灵结构。但在20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刚起步,顾颉刚指出古人说话的“支离灭裂”,其洞察力之锐利,论述之敢言人所不敢,也正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勇于向时代提明、与既有意识形态诘辩的革命气氛。
起于1910年代的这场民谣复兴运动,为五四运动及日后左翼运动中“到民间去”、“向农民学习”的实践方法,奠定了向下延伸与认同的文化理论基础。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时代巨变、社会动荡,怀抱淑世热情的文人转向民间,重新认识时局,并向民谣学习新的论说与创作方法,本就是一个长远的传统。公元758年6月,杜甫被贬,在安史之乱中离开长安,展开了他的公路歌谣之旅。
三
民谣传统往往在灾年、战乱或社会变革中,与忧国恤民的知识分子野合,生发成激楚的当代化过程。
1930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俄克拉荷马州发生连年的大干旱,天灾与人祸加乘,逼使大量无地农民迁徙,寻找活路。二十出头的民谣歌手Woody Guthrie随乡民向西出逃至加州,见证了农业大资本与银行业连手发动的土地兼并、其对小农与佃农的层层盘剥以及大农制生产方式对环境的毁灭性后果。路上,逃难的艰辛风景、吃人的体制与游民的行吟在歌手的心灵中交织,促使他写出美国现代民谣史上的开山之作《Dust Bowl Ballads》(沙尘暴纪事)。
1940年出版的《 沙尘暴纪事》在叙事者、当事者、阅听大众之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对话深度与向度,影响了日后众多优秀歌手。这张专辑有几项开创性的特质。首先是对事件的实时报导——专辑出版时,大萧条尚未完结,而Woody Guthrie所描述与批判的社会现象也正愈演愈烈,其反应之专注与迅速,有助于吸引注目、激起公众讨论。其次,是观察的眼光与叙事的口吻——纪实中的说故事者,其角色既涉入又疏离,有时是客观的全知者,有时是苦难者的集合体,易使听者产生半是宗教半是理智的关怀热情。再者,曲调上Woody Guthrie参考了当事者生活其中的传统音乐——小调、摇篮曲、福音歌等等,使得内含大量讯息的歌词得以藉着文化亲近性,抵达受众的良知。还有,在歌词的写作上Woody Guthrie增添了新意,譬如用肺病的诊断写沙尘暴之折磨生命、用银行抢匪写社会不义,其切入点既悲天悯人,又跳出人道主义的俗套,为民谣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了呈现的更高境界。
以上都还只是创作方法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生命态度。终其一生,Woody Guthrie不满足于安全的、远距离的观察与关怀,坚持参与到社会运动或事件的最前线,理解问题的症结,与群众同悲共苦,用创作发声,引发舆论关注,争取公众支持等等,为1960年代的激进民谣运动塑造了人格典范。另一方面,他不安于室,用尽各种办法上路,行旅祖国山河,体验人生,于途中记录、创作;这种滚动式的写作态度,早在嬉皮运动之前,就已创风气之先。70年代之后,街头复归平静、庸俗,那些受惠于民谣运动的歌手尽管名利双收,不少人仍剔励自己莫废初衷。他们或投身实践理想,或持续以创作批判现实、声援社会变革;溯其源,正是Woody Guthrie的遗绪。
1963年5月,Bob Dylan出版第二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Bob Dylan自在优游)》,不管从民谣运动、反战运动或现代文学来评价,均是精湛之作,而且出版时,他尚差3天才满22岁。之后,他以惊人的创作能量,3年内创作5张专辑,以犀利的激进批判为高张的社会运动助阵,以高明的音乐性响应民谣与蓝调复兴运动,以前卫的文学性呼应英美的现代诗歌运动及纽约的前卫剧场运动,将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推上巅峰。

但天才的实现除了时代的条件,更需要前人的累积。在杜甫之前,乐府诗历经数百年的搜集、整理、研究与传播,到了战乱频仍、政治与思想中心解析的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带有边缘性与叛逆性的文人如曹操、曹植、曹丕父子,及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傅玄、张华、石崇、刘琨、蔡琰等,常藉社会写实进行政治论述,是其时,乐府诗体中丰富生动的民间性成了时代的首选,他们以之为发声的依靠。这些新创的乐府诗——经典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蔡琰的《悲愤诗》等,为继起的唐朝诗人开启了一扇惊奇之窗,既让他们看到乐府诗形式与语言的巨大后坐力,又为他们展示了如何以民间声学,将政治见解、时代特征与社会关怀等表现面向织育为可攀爬可路跑的新文学体,向上为诤言,向下为风谣。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人之于杜甫,正如同Woody Guthrie那一辈的激进民谣实践者之于Bob Dylan。
从周天子命采诗官四出搜集民歌,蔚为“不学诗,无以言”的风气,至汉武帝立乐府采集歌谣,形成“为时而着,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创作风潮,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多年;不管是从世界政治史、文学史或音乐史来看,皆是惊人的早慧之举,其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恐怕要超过后来的四大发明。理想上这是明君藉风谣以观民情、知得失并自我匡正,实际上是民间的材料经过官僚及文人的编辑后,形式及音韵上更为严谨规律,并渗入政治伦理与礼仪规范,从而变身为教化百姓的媒介。司马迁不仅看出诗经编辑过程的政治性,还指出其复归音乐、以利宣传,故云:“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者……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世学者对孔子删诗说容有疑义,但对其过程的特点,倒有共识。
中国因此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学社会机制。文人受感染,内化为重视民谣的风气与传统。民谣既是观察社会舆情的窗口,对其进行理解、诠释与再创作,亦为文人养成学术与写作的必经之路,及评量重要性的依据。文学上,民谣从四方、由下而上地向京畿汇集、整编、出版,使民谣得以保存、流传,既延伸、具象化了文人的国家想象,丰富他们的社会视野,又为其提供创作养分。经过文人润饰的民谣,带着更精炼的美学与校正过的思想内涵,回返民间,与各地的风土、脉络杂交。文人从而成为中介体,使国家组成的上/下、中央/四方之间得以进行政治与文化上的交流、对话;这或许是千年来中国得以维持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充分条件。
类似的过程与机制出现在两千年后的美国。从19世纪末至1960年代,在国会图书馆及出版业者的支持下,美国民谣搜集/研究/出版/演奏者John Lomax(1867—1948)、Alan Lomax(1915—2002)父子对美国民谣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录音,并进行档案归纳、研究与出版。John Lomax为国会图书馆成立的《Archive of American Folk Songs》(美国民谣档案)覆盖了33个州,富涵多元的地域、职业、种族与信仰特性,在学术研究、公众聆听及文化学习上均引动了广泛的兴趣。但他们的志业不囿于此。
儿子Alan Lomax成长于美国最为左倾的年代,他对运动性民谣以及反映劳动者与低下阶层生活特性的歌谣特别重视。1939年底,Alan在全国性的电台上系统性地介绍美国民谣宝库,并现场演唱Burl Ives、Woody Guthrie、Lead Belly、Pete Seeger、Josh White、及 the Golden Gate Quartet等活跃歌手与团体的作品。这些节目直接于学校的课程中播放,受惠的学生多达一千万人,对年轻世代的民谣学习、文化兴味、社会意识与民族想象等等,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Alan Lomax见识到民谣运动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力,开始对三四十年代激进歌手的实践历程进行访谈,并录制、出版他们的民谣演绎与创作。50年代初,Woody Guthrie受家族性遗传疾病亨丁顿舞蹈症干扰,行动能力恶化,未久美国又陷入恐共的政治局势,活跃的民谣乐手受到监控。多亏Alan Lomax,美国第一批现代民谣歌手的进步作品得以保存下来,并至少能在藏家与图书馆流通。到了1959年,局势稍缓,他又与Pete Seeger、Theodore Bikel、Oscar Brand及Albert Grossman等民谣运动推手合作,举办Newport Folk Festival(新港民谣音乐节),安排他所采录过的重要民谣、蓝调歌手走出被遗忘的角落与年代,面对全新的民谣世代。第二年,Bob Dylan就在这个音乐节的舞台上初试啼声,迅速引发民谣革命。
这样子的承先启后,Bob Dylan与杜甫多么类似!
放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成就的境界显而易见,诸如政治性、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精致统一,批判性的高超艺术概括,形象、景象与情感、思想的相互渗透,复杂而幽微的心理描述,精准奇丽的炼字锻句,以及文词中丰富的构图与造乐等等,众注家与评家早有定论。读杜甫的乱世作品,其一生纠结在儒家君臣伦理、国家主义、人道主义、淑世热情、家庭责任与创作欲望之间,不断遭逢悲剧,又持续创造惊奇。杜甫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与期许,行旅于浊世凶年,像个报导文学家,不断记录途中的见闻并表达关切。以民谣运动的历程观之,杜甫以自身为媒介,接合文人文学与乐府诗歌传统,展衍出广阔壮盛的对话。
四
Bob Dylan的2006年专辑《Modern Times》佳评如潮,但其词曲中援引的传统民谣或前人作品,并未注明出处,因而招致多方诘难。Bob Dylan没有回应质疑,大概他从来就认为,民谣的传统中,没有“注明出处”这回事。他的静默并不寂寞,60年代民谣运动中的另一位重要歌手Ramblin Jack Elliott(1931—),亦从源远流长的民谣脉络看待此事,他说:“Dylan从我这儿学到的方法,是我从Woody Guthrie那边学来的;Woody没有教我,他只说,如果你要学点东西,就用偷的;我从‘铅肚皮’(Huddie William Ledbetter,1888—1949,美国民谣与蓝调歌手)那儿学到的,就是这件事。”Pete Seeger也说过同样的事,他回忆Woody Guthrie曾指着他向旁人说道:“这家伙偷了我的东西,但我的东西是向众生偷来的。”
杜甫也偷,而且偷得更凶、更广、更绝妙。感谢后代数百位注家的爬梳,杜甫如何因陈出新,吾人得窥一二。早年诗作《题张氏隐居二首》,首联“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以声音切入,带出风景之纵深,简直是电影中的摇镜手法。据清初的仇兆鳌汇整,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其参考来源可能涵盖南北朝诗人庾信的诗句“春山百鸟呜”、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刘琨的诗句“独生无伴”、南朝诗人王籍的诗句“鸟呜山更幽”、诗经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及易经“同气相求”。杜甫像个魔法师,消解前人的文字碎片,吐出景深更远、人味更浓的诗句。
再如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写西域来的汗血马,把北魏贾勰论骏马的“马耳欲小而锐,状如斩竹筒”及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形容曹操麾下大将曹洪坐骑英姿的“耳中生风,足不践地”,糅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不仅文字练达,形象精准,且速度感跃然纸上。到了《暂如临邑至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中的“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中年的杜甫藉以表现速度感的意象与意象间的联系,更加纷陈紧凑,令人目不暇接。转化,是诗意表现的基本要求,而杜甫在基本功上所呈现的出神入化天分,惊人至极。
终其一生,倒装句法是杜甫进行诗意铺陈与转化时,最重要的手法。晚年客蜀期间所写的《登楼》中,首、次联“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运用倒装法,将情绪嵌入动态的风景,焊溶时代感、意象与空间感;诗人的历史心灵,色彩斑斓。
倒装法在杜甫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前卫感。但倒装法并非出于杜甫的文学实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人就已广泛运用,著名者如影响杜甫极深的鲍照(414—466)。读鲍照的民谣形式作品,如《采菱歌》:“要艳双屿里,望美两洲间;褭褭风出浦,容容日向山”,倒装法的民间性呼之欲出。再读当时的风谣,如东晋初期的《豫州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则知倒装法根源于乐府中的问答式民谣——相和歌,亦即现代民谣研究中所说的呼唤与响应(Call and Respond)。
新乐府诗人采用民谣中的问答形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历程产生了两层革命性的影响: 第一层改变是叙说方式从第一人称移至第三人称;第二层转变是作者视野从精英中心移至黎民百姓。在这两层结构转变的作用下,新乐府诗中开始出现复数的“他者意识”,作品与读者间的对话层次因之纷杂,总而呈显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亦即群黎的多元主体性。
要知道,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独白式的史诗占据了非常长的时期,小说性质迟至16、17世纪才出现,而中国在公元3世纪初的汉魏时期,于当时的文学社群——建安七子之间,就已蔚为风气。从阮瑀(?—212)的《驾出北郭门行》表现作者与林中孤儿的对话,到陈琳(?—217)参考《陌上桑》、《东门行》及《孔雀东南飞》等对话体流行歌谣,写出小说体式的新乐府经典《饮马长城窟行》,再一次说明,中国诗学受乐府影响,至汉末、魏晋,早已众声喧哗。
杜甫从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人那里所继承的,不仅是白居易所指明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写实主义精神,同样重要的,还有写实主义的创作艺术。天宝十载(751年),困顿长安的中年杜甫写下即事名篇《兵车行》,承先启后,预示了他的所有伟大: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兵车行》是杜甫对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致敬与回应。在其创作历程中,此篇之所以重要,不只因其首度触及了生民苦难并针砭时政,且是诗人承接乐府歌谣资产并进行再创作的初啼之作,且为其后的三吏、三别等即事名篇,奠定了写实的手法。杜甫一出手就超越汉魏名家,将乐府诗体的写实艺术推高至前无古人的境界。然而,能文之人遭逢战乱,无论是反映社会苦难或批判政治败坏,汉魏以降早已辉煌见诸民间及文人的乐府诗歌;那么,杜甫要如何超越呢?
诗人回归民谣的根本: 声音、节奏与结构。《兵车行》的节奏强烈,就乐府诗而言,其撞击感之猛,宛如1970年代的英国朋克(Punk)音乐之于前一个世代的摇滚乐。此诗一开头便连用了两个三字句,使灰色系的声音场景充满了不安的氛围,接着平仄相间,绷紧文字的节奏,同时频繁变换场景与韵脚,令人感受祸乱的迫近,接着腰处插入八句五言,并起用短韵“u”,造成低回与急促感,传达男丁备受奴役的命运,最后又以长韵“ou”及“ui”,引领读者细细慢慢地咀嚼历史的悲痛。《兵车行》的音乐性丰富,不管使用哪一种汉语系地方语,读来尽皆抑扬顿挫、胸臆澎湃。
书写悲剧有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是写实,亦即掌握现实的矛盾与苦痛的细节;但真正把苦难写真了,又容易使人不忍卒睹,或读来沉痛闷抑,导致疲乏,令人急于脱逃。也就是说,写实主义文学的方法经常让它的主人到不了目的地。因此,伟大的写实主义文学家必须借助形式,在读者与文本间创造疏离的空间,使读者拥有客观的距离,以与作家产生审视性的对话;这是第二道关卡。
为达到疏离的效果,1960年代的Bob Dylan参考了两种风格: 充满边缘感的乡村蓝调(Country Blues),以及前卫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疏离剧场。同样地,杜甫从自身的民谣传统中汲取可用的元素;在《兵车行》中,他使用乐府歌谣的重要形式——问与答,帮助身陷历史场景的读者抬高视线,以作为客观的第三者。但读者刚安稳于客观的特权,杜甫又运用“君不闻、君不见”的乐府句法,将读者变为负有历史责任的第二人称。如此诱进、高抬与移位,杜甫藉乐府民谣的元素,创造了真正具有对话效果的写实主义文学。
在文学史上,杜甫早被誉为“诗史”,到了现代,更被封上写实主义诗人的称号。杜甫当之无愧,毫无疑问。然而,在诗人的创作生涯中,符合“诗史”或“写实主义”的作品,比例并不高。其大部分作品的说话对象,仍是诗友、文臣将相,以及最多的——他自己;更严格说来,前两者说的也是诗人自己。因此,确切地说,杜甫是一个务实的写实主义诗人;只有在面对时代的剧痛、不堪与涂炭的生灵,内心升起向生民大众说话的使命时,他才会动用乐府歌谣的民间形式。当然,一旦诗人起心动念,其作品便就是既写实且批判,音乐性强,艺术性高超,而对话性深且广了。
1960年代,Bob Dylan被冠上的封号也差不多属于上述性质。Bob Dylan藉由叛逆的姿态以及更多的创作,以逃离这类唯一性封号的桎梏。社会写实、批判时政或反映时代呼声,他当然驾轻就熟且义不容辞,但那并非他人生的全部。归根结底,诗人在乎的,是创作心灵的自由。杜甫若有机会表达他对这些称号的看法,当与Bob Dylan不远。

(本文选自《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