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家乐福在中国的首家门店北京创益佳店昨日闭店。1995年,第一家家乐福在中国开张,设在北京老国展旁。30年来,家乐福从一家超市变成承载集体幻想的能指——如同它所选的三个字代表的,家,乐,福——作为背景的家庭,笑声朗朗的欢乐,作为氛围的幸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型超市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共空间,人们的梦想随之更迭,更多与大型货架、鲜艳的水果蔬菜、美好家庭相关。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从后现代哲学理论视角出发,审视着家乐福的存在。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在一种妄想的语境里购物吗?它们会不会轰然倒塌?
《家乐福:语法、物品及娱乐的经济学》(节选)
作者|汪民安
名词
无论如何,“家乐福”听起来是个地道的中国词,“家”“乐”“福”,这是三个吉祥的汉字。如今,这几个汉字纷纷插入别的汉字中,同另一些字词组合、排列、串联起来,作为名称、标语,作为问候、祝福、祈祷的代码,作为最常见的情感意志的记号,既布满大街小巷,又充斥着媒体机器。对于民众而言,这是目光最经常捕捉到的字,是最日常的三个字,但也是三个圣字: 它们既浓缩了理想,又浓缩了哲学;既浓缩了历史,又浓缩了乌托邦。

这是民族记忆在当代的泛滥表现: 家、乐、福,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日常情境?这不是这个民族的集体乌托邦?这不是人们——那些在历史阴影中的人,那些在昏暗街道上徘徊的人——具体而切实的愿望?这几个频频闪耀的善良汉字使一种气质、一种意愿、一种心态暴露无遗。这是最不具备秘密的几个字,但又是埋藏真理的几个字,这是常识性的字,但又是有无限表意潜力的字。现在,它们被资本、商业和市场利用了,它们被转嫁、被改装、被招安到一些商业情境中。这些纯粹的商业行为正是通过招募这些汉字而试图掩饰它们的动机,掩饰它们的资本假面,它们将利润动机乔装起来,给这些动机添加一层光环,让资本行为诗意化,将实质性的金钱交易符号化,最终,经济行为通过某种修辞行为和言语行为而转化为伦理行为。如果说这里面只有资本的残酷消长的话,那么,这些词语就是对这些残酷性的有节奏的化解。

形形色色的广告都察觉和利用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作为背景的家庭,没有作为氛围的幸福,没有笑声朗朗的欢乐,这些广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们还有别的书写形式吗?它们还能四处渗透、驰骋吗?同那些广告一样,家乐福超市的命名并没有额外的企图,它也不是创意中的神来一笔,它符合普通的商业策略。稍有不同的是,家乐福不是强行的、凭空的命名,它采用了今天常用的翻译政治: 指称性的名词,总是采用音译,而且,是富于意图的音译。家乐福的原名“Carrefour”,这是个中性的空间和地理概念,它的准确的汉语翻译是“广场”或“十字街口”。它既不表达意识形态实践,也不表达伦理取向;它既非政治学的,亦非心理学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有浓重西方痕迹的词语。
但是,在北京,在国际展览中心的边侧,“Carrefour”大型超市,被音译为“家乐福”。根据目前流行的翻译政治学,根据少许的声音联想,根据商业策略对伦理学的习惯利用,一个中性的西方词语顷刻之间就弥漫着中国的乡土气息,既温暖又诗意。在将其利润动机藏匿起来的同时,这种翻译还掩饰了它的跨国性,这个本土化的名称抹去了异域的痕迹,它将跨国资本、跨国连锁店和本土性巧妙地缝合起来,这既缓解了隐伏在心理上的民族冲突,也消除了类似于殖民主义的创伤记忆。
因此,在家乐福购物,就不是被跨国资本所包围和吞噬,相反,我们是在一种妄想的语境里购物,在一种刻意剔除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中购物。是的,这里其乐融融,合家欢乐。此时此刻,谁又会想起,这里的一切,其起源、现实、目的都是从遥远的欧洲长途奔袭而来?
物品
低廉性和再生性,这是家乐福物品的本质。那么,它的形式呢?从体积的角度而言,这些物品都是微型的、小巧的,家乐福很少有大宗商品出售。这些微型物品通常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和展开。如果说,物类和物类之间存在人为的等级制,存在组织上的秩序机制的话,那么,在物的内部,这些复数形式的物品的布置服从于美学法则和可见性法则。同种类型的物品(如各种各样的色拉油)整齐地码放着,它们试图堆砌成一个庞大的体积,一个醒目的形式,一个夸张的图案。这些物品单个地不会产生视觉效果,然而一旦集体组织起来,它们就从沉默中、从一个隐晦的角落脱颖而出。这个醒目体积将单个物品作为材料,利用它的色彩、形状、硬度,利用它的自然材质和固有的搭配能力,来雕琢它自身的美学。
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庞大构图,它们形状各异,相互比附而又相互区分,它们各自划分了一个符号区域。这些构图不仅仅具有实际的指示功能,也不仅仅具有美学功能——它们可以对单调的空间进行装饰,可以使它更活泼、更俏皮——而且可以成为游戏对象。在这些构图中,包含着难度、心计、幽默感、无关大局的坍塌危险,这一切都使顾客产生了兴趣,他会走近它们,端详它们,抚摩它们,他可能动手挑选其中一个,他想看看它们会不会崩塌。那些像搭积木一样搭成的食品盒子,它们高高耸立,摇摇欲坠。给它们轻轻施加一点压力,它们会不会轰然倒塌?

在家乐福超市里,显现出一种真正的物的大海景致。购物者完全被物品所包围,物品将货架挤得满满的。它们将货架吞没和埋葬了,货架消失在视线之外,物品像是自己凭空支撑和生长起来的,它们就那样一排排地安静地矗立着。同时墙壁也消失了,靠墙的货架及其物品将墙遮得严严实实。这样,除了一排排平行着的物品之外,购物者什么也看不到,他像是在无边的物品体系中逡巡,看不到尽头。目之所及,是物之大海。购物者在观望,是物的目标在引导着观望;购物者在行走,是倚靠着物的背景在行走。从一个物墙到另一个物墙,从一类物品到另一类物品,从一个物的方阵到另一个物的方阵,自始至终,他走不出真正的物的牢笼。
物既是家乐福的目的,也是它的装饰品;既是它的内容,又是它的形式;既是它的材料,又是它的美学。物,是家乐福这一名词的全部所指。物品之外还是物品,家乐福不为物品添加任何额外的东西。物是赤裸的、直接的、原色的,是现象学式的。这使家乐福与另一些商店截然有别,在那些商店里——无论是诸如世都百货这样的大型高级商场,还是诸如东四的专卖店那样的小型店铺——物总是被赋予了精神背景。那里的音乐,有时是莫扎特,有时是麦当娜,有时舒缓,有时激烈,它成为物的言语,是物的间接咆哮或低语。那里的灯光,有时柔和,有时暧昧,它是物的情调,是物的氛围、光泽和气质。那里的物是中心,不过是被烘托的中心,它的周围,点缀着布景、壁画、时尚或者历史。而家乐福的物呢?它坦荡、绝对、自在。家乐福驱逐了一切的暧昧和氛围,它将物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家乐福使用的是单一的日光灯,它亮如白昼,昭示了物的绝对真理。物,是自律的,是自行敞开的,是自我存在的。这是绝对的物的现象学,它以沉默的方式,既处在氛围之外,也处在历史之外。物是中心,不过是没有布景的中心。
不是刻意的人工氛围,而是平淡无奇的标价签,不是幽雅动听的音乐,而是枯燥沉默的数字,构成了家乐福的物品语义。标价签是它的价值,也是它唯一的诉说和应答言语。标价签是物同购物者的谈判机器,它无法更改。这既是契约,也是法律,既是物的经纪人,也是物的统治者。标价签,这张电脑打印的小纸片,它黏附在物的一个小小的隐秘角落,然而,它既覆盖了物的整个语义,又揭穿了物的深邃知识。
这样,在家乐福,你就难以看到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售货员了。售货员是物和顾客的中介,是物的代言人,但是,在此,标价签取代了他的功能。这里没有问讯,也没有解答,一切都明确地铭写在标价签上。家乐福的员工呢?他们通常不是解答疑惑,出售商品,与顾客讨价还价。不,他们并不负责售出和减少商品,他们只是负责维持和添加商品。在商品被挑走之后,他们并不沉浸在出售的喜悦之中,而是陷入工作和再生产的焦虑之中: 他们必须搬运货物,随时随地维持着物的量的稳定性。这样,在家乐福,不论每天售出了多少,它的货物依然是饱和的、完满的,货架从不留出空隙。家乐福像从没出售过、减少过或损失过什么似的,永远保持着物的拥挤状态。它似乎永远是平静和一劳永逸的,从不经历波澜。就物本身而言,它似乎从没改变,从没流通,从没发生任何位移。但是,在这种稳定性下面,有谁知道,它在反复地历经着购买和销售的狂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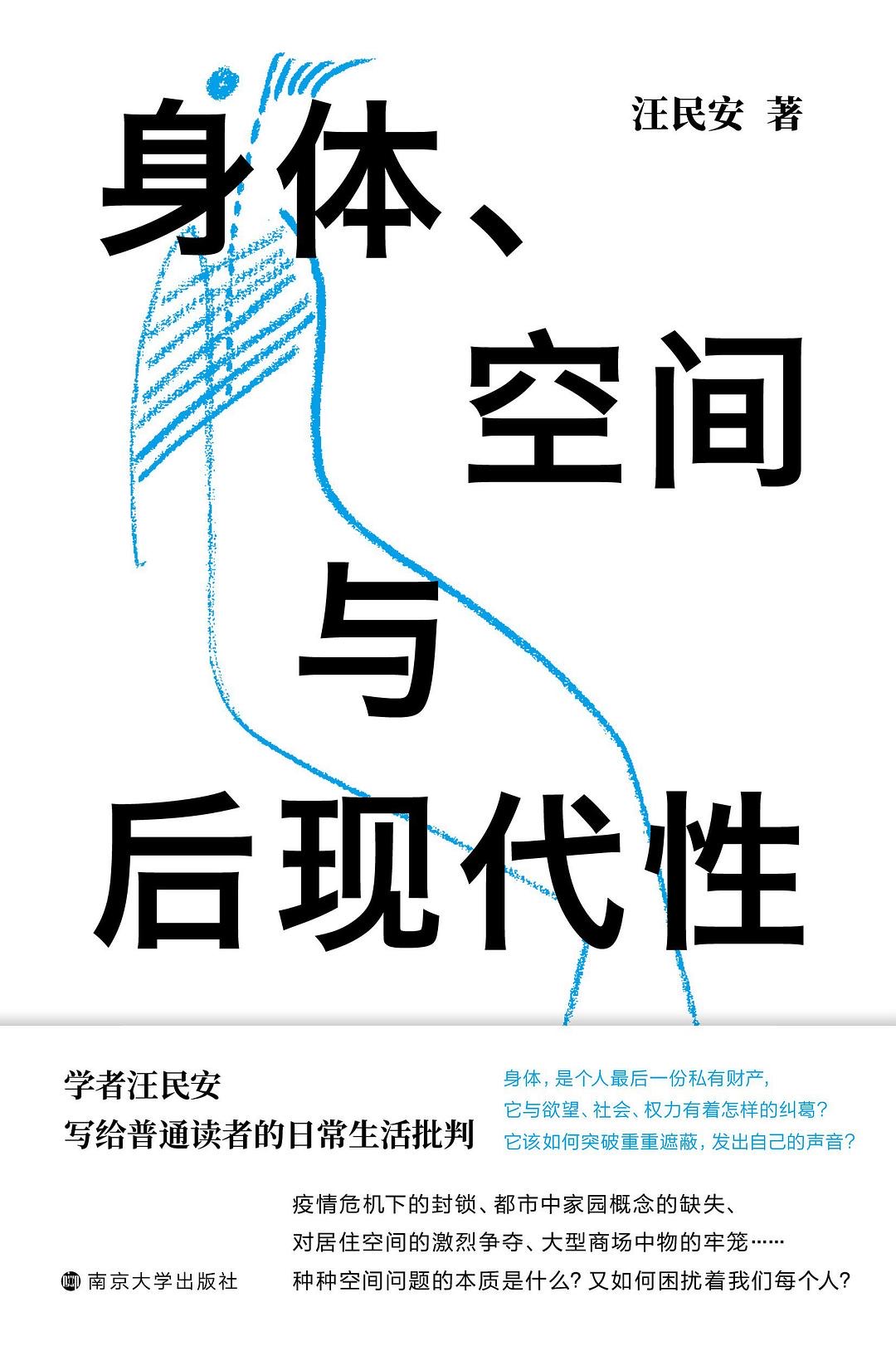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01
结论
严肃的购物转换成了符号的购物,交换脱离了它的基础,家乐福的原则就是将劳动剔除在商业行为之外,剔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这个空间要排除劳动的阴影,要抹掉商品身上劳动的痕迹。商品被包裹起来,它展现的是形式的一面,它首先是作为包装好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作为审美对象和娱乐对象而存在的,商品的内在价值、它的核心、它的基础、它的生产实践和劳动含量隐而不现,在此,商品好像从来没有被汗水浇灌。这不是含辛茹苦的商品,而是唾手可得的轻浮商品。商品在实用性外,展示了娱乐性。剔除了劳动性,也就剔除了美学的崇高法则。我们看到,在家乐福里,一切都滑向了游戏,滑向了表层,滑向了肤浅的戏剧。购物不再是家庭的盛大仪式,不再是精心谋划的壮举,不再是反复的算计、权衡、长久犹豫之后的痛苦抉择。购物不是在浓重的悲剧中完成,而是以喜剧的形式在谈笑间、在喧哗里上演。
在这样一个购物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现在同时上演着三幕戏。首先是马路戏。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地摊、菜场、游民的三轮车、昏暗街头的小吃店,甚至引导潮流的时装街。这是朗朗白昼下的小型交易。购买是在喧哗中进行的,不过是在讨价还价、算计、争吵、充满阴谋和骗局的喧哗中进行的。对交易中的双方而言,物是完全实用的,物的劳动价格并没有被刻意掩饰,相反,它被过度扭曲:在销售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尖锐的说教声中直冲云霄;在购买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咕哝的低语中一落千丈。交易的双方都不掩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都显而易见。在此,所有的布景、所有的格调、所有的隐秘劝诱和欲望道具都被抛弃了,如果说有谋略的话,那也是赤裸裸的欺骗谋略。这样一种马路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的、随机的、低成本的,它有时是蛮横的,并可能伴有轻微的暴力。它既不守信用,也不遵守法律。它只对有关利润的阴谋负责。这也是最古老的交易形式,开阔和无限延伸的马路是它的不朽图腾。

与此截然相对的是马路旁的阔绰、气派和堂皇的现代商场。这是美学的、幽雅的、理性的和文明的购物戏剧。这是崇高的美学、刻意的幽雅、小心翼翼的理性和道貌岸然的文明。在此,物多少有些神秘,有些深度,它们意味深长。结果,这些物的繁杂的人工因素强化了它们的劳动价值。物,总是自我增值。购买不再是一种纯粹而直接的交易行为,它是暧昧的探索、严肃的仪式和慎重的选择。这里既不欢笑,也不忧愁;既不争执,也不喧哗;既不狂喜,也不悲鸣。法律和契约对公开的欺骗大睁着双眼。总之,这里没有阴谋得逞的戏剧,只有理性反复推敲的暧昧艺术。
第三种交易形式在家乐福里表现出来,这是平易的、娱乐的、游戏式的、忘我的交易行为,甚至连交易的出售一方都是隐匿的。交易性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或者说,这是反交易的交易,反计算经济学的交易,反劳动的交易。物变成了没有深度的道具,交易变成有关物的游戏,超市成为新型的游乐园,这是当代社会的购物乌托邦。这样一个神话,在狭窄的出口处,在冷漠的收款机器旁边,在收银小姐礼貌而悦耳的招呼声中,刹那就崩溃了。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第十一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