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养天年、老有所养、老有所归,都是儒家社会老年生活的理想景象,老来孤寡、老来贫困距离主流话语很遥远,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提起。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四种孤单:中国孤宿人群口述实录》一书中,湖北和河南福利院的几十位孤寡老人作以口述的方式讲述各自生活,“打捞出老人生命长河中最重要的记忆骸骨”。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并不是年轻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才会落得老无所依,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离比想象中更近这个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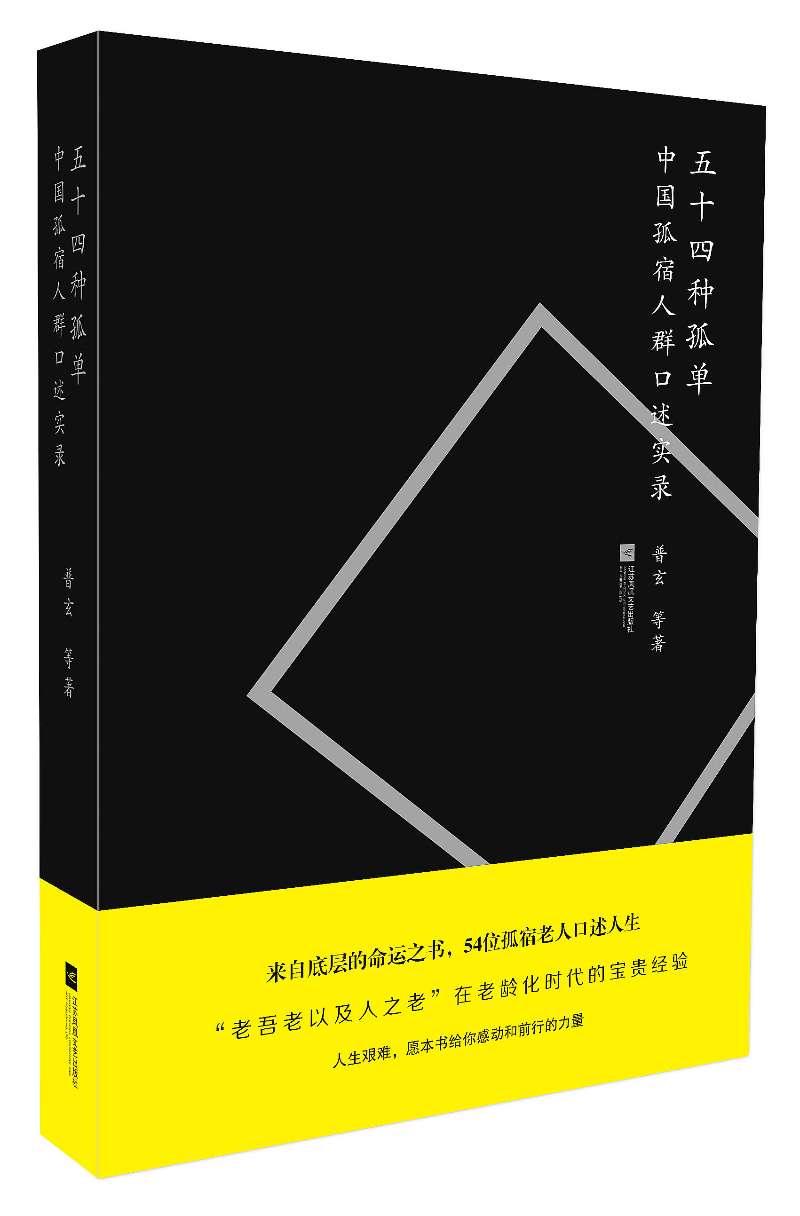
《五十四种孤单》的采访项目由“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项目组”实践,组内成员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每个地区选取3-5个乡村福利院,采取短期访谈和长期跟踪结合的方式,先后采访了七百余位居住在福利院的孤寡老人,最后筛选出五十四篇口述实录。
通过老人们的人生故事,这个项目打开了“福利院”这个被视作家庭伦理范围之外、日常生活禁区的机构;也打开了孤寡老人这个在他人眼里可能是封闭的、奇异的,但并非全然是悲惨单调的世界。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福利院的老人是一群无儿无女、没有储蓄的可怜老人,他们日常活动范围有限、与亲友断了联系、虽然生活温饱但是无聊,性格难免古怪刻薄。采访者也曾被旁人介绍道,“这些老人异常寡情刻薄”。老人院里也确实常常能观察到,“他们争吵时常常咒骂对方,会为菜碗里的一块肉的大小而大打出手”。
起初,这些采访者将孤寡老人采访项目定位成,“写这个最弱势群体最悲惨的命运和最凄凉的人生状态”。但在调查中他们改变了想法,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老人年轻时也曾经血气方刚地活着,热情地恋爱,努力地工作——“他们并不是跟我们无关的人群”。
书中按照导致孤寡的核心事件分期,第一时期的孤寡老人是“代表着新中国初创期,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的小人物”,他们中有上过朝鲜战争的老战士、国有大型油田参与施工的民兵班长、大型铁路铺设钢筋的技术人员、乡村拖拉机手、乡村唱戏和练武的人员,他们因为各种政治或者个人因素导致孤寡;第二时期的老人当年是70年代的养猪能手、大队干部、工程队炮手、乡村财经人员和乡村裁缝,因为各种“偶然”陨石的坠落突然变成了孤家寡人;第三时期的老人当日是改革开放时期在由集体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夹缝中苟活的小人物,比如合同工和临时工,在从乡土向城市的奋斗中,有人牺牲了婚姻,有人影响了终身。
这些老人讲述自己故事时流露出的复杂的“人性”,也提醒着我们每个人与这种孤寡命运的暗淡联系。比如说,老人们因为住进了福利院无牵无挂,所以比普通人更渴望与人接触,用千奇百怪的方法削减孤独:有人养猫养狗,半夜跟猫狗说话;有的几个老兄弟挤在一起,每天像孩子一样,形影不离;有个替别人养了几十年孩子被老婆扫地出门的老人,经常和那个凶狠的前妻联系。他认为,比恶妇更凶狠的,是无形的孤独。

即使在老人院里,他们也“残存”着顽强的生命意志,据采访者熊湘鄂记录,有次与瘫痪在轮椅上的老人聊天结束后,看到他使劲地转动轮椅的钢圈,“抬起一直低垂着的花白脑壳,咧着垂悬着一条常常涎液的大嘴,指着门外不远处的台阶自豪地告诉我,今天已经滚到走廊边上,兴许明年我就可以滚到那里了”。
在五十四篇口述里,孤寡老人不再是面糊模糊的孤寡受害群体,而是曾经将自己的体能、精力和智慧贡献给时代和国家的人,但因为种种原因,老的时候,却没有家,没有孩子,也没有钱。但他们并未一味悲戚,还保留着生命力和与人交流的念想。所以采访组长普玄认为,比起孤寡的现状,更可悲的应是甚至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些人曾经活过。“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才导致我们好多人忽略孤寡的存在。”而人人都会老,谁也难免保证老时会不会如同他们一样。就像《五十四种孤单》前言所说:
“也许你说,你现在事业有成,有夫有妻,有儿有女,孤寡的生活与你无关。那我们告诉你,我们访问的老人们,他们中有很多早先也是有儿有女,有夫有妻。也许你说,我现在位居官场,是科长,处长,是经理、总经理,或者更高,那么多围着我转,我怎么会孤寡?那么我们告诉你,我们接触的这些老人,他们中有人过去也在台上开会,对着很多人讲话,他们也是领导干部,也曾叱咤风云。也许你说,你现在腰缠万贯,你有别墅和豪车,你有很多的资产,你的钱能买来一切。那么我们告诉你,我们在福利院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有钱人,跟现在的暴发户相比,那个时代更让人羡慕嫉妒。你还可能很帅气漂亮,还可能能力超群,还可能祖上有福荫,但这都不能保证你儿女成群和老有所伴,这才是人生。”
书摘
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口述人简介:李廷山,1929年出生,湖北省建始县茅田乡封竹坦村人,抗美援朝老兵,2005年入住茅田乡福利院。
一、我还记得打仗,还有那些战友
我现在在福利院过得很好,吃的穿的睡的,不用操心,有人服侍得舒舒服服。比在外面孤身一人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刚才龚主任还带人来给我测血压,他们每个月都要为我检查身体。我是打过仗的人,大家都尊重我。这个福利院里56个院民,他们都尊重我。有什么事都来问我的意见。我有时候也给他们讲讲战场上的事。可惜我耳朵不太灵便,他们说什么,有时候我听不清。
我的部队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不想回部队去看看?如果是你,你也想。问题是我不知道部队在哪里。我问了很多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告诉我部队还在不在。我不怪他们,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没有骗我。他们没有打过仗,谁关心我的部队在哪里。
我还记得他们。
李朝松这个人我记得清楚。他就是李家湾的人,我们封竹大队隔壁的。那年我们一起去当兵的,可惜他死了,他后来当了班长,我当了机枪兵。我没死,他死了,他要不得。从朝鲜回来后,我复员回到茅田,我还去了李家湾,找到李朝松的老家。我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了他父亲,去山上给他父亲砍回了能烧一个冬天的柴。还给挑了一满缸水。我说,我也是你儿子。后来我每年都去一次李朝松家,每回去都帮他父亲砍柴挑水。我这个人没别的长处,力气有一把,舍得花。
我们的排长我也记得蛮清楚,他是恩施七里坪的人,名字叫向七宝。他们家是大户人家,据说爷爷在晚清施州府里做过官,父亲也在国民党恩施县政府里当过文书。向七宝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不像我们,衣无领裤无裆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我们都叫他“向吃饱”(恩施方言里,“吃”与“七”同音)。记得我们离开恩施的时候,向排长的老婆去送他,提一大包衣服。向排长说,都拿回去,在部队要穿军装,不准穿家里的衣服,都拿回去。那女人就哭,坐在板凳上抹眼泪。排长就吼女人,我又不是去死,要嚎回屋里去嚎。女人就真的站起来走了,看都不看排长一眼。女人一走,排长也掉眼泪,害得我们几个也跟着掉眼泪。我和李朝松对排长讲,你女人那么好,要你女人给我们也说个女人,就比着你的女人找。向排长说,等你们有命活着回来再讲。
最终有命活着回来的,就我一个人。李朝松死了,向七宝也死了。我们一个排,差不多有三十来号人,在一次突围中死得差不多了。
打仗,当然害怕,哪能不害怕?我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比你还年轻呢,没见过大世面。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有的受伤了,缺手缺腿了,害怕得不得了,上战场的时候,腿发抖,拼命忍都忍不住。但是不管怎么害怕,还是要打仗,指挥员说冲,我们就要冲,硬着头皮冲,管不了那么多了。后来,也就不怕了。天天有人死,有人伤。看得多了,也就不害怕了,麻木了。
我是机枪兵,我的枪一响,突突突,别人的枪声就被盖了,听不见了。我肯定打死过敌人嘛,机枪兵能不打死人的吗?排里挑选机枪兵的时候,就是看中了我个子大,有把子力气,扛一挺机枪很轻松。
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战场上打死了多少敌人,肯定是打死过一些的。有一次我拿机枪扫过去,就看见一排人倒下去了。连长和指导员说起码打死了十几个。我想肯定没有那么多,人家又不傻,怎么可能站着不动让我打,说不定是躲起来了。我想四五个总是有的。那次连里给我报了二等功,但是后来发的证书是三等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二、我差点就结婚了
我这辈子没结过婚。我不能害人家,是吧,我连男人都算不上,怎么能娶老婆呢,是吧,做人怎么能害人呢。
以前我还是行的,去朝鲜之前,看见人家姑娘家,我心动。十几二十岁嘛,还是想姑娘。想姑娘的时候肯定是有感觉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在朝鲜的时候,总感觉不行,想姑娘也提不起劲。我就想,可能是打仗,紧张了,怕了。可是后来不打仗了,回来了,还是不行。我就感觉到这辈子肯定是不行了。
但是这个事我不敢声张啊。这个,丢人啊。
去医院看过,悄悄去的。我对家里人讲说,去乡里找政府落实复退军人的政策问题,其实是去了乡医院。医生也没办法,就讲说要多吃肉,多吃好的补身体。那些年,我们家连填肚子的包谷红苕都不够,哪有好东西来补身体。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家家户户都这样。那天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在供销社的铺子里买了一斤红糖,拿回家藏起来,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泡糖水喝。不敢告诉家里人啊,怕他们埋怨我,说我浪费钱。
其实,我差点就结婚了。复员回家第二年,就是1954年吧,那年我25岁,我们家给我说了一门亲事。那边人家姓刘,姑娘家长相周正,高高大大的。媒人带我去看过一次,他们家就住在我们山脚下的木桥河,离得有七八里地,两家人过去就认识,也是算知根知底的。后来我父亲借故去木桥河背煤,去刘家看过一次。人家好吃好喝地招待我父亲,完全是当实在亲戚招待的,饭是刘家姑娘下厨做的。我父亲高兴,回来对周围邻居都讲刘家好,讲刘家姑娘好,能干,知书达理,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茶饭,一手好活路(活路,即耕田种地的技能)。父亲还讲,他儿子是要参加工作的,是要参加国家建设的,这样的姑娘配得上做他家的儿媳妇。搞得周围人家都知道我说了刘家的姑娘。父母定了日子,让刘家来看地方,实际就是认门。我们家穷,但父亲还是找亲戚借了钱,扯了八尺蓝布八尺花布,打发给刘家姑娘。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我肯定很恼火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肯定是想结婚啊,想有个女人,想有娃儿。个年代,我们都得听父母大人的,自己也做不了主。父母大人说要你娶谁就娶谁,父母大人说要你嫁谁就嫁谁。我们家家教很严,连嘴都不敢顶,哪敢反对他们安排好的亲事?我们家托媒人去刘家定下日子,说好那年冬月初八我们办喜事。刘家开始请木匠打箱子柜子,准备嫁妆。我们家也打床,粉刷房子。
眼见着就要到冬月初八了,大约是十月中旬吧,我和女的去乡政府扯结婚证。走到半路上,我给她讲,我说我不能和你结婚。女的说,你玩弄妇女,我要去政府告你。我对女的讲,你不要冤枉我,是我没得福气娶你,我那方面不行,做不了你的男人。那个女的还要傻里傻气的问我,哪方面不行?我没办法给她解释啊,我只能说,我不是个男人,我不能害你。女人还是不信,她说你是个骗子,你让我摸摸,摸了我才相信。你说我哪能让人家摸啊,哪有现在你们年轻人开放,我是民国十八年出生的(公历1929年),解放后到五十年代,我也才三十岁不到,还是很怕。那个年代,有讲究的,老辈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我总共才见那女的两三回,手都没碰过,哪能让她摸我?传出去,说她摸过我,那她也嫁不出去了。
那女的就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哭,哭醒了就站起来,走了,看也没看我一眼。那天下了蛮大的雪,听说女的在路上,在下木桥河的坡上,摔了一跤,一只手摔骨折了。
三、我要好好为他们活着
我不是男人的事,很快就都传开了,四邻八舍都知道了。起先我很怕丑,觉得太丢人,抬不起头来。后来日子一长,也无所谓了,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我懒得管这些。从此,再没有媒人给我说亲事,我父母讲再也不管我的事,说我死了他们也不管。早知道现在这样还不如死在部队。我说这不能怪我,我不做害人的事。我说我那么多战友都死了,我没死在朝鲜,我知足。
我不是讲现在我住在福利院里,有国家养活我,有人服侍着,我就假装说知足。不是的,我是真的知足,我活到现在八十多快九十了,够本儿了。你看李朝松,我们1950年一起从茅田去业州,从业州又去恩施,1951年又去朝鲜,我们都在一堆儿,他却在朝鲜死了。我打死了那么多敌人没死,他一个敌人都没打死就死了,他还是班长,还是当了小官的,是不是划不来?那天他中了流弹,胸部清清楚楚一个枪眼,血一直流啊流,包都包不住,我赶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对我比划了一个手势,对我摆了一下手,卫生员还没到他面前,他就死了。我当时不明白他做那手势的意思,后来我猜想,他应该是要我别学他,要活下去。
我当时只看到,李朝松的血流到地上,地上的雪都红了一大片。
上访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他们说我是上访,说我不讲道理。可我不这么看,我不是上访,我就是问清楚情况,我不吵不闹,不犯横,不干扰公务,这能叫上访?他们硬要说我是上访,我也没办法,你是记者你明白的,上访又不犯法,又不丑,是不是?
复员回乡以后,我就一直在等消息。那时候听说有政策,在部队有立功的,回来安排工作。我不是有个三等功么。1952年我们从朝鲜回来,又到沈阳当了一年兵,1953年复员了。我到县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他们说让我等消息。我就老老实实等,等了两年没消息,我就去找县人武部,他们说归民政部门管,我找了县民政局,又找了恩施地区民政局。打听到从朝鲜回来的,有些已经工作了,但大部分都没安排,他们让我继续等。我说我是立了功的,我在战场上立了三等功。县人武部的领导说,三等功不算,要二等功才安排,而且二等功都不用复员,在部队就提干了。
我想,既然还有蛮多人都没安排,也不差我一个,我也不能搞特殊化,那就继续等。这一等又是好几年,乡里县里的民政干部、乡政府县政府领导,个个都认识我了。因为我经常去找他们问情况,有的人看见我,点个头打个招呼,有的人看见我就绕路假装没看见,想必他们是觉得我经常找他们,烦我了。我不吵不闹,说话细声细气的,生怕得罪人,他们烦我什么呢?后来我无论去哪个单位问情况,我主动给领导们泡茶,给他们擦桌子拖地。但这也没用,后来他们就不准我进办公室,说要反映问题去信访办,信访办就设在县政府的门卫室,只能去那里,其余哪里都不能去。
我讲我只是打听情况,又没搞坏事,为什么反映问题还要规定个地方?我就要找县长找书记,找他们给个说法。我是为国家作了贡献的,我是准备牺牲的,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要饭的,为什么不准我找领导。有一天我去政府里面,找县长,秘书不准我进办公室,我就大声喊,我要见王县长,我要见王县长,他们就叫来了警察,把我关了两个月,快过年了才放我出来。在看守所的时候,一个警察问我,为什么要去县里闹事。我给他讲,我就是想有个工作,活得体面一点。我的战友们死了,我没死,我活得太窝囊,那就对不起死去的人。我说我要好好活着,为自己活着,也为他们活着。
那是1969年的事了。那次以后,我认命了,我再也没去找过任何人,我就在家搞农业,在生产队当了几年保管员,不识字,看不懂账目,后来保管员也不当了,就搞农业。
我不上访了,反而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我一个侄子在县里工作,他帮我去人武部查了档案,说我档案里有污点,记录我这个人不能重用,因为我在部队违抗上级命令。
说我违抗命令,我肯定不服。指挥员说冲我就冲,再怎么怕死我都冲,怎么会违抗命令?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啊。这个事,几十年来在我心里都是个疙瘩,解不开。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有一次我手膀子受伤了,去找卫生员,卫生员的帐篷里还关着一个俘虏,是我们连抓到的。一个南朝鲜小伙子,看起来年纪还没我大,白白净净的,瘫在地上,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想他肯定是饿了,我就把身上的两个煮鸡蛋给了他。那一下,他眼睛都亮了。没想到这个事刚好被连长看到,连长是山东人,霸道得很,他骂我。说你个小王八蛋,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你还把鸡蛋给敌人?我说他不是敌人,他是俘虏,我们要优待俘虏。连长说,你把鸡蛋拿回来。我说不拿,他都饿成那样了,他也是个人。连长说,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说你儿子比他小不了几岁吧?你儿子要饿死了我也会给他吃的。连长骂我说,滚。
想来想去,违抗命令只有这件事。我也不想去追究了,连长还活没活着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能活下来,就蛮幸运了。唉,其实就是现在找着部队了,我也去不了了,走不动了,老了。其实部队不是每个当官的都霸道,也有蛮多温和的,向七宝向排长就蛮好。那天他还对我讲,说他老婆有个表亲,长得好标致,屁股大,一看就能生一窝娃儿,说比他老婆还好。他说如果我们活着回去,他就做媒说给我。那天我们裹着棉袄躺在战壕里,裹了一个烟卷,他抽一口,我抽一口。我说那我们以后就是亲戚了。
一颗炮弹飞过来,在我们不远处炸了。石块土块木头块块到处飞,我连皮都没破一块。我说,排长,好险啊,你有没有事?向七宝不说话,我说向七宝你是不是死了?他还是不说话,就睡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真的死了。我就那么看着他,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就那么看着他,现在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觉得我看见了他。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