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顾前的故事。
春节前,顾前在南京艺术学院门口,被一辆疾驰的电瓶车撞断了腿,骑车的人赔了他三千块钱。而他只得打上白色石膏,待在迈皋桥的家中,哪儿也去不了。在南京的雪还没化尽,小区里的积雪多得快要把门洞堵住的一天,朋友们来家里探望顾前。他们拎着几罐啤酒,顺便凑了两桌牌局:一桌在餐桌上,另一桌在客厅的茶几上,人们一边打牌,一边抽烟。

这是我到迈皋桥顾前家采访时遇到的情形。顾前说,这样的相聚是很经常的,一个礼拜里总有那么一两次。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他们这群人从中午开始打牌,打到晚上吃饭,吃完饭再继续打。因为经常混在一起,顾前、曹寇,还有另一个朋友(在西祠胡同上写作的小红),以地名自封为 “迈皋桥三杰”。
在顾前家,我见到了“迈皋桥三杰”其中的两位,一位当然是顾前,另一位是曹寇。这二位,年龄相差十几岁,因为生活状态一度很相似——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时间自由,混混酒局、还写写东西,所以走得挺近,有时候还一起相约着去周边的小县城旅游。
顾前的书房不大,放置着古董模样、年代不明的梳妆镜和琴台,这都是他的收藏之物。当然,还有一个书柜,里面的书很杂,既有《1Q84》,也有《张爱玲文集》,还有许多类型小说。我带去了他早年的两本小说,其中一本是出版于二十年前的小说集,封面是红褐色的《萎靡不振》;另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嗨,好久不见》。顾前对前者的反应是,“这本书不值一提,里面许多句子都不通。”说话的时候,他腿上石膏套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脚上的白色塑料袋是做什么用的?”“白天到处走来走去,会蹭到地上,晚上还要睡觉上床的,怕脏了。”“你没有更合脚的鞋套吗?” “哪有鞋套?像我这样生活在底层的人。” 顾前的态度十分爽朗,好像在讲别人的窘境,且这样的窘境由衷地可以被原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一家台湾公司离职之后,顾前就一直保持自由无业的状态,如今已有二十余年。最初,他独自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房间遍布灰尘,沙发上有一个大洞,屁股刚好可以“卡在里面”,他就一直坐在坑里,也从没想过去补上这个洞。
对待写小说,顾前也像对待沙发上的这个洞一样——虽说这么多年来他闲在家写小说,却也从没有下过什么想要出人头地的狠劲儿,“有吃有喝,我才不写小说。”顾前说,潜台词是,这么多年若是有其他“发财”的方法,他也不见得会走到写小说这条路上。在名为顾前的豆瓣小组里,说明只有一行字——“希望顾前多写一点”。
“顾老师穷是穷的,但不是毫无根基的、农民工似的穷,而是没有负担、自由自在的穷。”曹寇认为,“他跟我们屌丝出身的人完全不同,他也不是想用写小说得到什么,他追求的是好玩、有趣的小说,跟收集古董、喜欢下棋、打牌一样,是一种好玩。”
至于具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玩或有趣的,顾前觉得这问题没法回答,“好玩没有标准,无聊也是没有标准的,有人觉得一些经典作品好,但我简直看不下去。”他现在一年中有几天担任南京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入学面试考官,很多学生提到他们非常喜欢东野圭吾,他也不觉得有趣。虽然他原来也是彻夜不睡地读金庸读福尔摩斯,“只能说,好玩的标准不同”。

顾前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
就在2017年,他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一部叫做《嗨,好久不见》,另一部是《去别处》。隔了漫长的20年。很长时间不出书,顾前什么解释也没有,感觉出新书只是跟读者打了个“招呼”。
萎靡不振
依旧是什么解释也没有。顾前说,已经不记得自己第一篇小说具体写的是什么内容了,只说,第一篇好像叫做《大丈夫》,发表在《青年作家》上,但这篇对于以后的写作说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定调作用,“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么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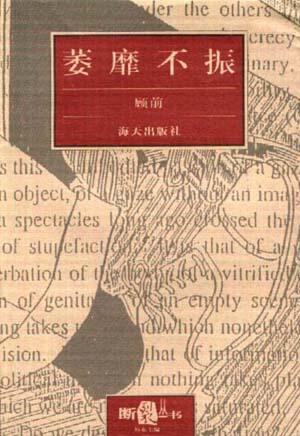
顾前著
海天出版社1999年
跟顾前本人的状况可以类比的是,他早年出版过的一本小说集《萎靡不振》,里面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怎么也推销不出去广告的广告业务员,有的是在工厂旷工胡混电路图都不会看的电工,还有很多渴望着亲密关系,却屡次失败的离婚男性。而顾前在描摹这些失意者的内心活动时,反倒充满着释然的黑色幽默感。
比如一个夜里看了球赛,第二天中午才起床的人,对自己的虚度时光,有这么一段心理独白,“我个人的看法是,足球,包括所有的体育活动在内,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瞎胡闹,其意义仅仅在于,把人类多余的精力给消耗掉。试想像泰森那样的人,如果不打拳,他会去干什么呢?”
再比如一个很久没有工作的人遇上了突然发达的熟人,揣度着对方究竟怎样才会在事业上“帮带”自己,“说实话,我对经商一无经验,二无兴趣,但如今我既然已沦落到这步田地,就再也没有挑三拣四的权利了,只要有人给我大把钞票,即使让我去当个董事长或总裁什么的,我也要硬着头皮干了。”
为什么顾前总要写未遂的志愿以及失意的人生? 一些评论者喜欢将这样的小说风格评价为——对于身边“灰色人群”,日常生活、小人物的命运的情有独钟。而顾前说, “这是因为我接触的基本都是这样的人,马云我也不认识。这只能解释为,不成功的人更吸引我,我只能和不成功的人一起玩,成功的人不会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像我这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挣的钱只够吃饭,工作也都是最普通的,也没有什么管理、当官的工作,只是维持生活而已。”他的一个编辑朋友李黎觉得,这个书名几乎是个“谶语”,顾前写完了之后,就真的萎靡不振了二十年。
在工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前在南京的无线电元件厂里做电工,那时候,电工是很好的工种,全厂一千多人只有几个人才能成为电工。这个活计,一是受人尊重,二是特别“好混”。集体工厂大锅饭好吃,做多做少一个样,做电工就更是如此,顾前回忆中的电工形象就是,“整天扎个皮带,背着一包工具,东晃西晃哪好玩往哪去”。他自己更是如此,从来不研究业务,总是躲在某个地方打牌、睡觉——他的小说里还出现过身为电工的“我”往柴油桶里撒尿引起生产事故的桥段。
混了几年,顾前连电路图都不会看,换机床上的保险丝,他会忘记把保险丝上的瓷帽子戴上,用手抓着保险丝直接往上拧,有两次极为惊险地、被380V的电压电得直接跳起来。说这话的时候,曹寇刚好进到书房里,“他是这么换电灯泡的”,曹寇一边假装拧电灯泡一边转了一个整圈,如此嘲笑道,看起来对顾前的电工生涯十分了解。
为了玩,顾前经常向工厂里“请病假”。有时候“病假”时间太长了,请病假就变成了“泡病假”。他把朋友的肝炎血液报告伪造成自己的,从单位批下来了几个月的假期,这几个月里,他跟着养蜂人去山里养蜜蜂了。
他养蜜蜂不是为了挣钱——事实上一分钱不挣,只是觉得在深山老林里很好,“我当时想,山里多好玩啊,多安静,养蜜蜂多有趣啊。听说我要去,养蜂人挺高兴的,白干活不拿钱嘛。”顾前在山里跟养蜂人住在一起。白天要给养蜂人烧饭,没别的饭菜,只有黄豆加酱油,实在想吃蔬菜了,就用蜂蜜跟农家人以物易物换点儿;晚上睡在帐篷里,这帐篷是用一根竹竿搭在两棵树上,上面再搭一块帆布构成的。睡在这样的帐篷里,头可以摆在外面,还可以看看星星。养蜜蜂久了,他经常被蜜蜂蜇伤,蜂毒又引起各种风疹过敏,最厉害的时候,头和身子都肿了起来。
但对怎么采蜂蜜,他讲得就比做电工活细致多了。“蜜蜂把蜜采回来就放在那个蜂房里,蜜在里面怎么把它取出来呢?你要把蜂框拿出来。有一个摇蜜桶,你把蜂框卡在里面、卡满。外面有一个把手,一摇里面就在转,利用离心力就可以把蜂巢里面的蜜甩出来了。等摇蜜桶里面的蜜多了,再把蜜倒到塑料桶里。”
追着花期的时候最忙。养蜂人听说滁州槐花开了,又没有雨,就要搬家了,他负责去找人拼车,顾前就在家里钉蜂箱。“蜂是一筐一筐的,卡车上、火车上一碰撞蜜蜂会撞死的,所以我要拿小木头塞子钉在每个蜂筐之间。那么多蜂箱,要慢慢钉。”养蜂人找了另外一个养蜂的老头拼了一辆卡车,老头和养蜂人坐在车前头,顾前跟老头的两个女儿就待在车后头,为了不被车甩出去,他们三个一起被高高地绑在蜂箱上面。
后来,集体工厂愈发不景气,混日子也逐渐到头了——工厂在偏远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分厂,要分配一部分工人去农村上班,顾前因为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当然也在发配的行伍之中。他实在受不了这么偏远的环境,索性辞了职。
多年后,当顾前再见到那些工友时,他们都已经被遣散了,有的在自行车棚里看自行车,有的在卖报纸。昔日工友现在在卖报纸的场景,可能给了他不小的冲击,在小说《炎热的岛屿》里,“我”的“好友”许亮也是卖上了报纸。
去别处
我问顾前90年代去海南的情形,是不是和《我爱我家》里贾志新去海南一般,他说,“我比他还要早几年。”事实上,他跟贾志新去海南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听某个朋友说在海南可以发财,也不管消息是不是真实,就匆忙去投奔了——顾前的朋友是分配到海南当公务员的南大毕业生。
《炎热的岛屿》就是写这里的生活的。故事的开头说,“我不知道许亮为什么滞留在这个炎热的岛屿上,这里就像桑拿浴室中那块烧红的石头,无边的海浪哗哗地泼上去,蒸腾出永无休止的热气。”
到了海口,顾前才发现海口的混乱超乎他的想象,行车道是不分正反的,找工作也不容易。本来,他首选的工作是文员秘书类的文职,因为这样的工作“体面,不卖力气”,至少比当搬运工省力气。“我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写作才能,写字谁都会写,我会写字。”顾前说。
他每日在海口公园的张贴栏里搜寻,当时的张贴栏里贴着许多招聘广告,找工的人之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规矩——看到中意的岗位就撕掉或者用笔划掉,免得别人过来抢。然而一天天过去,他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将之归结为性别的原因,“我看人家写的都是要相貌端正、多少多少岁数的姑娘,哪里是招秘书,就跟招情人差不多。”
穷途末路下,顾前只能放弃最初的打算,干起了别的活,他接手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舞厅打灯光,需要让灯光跟着歌手走来走去”,接着他又做起了音像市场管理员,还是跟舞厅相关的,只不过从“跟班”升级成了“管理者”,工作内容就是去各个歌舞厅检查有没有黄色录像。音像市场管理员听起来像公务员,但其实不是,也就是在混乱市场里生长出来的一种临时工。顾前对于自身上门检查黄色录像的资格,并不确信,“这当然不是扫黄打非,我们自己都是盲流,还打什么?我这样的人都能当,可见乱到什么程度。”
他还为一份杂志拉过广告。比起音像市场管理员,这个工作更加不正式,不仅没有底薪,连正式的合同都没有。如果“幸运”地拉到了广告,便能有25%的提成,可问题是无资源、无人脉,怎么能拉到广告?开始的时候,他要拜访客户全靠步行,连二手自行车都买不起,他至今仍然记得“海口的大热天”。还没有工作证,只带着一摞杂志的宣传资料,推销的言语往往陷入空口白话之中,“我们这杂志是做什么什么的,你们要不要来做广告?”对方见到这样的“无名之辈”,有的直接将资料甩在地上转身就走。
如此往复碰壁,收入当然也是很少的。“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很长一段只挣了250块钱。”后来,顾前跟“前辈”探讨,倒也摸索出来了一套经验,知道上门拜访之前,应该打电话自我介绍,“至少问清总经理姓什么,要找哪个总,再约时间见面,这样显得更有身份,成功率也更高。”
不管怎么说,这段拉广告的经历算是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的小说里有时会出现一个拉广告时期的“朋友”,而“我”反倒向“朋友”传授起了广告功夫,“首先你要充满自信,你要想到那些所谓的厂长经理们不过是大草包,他们的威风都是靠高档办公室、女秘书、真皮沙发撑起来的;其次你要注意观察,比如你发现一个总经理是个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家伙,你就说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魄力的改革者,第三你要有软磨硬泡的功夫,只要对方没把门彻底关死,你就一次次地找,一遍遍地盯,把他缠得没了办法,可能也会成功……”
除了检查黄色录像,给杂志拉广告,顾前还在灯光夜市里的地摊上卖过来历不明的二手衣裳,从材质、价格、款式综合看来,他推断可能是“从外国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最得心应手的工作还是做编辑,他曾在在别人的委托下给一份财经杂志做编外的编辑,工作的过程相当轻松。他说,即使专业的内容,他看几遍稿子也就弄明白了。“还有什么比编辑的工作更容易吗?太容易了。”顾前自问自答道。
但更多时候,他在海南是没有工作的,他倒也不觉得心慌,因为那时没事做的人多得是。他们都是听说了海南发财机会多,前来撞大运却毫无收获的人,有时也在一起交流经验,有的人混不下去就回去了。他也是这样,最后还是回到了南京。
小说可是要费点事的,写多了写不动
顾前回到南京后,还做过几份工作。他给老板当“秘书”,这个“秘书”是专门给老板送碟片的秘书,老板特别喜欢看录像带,他就负责上午跑到录像点去选录像带,再把老板头天看剩下的,拿了还给录像店,唯一要记住的就是老板喜欢文艺片,获过奥斯卡那种,不要枪战片。一通儿跑完了,他回来就到公司喝茶、抽着烟“东晃西晃”。
最传奇的一段工作经历是,顾前还在传销公司里编过内刊(在传销尚且不算违法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正是传销公司发展壮大的时期,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传销商,还有许多人是退休后来传销公司兼职,顾前编的内刊要在内部流通,鼓励人心。他认为这个做编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既省心钱也多,内刊编的还很漂亮,要不是后来换了个老板,为件小事把他批评的不高兴,他也不会就这么回家了。

从传销公司辞职以后,他再也没有工作过。他自己也不清楚,回家待着的结果究竟是自己选的,还是别人逼迫的。“我一辈子干的都是简单的活儿。”顾前回顾半生,这样说。
即使是在家待着,他也没有憋着大劲儿写小说,小说产出得很少很少。在小说《困境》里有这么一段话,写出了他在家写作的焦虑,“刚辞职那会儿,我以为我会文思泉涌,起初也确有那么一股子泉涌的味道……接下来就渐渐地不行了。我仿佛患上了严重的便秘,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而绞尽脑汁……但我依旧在电脑前苦熬”。
没了工作以后,写作成了他收入的唯一来源,“九十年代,一篇小说稿费几十块钱,也能请人上饭店吃顿饭。”可是,顾前说,小说不能老写,写多了,也是写不动的。“相比扛大包,写作是不费力的,但相比打牌,写作就费力气了。费力跟不费力是相对而言的。我有吃有喝,为什么要写小说呢?”
为了挣钱吃喝,怎么办呢?顾前就给报纸写点千把字的小文章。他有一个名单,上面列着各家报纸编辑的联系方式,有的写好了就可以一起投,那时候各地信息不联网,就算同时发表了,彼此也不知道。纸媒景气的时候,有的报纸稿费给的还挺大方的,有的一篇就给好几百块。“深圳的报纸很大方,有的就不行了,只有一百。”顾前对稿费记得很清楚。
“小文章的好处是,可以什么事都没有坐那儿硬编,花一小时、两小时就能写一篇。小说可不是,小说可是要费点事,你总要构思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不能瞎编胡扯。不像他们(指他的朋友们),我没什么才能。但这个也不能写太多了,写得多,要吐的。”
而曹寇觉得,顾前写得少,这与他的写作方式有关。“因为他的小说更多地来源于经验,包括自身的以及朋友的,他不是学者型的,也不是野心勃勃型的,所以他只能写自己知道的,只能写自己觉得有趣的。但他自己所经历的是有限的,朋友圈所能提供的素材也是有限的。”曹寇说,“韩东的一件事,顾老师就变成小说了,可能主人公名字就叫韩西。”在顾前自己看来,自己的小说里面的事情和人物都是“虚构、或者胡扯出来的”,但其中的心理和情感都是最熟悉的, 就比如《打牌》那篇,“我打了多少年牌嘛。你要叫我写打毛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毫无这方面的经验嘛。“
顾前尤其喜欢讲不知道,不关心,他说不关心的事情说起来简直没完没了,“我不关心时尚,潮流,科技进步。什么男女明星谁跟谁好了,谁生了孩子,什么哪部电影火了,哪个歌星复出了等等,我尤其不关心。”其实不仅如此,他是最近才刚刚用上了微信,回复邮件需要夫人的帮助。
就像苏童在顾前第一本小说集的序中所写,“在他的身上文学的欲望并不比别的欲望更加强烈,因此所有的欲望被一视同仁,哪个也不让它拥有特权。”
现在,顾前和曹寇经常玩到一起。有年冬天夜里,他突然找曹寇去紫金山上看梅花。他们背了几罐啤酒,准备赏花喝酒,没想要喝酒时却感觉冷得要命。曹寇说,“古人这么玩的时候,是有一个仆人挑着有火炉的担子。”顾前说,“那太好了,你下次就挑着担子来吧。”
除了夜里去紫金山上看梅花,他俩还会相约着去周围的小县城转转。他们不开车,搭汽车去,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两个人一般住小旅馆的标间。“常州金坛有家状元户,院子里有乾隆年间的牡丹花,我们专门慕名去看过。”比起名山大川,两个人更喜欢游历各种小地方。
顾老师特别喜欢看别人是怎么过的,曹寇说。“各地人过日子是不一样的,人家是用什么家具,妇女怎么长的,小孩怎么长的,办丧事怎么着,都是不一样的。”曹寇记得,2017年年底他俩在浙江临安,正好去到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办丧事,人家家中大开流水席,两人就站在一边看着,“我感觉顾老师就想坐进去吃一吃,只是人家是办丧事,就算了。”
不巧,这次“车祸”顾前把腿撞了,也扰了他们的出行计划,本来说好过完年两个人再去皖南的小县城转一转,一直转到池州的九华山——如今,这个计划就延后了。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国外作家是谁?
顾前: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喜欢写《傻瓜吉姆佩尔》的辛格,喜欢高尔基,契科夫、卡佛。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国内作家都有谁?
顾前:中国作家多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郁达夫等等。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顾前:我觉得圈子这个应该顺其自然,不是什么必要条件。有的人没有这个圈子,也写得很好,有的人有圈子,写得也可能很差。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顾前:没有什么习惯,就是闲来无事写写。写得多或者少不叫习惯,写得少是因为懒惰。我都是没人约,也没地方玩儿了才会想到写作。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顾前:我其实看的更多的是杂书,各种宗教书,我喜欢看南怀瑾、奥修、克里希那穆提,《读者文摘》我也很喜欢看。还有一些古书,像是《三言两拍》《儒林外史》,反正不光是文学书。还喜欢看围棋棋谱,研究研究人家为什么走这步;我还在网上看围棋实况转播,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的我都看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顾前:我电影和电视都看得特别少,无法回答。就算看电视我都看《青铜兵团》《我从汉朝来》这样的纪录片,不看故事片。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顾前:语言和故事,语言不能晦涩,故事不能太无趣。比方说,如果读到写一只猫,一只狗的故事,我就毫无兴趣。我想看动物,我就直接去看《动物世界》,电视台里的《动物世界》我就没有没看过的,现在几乎都是在重复看。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评判作品好坏的公共标准。这当然不是说文学青年写个文字不通的东西去跟托尔斯泰比,而是说当一个作品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以后,那就看个人喜爱了。我很喜欢辛格,这就是我个人喜欢。那个人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那是他个人喜欢。我们俩可能并不统一,但不能说谁对谁错。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顾前:从来没想过,我考虑读者干什么?我不知道谁写作的时候会想到读者。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顾前:我个人不关注,也不认为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像你刚才说的,既然我们的生活天然就离不开政治,那还要我关心干什么,甩都甩不掉呢,是吧。我不关心政治,毫无兴趣。我关心什么?我关心能安安静静地活到老,无病无灾地活下去。我关心基本生活,对人类命运没啥兴趣。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小说读者是更多还是更少?
顾前:这个问题我丝毫也不关心。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顾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也不重要。
顾前:生于1958年,长于北京军队大院,现居南京迈皋桥附近,牌友、醉汉、作家,以前做过广告推销员、养蜂伙计和工厂电工(不会看电路图),著有《萎靡不振》《嗨,好久不见》《去别处》。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