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没有人可以看尽一座城市的全部,城市的时间与空间都太过庞大,那许许多多看似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终如云烟过眼,或消失无形,或渗入此时城市的肌理之中,如同幽灵。
当曙光划破天际,薄雾之中隐约可见的幻影形同宫殿一般,那是一座已经消失的宫殿。空中飘荡着宫廷长笛独奏曲。曾经,在列宁点燃革命的火焰之前,他还乘坐火车在此地短暂停留。但现在,这条铁路已无人记得,铁轨两旁杂草丛生。蒂尔加藤公园中森林繁茂,却难以遮蔽胜利的光芒。萨克豪森集中营焚尸炉内的骨灰,尘卷般地飘浮在大屠杀纪念馆的上空。在那一堵长墙的旧址处,如今是一座公园,分为若干区域,狭长而毫无修饰,经常可以听见孩子们的笑声回荡于此。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停车场中,游客们驻足而立,屏气凝神,他们的脚下曾是希特勒的地堡。
这座城市,便是柏林。
新近出版的《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一书,借21位柏林人的故事,为我们绘制了这座城市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仿凡尔赛宫建造“无忧宫”之前的三个世纪直到2011年的一幅幅肖像。柏林,一座变化无常的城市。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般,循环往复于强大兴盛与萧瑟衰败之间。没有一个首都如它这般,遭人憎恨,令人惶恐,同时又让人一往情深。没有哪处地方像它一样,五个世纪以来饱受冲突之苦,深陷混乱之中,从宗教战争到冷战一直都位于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
这是一个支离破碎、孤魂野鬼的城市,一个激励了无数艺术家、见证过不计其数谋杀的大都会,一个思想的实验室,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百年中,最充满光明的设想,最邪恶黑暗的伎俩都来自这里。这里曾是欧洲最狂妄自大的首都,这里曾被盟国的炸弹肆虐,这里曾被分裂为二又合二为一,重生为世界创新城市之一。
作者罗里·麦克林(Rory MacLean)居于柏林,柏林这座城市也住在他心里。麦克林在尾声章节《想象柏林》中写道:
“我们的记忆并非固定不变,也并非需要重新拼凑的无序碎片,更不是图书馆中积满灰尘的书籍。相反,记忆促使我们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对话。我们的整个历史记忆,个人的或集体的,都在想象中得以重建,成为不断延伸发展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得以理解眼前纷繁嘈杂的新生事件。”
从21位柏林人的21个故事中,我们为你节选了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的儿子被征入伍在西线阵亡。珂勒惠支的作品最早由鲁迅引入中国,鲁迅曾说:“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声,挣扎,联合和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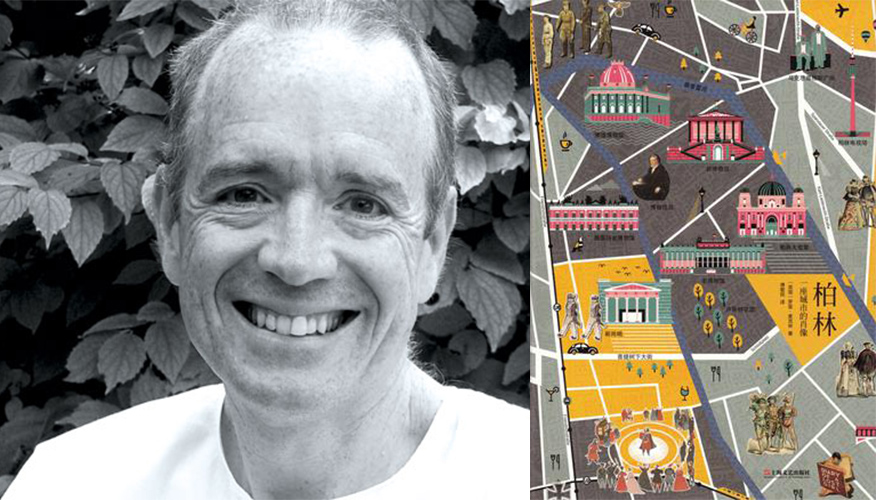
凯绥·珂勒惠支和《母与子》(节选)
1903年,沃尔特广场
转眼凯绥就二十八岁了。她抛弃了独身主义,嫁给了医生卡尔·珂勒惠支。他思想开放,喜欢帮助穷人。他们住在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这个区里住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离柏林富有的市中心不远。这儿的廉租房灰暗阴郁,臭气熏天,光线暗淡。这里的孩子,四分之三没有见过日出,一半的孩子从未听见过鸟叫,三分之一的孩子身高和体重都在正常水平以下。结核病肆虐,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把这里称之为“穷人的营地”。在这个人口拥挤、危机四伏的普伦茨劳贝格地区,当地人开玩笑地说,杀死个人像把玩斧头一样简单。
珂勒惠支家的住所,相比其他邻居,稍微宽大些,有四间干净的房间,有一个可以眺望沃尔特广场的小阳台。沃尔特广场是这个居民区唯一的开阔地。凯绥经常站在阳台上远眺并且问自己:“我能做点什么呢?”毕业后,她生下两个儿子,帮助丈夫经营他的诊所。她在画室里安放一张用橡树做的工作台,增添了铜板和画画用的工具。她的脸,本来是瘦长形的,如今也变得越来越胖,双手也因为经常用苏打水擦洗丈夫的手术室地板而变成了酱紫色。不过,她那双漆黑下垂的双眸依旧像小女孩的眼睛一样明亮,让她丈夫迷恋不已。凯绥知道,丈夫对她十分忠诚。他支持她,鼓励她的工作,从不要求她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帮他做事。做母亲并没有消耗她太多的精力,倒反而促进了她。她觉得自己更有创造力了,因为她可以更精准地把握自己的感受。

她越过一栋栋房子的屋顶向外遥望,南面是光芒四射的教堂和皇宫,西边是浓烟滚滚的工厂,怪兽般的机器轰鸣着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服务。凯绥将素描本和早晨画的画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自己的心房。她每天都会在卡尔的会诊室里给病人登记,然后用她的画笔将他们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因裁布而严重受伤的手指,从高处摔下致残的泥瓦匠,刚从第三次流产中恢复过来的女制革工人,还有因为得了肺结核而喘着粗气、长着罗圈腿的双胞胎。
“那次我遇到一位妇女。她是找我丈夫看病的,碰巧遇到了我。那一刻,无产阶级的命运让我无比震惊,心一下子被揪住了。”她回忆说,“像妓女和失业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我感到悲伤和痛苦,促使我觉得有责任关注工人阶级。”
卡尔的病人成了她绘画的模特,她的两个儿子亦是如此。凯绥极力地去捕捉那些“从灵魂深处才能看到和体会到的东西”。在画室的桌旁,她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卷起袖子,任凭头发垂落眼前,似乎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自我世界。她承认:“我从不会无动于衷地创作。我创作时一直都充满激情,热血沸腾。”
但德皇却不希望艺术家们直抒胸臆,不希望他们打破传统,不希望他们自由自在。相反,他希望将这些艺术家们掌握在手心里。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就在于反映国家的强盛。正如他的祖先勃兰登堡选帝侯“铁牙”曾经相信歌集和游吟诗的价值一样,他认为普鲁士艺术家的价值也在于称颂德国的英雄。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在柏林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纪念碑。纪念碑的两侧饰有胸部丰满的天使和兴高采烈、身披铠甲的半人神。他在蒂尔加滕公园开辟了一条路,两旁耸立着霍亨索伦家族历代统治者们庄严的塑像。他修建的这条“胜利大街”粗俗不堪,但这是他赋予给这座城市的一个礼物。它使“那些即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相信,只要付出艰辛,只要努力奋斗,理想就能实现。”
他需要的艺术,一方面要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要起到恐吓威胁的作用,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市民循规蹈矩。“艺术若是僭越了我所规定的法律和界限,就不再称其为艺术。”1901年他大言不惭地叫嚷。“如果艺术像眼下时常出现的情形那样,向人们展示的只是苦难与悲伤,或者夸大苦难与悲伤,那么它就是对德国民众的犯罪……这样的艺术应该下地狱。”
德皇修建的胜利大街被戏称为“玩偶大街”。拉特瑙认为它封建愚昧;马克思·利伯曼建议人们看这条“亵渎艺术品位”的大街时应该戴上墨镜;旅行指南出版家卡尔·贝德克尔拒绝给这条大街,甚至拒绝给皇帝修建的所有纪念碑做星级评定。经常来访柏林的舞女伊莎朵拉·邓肯则呼吁市民摧毁这条大街。
皇帝眼中的“罪人”,是柏林的分离派——一群叛逆的画家和雕塑家。这些人崇尚现代主义,将柏林介绍给欧洲的其他画家,比如莫奈、马奈、蒙克和塞尚。凯绥也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画展,结果大获成功,受到追捧。甚至也有军人悄悄地溜进西区剧院去看个究竟。这些军人大部分匿名前来,穿着平民的衣服。因为皇帝威胁说,军官若是去参观这些颠覆传统的展览,将会受到惩罚。

凯绥用针尖不停地在铜板上刻画着。楼下街道上的喧闹声——小摊贩的叫卖声,酒肆里的寻欢作乐声,似乎都渐渐远去。她喜欢钢针刺进铜板的那种感觉,那种轻微一刺就能刺穿真实、坚硬之物的感觉。通过钢针,她攻击画板,嘲弄画板,赋予它生命。她全神贯注地在铜板上刻画出她的理想,用刷子刷去残留的细隙,忘记了在炉子上炖着的扁豆汤,直到汤炖焦了的味道飘来,才想起来。在《强暴》这幅铜版画中,她注入了她最原始的情感,刻画了一个女孩被蹂躏后又被抛弃在灌木丛中死去的景象。在窗户下面的画桌旁,凯绥在完成了“反抗系列”后,开始画“农民战争系列”。该系列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一次起义。这幅画中有一幅《爆发》,描绘了一个和凯绥年龄相仿、身材差不多的妇女慷慨激昂地要求农奴们起来反抗的场景。另一幅画《战场》,描述了一位母亲在一堆堆的尸体中搜寻她死去的儿子的场面。她画中的人物,柏林人都不陌生,因为都似乎与历史上的某些人物有关,这些画都是参照那些在她丈夫手术室里等待、哭泣的男男女女的形象绘制而成。她印制了那么多画,浪费了那么多的铜质画板,但是她丈夫从不对花费说三道四。
时断时续的创造力,起伏不定的情感,连续几个月才思枯竭、两眼茫然地盯视着白纸,抓耳挠腮,苦思不得,这些都让凯绥很入迷,很惊讶。她试着摸索其中的规律,在图标中标出自己的创造周期。她将艺术的力量视为支配自己的力量,发挥想象将性欲和生育联系在一起。但是,除了无休止地害怕失去之外,她看不出日常生活和灵感之间有什么联系。
1902年那个寒冬,她两个儿子都病倒了。皮特的肺不好,汉斯染上了白喉病。在那些漫长的寒夜,她和卡尔两人心情焦虑地照顾着这两个孩子。在没有暖气的卧室,凯绥感到心寒,时常想起她母亲辞世的场景,也常常做噩梦,害怕儿子的生命戛然终止,永远地离她而去。她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害怕,害怕失去,想紧紧地抓住当下拥有的一切。正因为害怕失去,她整日提心吊胆。
春天的阳光白晃晃地再次洒落在他们的病床上,两个孩子开始慢慢康复,凯绥才渐渐宽下心来。她把皮特抱在怀中,让他把头朝后仰,放松肌肉,然后像死去的人那样一动不动。她拉着儿子来到镜子前,借助镜子画自己和儿子的画像,一直画到俩人姿势僵硬了,她也叹了口气,那时才觉得累了需要停下来。“别担心,妈妈,”皮特奶声奶气地安慰妈妈,“你的画很漂亮。”
她的生活与油墨密不可分。素描本、凹雕版、铜版画堆满了画室的各个角落。一位母亲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孩子死了,这一意象在后来的绘画生涯中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承认:“我的画都是源自我的生活。”

生命,正是因为有死亡而有期限,也正是因为死亡而生机勃勃。死亡让凯绥对生命更加留恋,促使她不想虚度年华,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她对丈夫很忠诚,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她对他已无激情可言。她丈夫平常的起居生活开始让她感到恼火。她哭喊,希望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呼吸。她封闭自我,独自游历巴黎和佛罗伦萨。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她便到巴黎和佛罗伦萨去旅行。在那里她遇见了艺术批评家雨果·赫勒(Hugo Heller)。赫勒是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他不仅充满活力、知识渊博,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民主党人。当赫勒去维也纳开自己的画展时,两人开始写信互通往来。1909年,赫勒的妻子去世后,两人发展为情人。
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因为凯绥死前将他们之间的通信都付之一炬。但是那一年却有六幅画幸存下来,使得他们之间的亲密一目了然。在一幅名叫《秘密》(Sekreta)的画中,画家用炭笔勾勒出充满质感的画面,再现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画面中,一个男子正从一名妇女身上站起来,而那名妇女则仰面躺着。另一幅名为《爱情》(Liebesszene)的画中,男子从她身后紧紧地抱住她。那个女人便是凯绥,总是陷于各种情感之中不能自拔,总是纠缠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
在《死神与女子》(Death and Woman)这幅画中,凯绥故伎重演。只不过这幅画中的情人替换成死神。死神反剪她的胳膊,用他瘦骨嶙峋的四肢紧紧地锁住她的双腿,正将她拽进黑暗之中。对于他致命的拥抱,她一面反抗,一面又显得无可奈何。她的头靠向死神,但怀中那赤身裸体的孩子却又令她留恋生命。
“彼此相爱后,难免伤感。”她这样写道,“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难免凡尘所困。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悲伤,生活才变得更加绚烂美丽。人们看到最简单、最人性的场景时为何潸然泪下?因为,最让人恐惧的事实莫过于活在尘世。”
1914年一战爆发时,凯绥四十七岁。她坐在床上,终日以泪洗面。八周后,她的儿子皮特在战场上阵亡,她最害怕的事情变为现实。跟其他众多父母一样,卡尔和凯绥也认为德国需要自卫。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在战场上中弹身亡,被炸或者中毒,长眠血腥大地,他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一开始就被出卖了。如果没有被无情出卖,皮特或许还活着,成千上万的人或许不会死去。但大家都被耍了。”
儿子的死亡让她倍感空虚,她要用创作来填补空虚。她不停地画啊画啊,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麻木自己,减轻痛苦。她计划给皮特雕一个纪念像,雕刻一尊她一生中最大的雕像,将耗费她十八年之久。这幅画的主体起初是他的儿子,后来变成一对哀悼的父母,最后是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的父亲和母亲。这对父母便是卡尔和凯绥,痛苦地蜷缩着,相互紧紧拥抱,孤独,凄凉,失落。1932年,作品在比利时的弗拉兹洛(Vladslo)战争公墓揭开面纱。在弗拉兹洛战争公墓埋葬着25644名德国士兵,皮特就在其中。
凯绥相信,艺术能够,而且应该改变世界。她希望她的作品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让人们付诸行动,有益于人们。当德国青年浴血战场,当德皇号召未成年男子参军打仗,凯绥在一篇社论中挑战皇帝。她呼求:“死的人已经太多!别再让人倒下!”
而与此同时,她开始放弃那些历史题材,不再以过去审视现在。她要对当下有所作为,“因为当下的人类太过迷惘无措,亟待帮助。”在《战争》这一与毕加索画的《格尔尼卡》一样感人的木刻版画中,一位赤身裸体的母亲将刚出生的孩子献给了战争。死神敲锣打鼓欢送狂热的志愿者们投身战场,一群母亲形成一个反抗团体,下定决心不再放弃她们的孩子。凯绥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她不能只是做一个艺术的前卫,她有责任去表达世人的苦难,那永无止境的苦难。

“亲爱的皮特,”她对死去的儿子倾诉,“我要和你一样尽心尽责。其意何为?正如你用你的方式报效祖国,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国家,而且要让我的爱行之有效。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出现在我眼前,时时刻刻地帮助我。我知道你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我只能若隐若现地望见你,好像你隐藏于迷雾之中。我向上帝祈祷,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你的存在,让我可以将你的精气神注入我的作品。”
凯绥如今已经五十二岁。站在她家的阳台上向外眺望,战败后的柏林,悲观绝望,如醉汉般地跌跌撞撞,不知所往。沃尔特广场上,一个在战争中致残的人像螃蟹似的蜷缩着在那里乞讨,战争勋章撞击着金属做的假肢,发出“当当”的响声。两个稚气未脱的老兵,身上的制服肮脏破烂,好像刚从战壕里滚爬出来,此刻正挽着一个妓女的胳膊逗弄调戏。妓女面露饥色,嘴唇如血,稍有不慎就会被这两个兵痞弄死。不远处,一头原本在公园里的大象正拉着炭车。因为,大多数的马匹被人们屠杀充饥了。战败已经剥离了柏林浮华的帝国外表,一览无遗地展现出其外表下扭曲丑陋的躯壳。
(书摘部分节选自《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第十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罗里·麦克林 著 傅敬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04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