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比想象中的还瘦小。圆圆脸,听提问的时候会认真地看着你,用力的“嗯!”一声,眼睛里透出一种涉世未深的少女感。她也害羞,摄影师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远远地挥挥手,让周围的熟人都走开,“你就不要在了吧。”采访当天她将相熟的朋友“驱散”。
朱天心的生活一直被包裹在“传奇”中,母亲是翻译家刘慕沙,父亲朱西甯是小说家,姐姐朱天文亦是作家同行,还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从17岁写《击壤歌》一举成名开始,朱天心参与也见证了台湾文坛这么多年来的变化。而位于台北辛亥路山坡巷子里的朱家老屋,则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文学现场,见证台湾文学和社会格局变迁”。

这是原生家庭,而后朱天心和评论家唐诺组成的家庭,连同二人的孩子——曾经是女儿,如今已是儿子的谢海盟——则构成了另一个传奇。三人至今仍住在不到二十平米的老屋中,由于家里没有书桌,每天早上起来后,三人一同去咖啡馆,坐在固定位置写作。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朱天心很郑重地解释道:“我们完全就是借人家一张桌子,所以也无意去炫耀。到后来很多人在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这么看的,其实只是想说明我们不是在天天搞浪漫。”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如今这种生活方式,朱天心给出的答案坦诚也可爱,她说因为胆小,所以不敢冒险。“我完全不敢考验自己,因为看过很多的同辈,他们会觉得我要养老婆养小孩,是不是等我生活好一点点以后,我再写作。开始走上那一条路,其实是很难回头的。我是很胆小的,会极力地保护自己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无非如此。”

除了文学世家的传奇,朱家三姐妹和胡兰成师生一场的故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74年,胡兰成赴台,移居朱家隔壁,一度为“三三时期”(编注:《三三集刊》是当年朱家姐妹与友人一起创办的文学期刊,曾经召集和启蒙了一代台湾的文学青年)的年轻书写者们授课。
而这本以京都为回忆之锚的《三十三年梦》,记录了过往三十三年中朱天心三十余次往返京都的经历,其中第一次前往,正是因为胡兰成的邀请。1979年5月,朱天心和姐姐朱天文以及三三时期另一位成员仙枝一同来到日本,老师胡兰成将自己眼中日本美好的一部一一向她们展现。从那之后,朱天心屡屡携家人、友人往返于京都和台北之间。有了这本屡次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回忆与当下的《三十三年梦》。
借由大陆版《三十三年梦》出版,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朱天心进行了专访。在访谈里,朱天心谈到了《三十三年梦》,谈到记忆与当下,谈到台湾文学的发展变化,谈到胡兰成,也谈到她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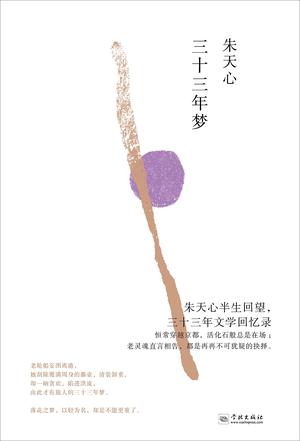
朱天心 著
理想国/学林出版社 2017年7月
作家就是在与主流记忆不同调的时候,敢于逆向行走
界面文化:为什么决定把京都作为回忆之锚?
朱天心:自自然然正正好去了这么多次,要是我去的是伦敦,可能太远太贵,就不会有你问的这个问题了。
第一次去京都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胡兰成老师带我去的,那一次他大概是打定主意,带我们看日本最好的工匠技艺的部分,我对当时的很多风景非常非常怀念。去的时候是樱花季,看一个寺庙的山门,很像屏风美学,很想知道秋天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等有机会去看了秋天,就会好奇下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贪恋看那个风景,一去再去,也很自然自己的生命轨迹就留在那里。从一个二十几岁、刚念大学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女生去,到后来结婚、推着婴儿车去,带着好朋友去,带着自己快要初老的父母亲去。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记忆的依凭之地。
而且京都是一个变动很少、很保留、很珍惜人在那边生活的轨迹的地方,所以现在去还是能看到二十几岁时候的那棵树,或者是当时的某些店铺,寺庙就更不用说了。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谈到,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想要写的长篇迟迟不能动笔,本“想借着因视角拉远以便逃脱掉不须写小说家必得书写的当下,尤其当下年轻世代的世界……但我实在不愿放弃我一点也不想进入那块世界的自尊,遂逃躲到三十年后返身看当下”这样的当下,和你年轻时代时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天心:因为我整天的室友,就是我孩子,一个八零后,我常常不小心就被他床头堆叠的BL漫画砸到头或者是淹没。如果要书写这个当下的话,我必须进入一个够称职的小说家大概都得进入的状态,就是做功课,不管我喜不喜欢漫画,喜不喜欢BL,这是小说家的基本天职。我好像有那个自尊心,心想:拜托我一点都不想要知道这一些,我还有这么多的书还没看。
因为这段话写的是我一本失败的小说,等于逃离开当下,逃离开一个小说创作人应该尽的天职,当然我已经付出代价了。因为三十年后看回来,小事情不用讲了,肯定是化为乌有了,甚至连大事情都是波澜不惊,所以这个小说就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东西。我自己都知道,偷懒或是逃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界面文化:你说的这个当下,是从海盟(天心的孩子)身上折射出来的一个当下。除了这个当下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当下,比如台湾现在的当下?
朱天心:自然也一定会有。就像我携带着这几十年看过的台湾的变化,当然看当下会不一样。好比台湾有戒严解严,在这之后出生的小孩,就像我儿子这一代,自然会有不同。对他们来说,民主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不需要争取的。可是我们经历的时代不是,我们看到一代人必须付出青春甚至付出生命才有自由。所以再看当下的事情,就算年轻人再不满意,对我们来讲都是够好了。
当然我也看到我的同辈,为了要能够取得跟年轻人一样的对话,可能把身上曾经携带过的、属于他的那些个当下都扔光了,因为那些再着就好碍事,好妨碍跟现在年轻人的当下打成一片,会很困难,很扫兴。
台湾这一两年,年轻人会说这是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知道史上最黑暗的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我们说的民国四五十年,你们说的五六零年代,很多的白色恐怖,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被国家处死,埋在山上的,那些才是啊。
所以人要有历史感,会让人比较不会看错事,比较把事情放在对的位置。
界面文化:你强调历史感,我也看到一种评论说,你“拒斥台湾的一切变化,除了’我记得’之事全部奉认。”你会怎么回应这样的评论?
朱天心:那是国族主义的时候,他们排斥一切杂音。好比我们刚讲的,如果一个人对过往的记忆或者是自己的族群故事和主流声音不一样的时候,还坚持说出来,会很扫兴的。我觉得自己在台湾这些年来,在本土化过程中,确实是被大家说“你可不可以闭嘴”、“你可不可以不要说”、“我们现在在打造的是一个我们要的台湾,而你还在那边讲,可是‘我记得’或者是‘曾经怎样怎样 ’,好扫兴!”
作为一般公民,最好学乖点。别说话了,就融入当下,向所有的主流靠拢,甚至去交出自己的记忆。可我是写东西的人,什么都没有,只剩一些这么真实的曾经在场的所看所观察所记得的,我不说,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不会有人记得。也许对很多人来讲,他们是在欢迎一个新的时代。提起以前不光彩的事情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事。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我完全不接受。
一个国家也好,或者是一个个人也好,我们在面对自己回忆的时候,真正健康和强健的人或国家应该都敢照单全收自己的历史,光荣的固然要一提再提,耻辱的也敢去面对,也敢说出来。只选荣光的事情说,非常掩饰太平。
界面文化:你提到记忆,这本《三十三年梦》也算是一本回忆之书,里面很多比较私人的记忆,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部分来呈现?
朱天心:可能跟我的长篇迟迟写不出来有关系。因为我几次尝试写长篇,大概都是各写出第一个章节,可能有三四万字,然后戛然而止。我发现我在写了三四十年之后,犯了初学者的错误:一个人物出场,我很急着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话塞到他嘴里,强要他说,把他当成是一个木偶或者是傀儡。因为屡试屡失败,我意识到该先清理一下个人的记忆,应该把自己的记忆先打包好放到旁边,我才能轻装出发,来好好面对我的小说。
界面文化:这个长篇是关于什么的?
朱天心:最松散的主题大概是我在场的五十年的台湾。大概从我开始记得事情,看到事情,然后有意见不吐不快开始。
界面文化:这五十年,台湾的政治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觉得在这种背景下,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朱天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和主流整理过的、选择过的集体记忆不和的时候,通常是很慌张的,会觉得很危险。大家明明说那件事情是那样的解释,有人说:“不是不是,我记得的不是这样的。”我说的不是政治上的灭口,而是整个处在一个社会里头,就是等着被封口,或者你就是一个很扫兴、很不识相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作家的工作,这个社会,尽管在整理选择之后,已经这么多人都放弃了或者是选择了可以合于主流记忆的时候,天下之大,哪会不能容一个不同的人,不与时人同调呢?有时候这才是最动人的。它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当这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追寻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人若有所思地逆向而走,插着口袋望天空,或者吹着口哨,那个景色好动人哦。作家之于他的时代,其实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他站在不一样的位置,诚实勇敢的说出他所见所想。
现在的文学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它好像耳根清净一点
界面文化:在2011年你来大陆的时候,你说大陆的情境让你“想起三十年前的台湾”,能否详细说说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
朱天心:三十年前,我差不多刚开始写作,我觉得那时候的台湾对于文学之于一代人的生命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的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那时候我念的是一个精英女校,我只要回想那时候的同学,她们将来不管是念医、念商、念法,甚至念农,都会去看几本小说,看看文学。
现在除非一个人将来要念文科,甚至是外国语文或者是文学,才需要去看文学,而且还不一定是很全面地看,只是为了应付课程看,多看好像吃亏了,这跟三十年前把书店当成探险之地是两样的。那时候人要得到远方的新知、得到人生的一些诫言或者是比较深刻的思想,都要从文学里头找。文学是生活的事实。可现在的台湾不是这个样子,远方的事物不需要通过文学知道。现在通过网络就可以看到撒哈拉沙漠,看到撒哈拉的一场婚礼是怎样的,一只狐獴是怎么样的,不用再去看三毛。
现在的文学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它好像耳根清净一点。所以那时候来大陆会想起三十年前的台湾。当然也可能是我过度乐观,也许就那么些人,并不代表他们一代之人,或者说在场的人代表着背后一个相当庞大的读者群,这个我没有研究。可是起码从在场的人里,你会看到他们很像三十年前的台湾。他们还觉得文学是生活必要的一个基本事实。可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大陆怎么样。
界面文化:我会觉得你描述的场景会更像八十年代的中国,读书热的时候。所以感觉大陆和台湾在这一点上,像是一个平行空间,都是在一个时代因为一些原因,有了那样一个热潮。也有人说大陆和台湾在那时候,在文学上,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台湾当时是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争论?
朱天心:应该算是六七零年代吧,最先是像白先勇他们,大学的时候都是念外国语文系的,然后他们办杂志,他们在实践的、在练习的、在引进的理论全是现代主义。当然几年以后会引起一个很大反弹,不管叫写实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还是乡土文学,这些人觉得现代派那些全是外来移植,没有根的东西,不适合华人,我们应该写自己的东西,要凝视我们在地人的土地,人民,而不是把国外的那一套现代主义的描写拿过来。
所以有一阵,尽管白先勇他们的读者群非常庞大,大家也喜欢看他们的东西,可是他们会被这个理论打压得很厉害。当然后来文学史会稍微还他们一个公道,说其实他们这么做也是个逃逸的出口。在当时国民党还是很一党专政的时候,控制言论自由,不能办报刊,不能上街说话的时候,他们的文学是一个排解苦闷的出口。所以他们看起来是在谈现代主义,其实是在谈台湾当时政治高压气氛下的出口。我觉得帮他们讲话的成分比较多,因为我不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可能有一两个人是这样,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其实也就是流行。
界面文化:在那个时候,你的位置在哪里呢?
朱天心:在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写作。我只能写我会写的。小女生在大学里头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写政治正确的东西,还是要写真正感受到的。那时候台湾已经开始有文学奖了,每年得奖的都是写实主义的东西,写台湾的矿工、农人、劳苦大众。我有些同辈为了能获奖,即便他可能就是一个台北人,从来没有过任何下乡的经验,也勉强来写。当然那个结果是很惨烈的,因为处处是漏洞。没有得奖还是小事,自己的那种很微弱的写作初衷从此就不在了。
我在那个时候曾经困惑过很久,我的父亲可能看出过我的困惑,他有一次就讲“要是我现在写,我的每一个小说,都有把握写得比你好,那是因为我的阅历。可是要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台北女孩的话,我一定写不过你,因为我无法想象你们是怎么看世界、怎么看街景、怎么想感情的,我无法装得那样天真,像一张白纸来看待这些。”
这确实给我很大的启发,诚实面对自己能写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要认真地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五岁,哪怕很幼稚。比如那时候刚看完《战争与和平》,怎么能有耐心去写小爱情故事?大家都想写大时代,大的题材,了不起的故事。可是那时候我会想,我只有很诚实地写我的十五岁,我将来也才能够很诚实地面对我的五十岁。当然不是说作家在什么年纪只能写那个年纪,而是说诚实面对自己,哪怕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题材,这是对作家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和一个锻炼。台湾在变化这么多的几十年间,我始终都没有跟着当时候的政治正确起伏或者东倒西歪。

界面文化:你刚说到诚实地面对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就把十五岁的状态记录下来,这其实可以联系到一个小说家和他所描写的世界的关系。对你来说,这个关系是怎样的?
朱天心:其实都有变化过。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小说作者把看到的东西,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灰尘也没有,一点扭曲都没有地呈现出来,这是小说家天经地义的事。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不行,因为人是有机的,是有想法有感情的。
光看我和天文,我们差两岁,同样住在一个屋子里,到现在还是。我们都没有分开超过一个月以上,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对父母,我们感觉的是同一个温度,看的书甚至很多都是重叠的,可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这么的不同。所以承认吧,人不可能像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一块玻璃,可以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映照现实。
我的个性很强烈,很黑白是非分明,我会觉得那就把这些或许带着偏见、或许带着跟人家强烈不同——不管是站的位置还是携带的价值观——好好地、有品质地表现出来吧,甚至更进一步,让人家在看得时候赏心悦目,不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疯子,一个扫兴的人。
像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一样,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把特洛伊迎进来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喊千万不能,因为她有预言的能力,可是没有人信她的预言。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被下了咒诅,明明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喊破喉咙,大家就觉得我是个扫兴的人。在那段时间,只能自我承认,对自己说:你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不带任何意见反映真实的人,那就好好厚置你的意见、你的看法和你的勇气,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希望可以被欣赏。
人和城市之间的互动与感情是城市书写的开始
界面文化:你提到最早的作品是讲一个少女,有点像游荡者,在《三十三年梦》里也有这种探索城市地景的感觉,是一个城市文学的样本。北大中文系的陈晓明老师认为大陆的城市文学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你觉得城市文学应该有什么样的质感?在台湾、在大陆或者是在国外,你比较喜欢的城市文学作品有哪些?
朱天心:还是应该回到人,回到人最自然地跟他所处环境所发生的关系或者是互动。有些城市并不提供这些。不是每个城市都这么幸运,让人跟它有一个很正面、很快乐的互动关系。得先有这些前提,才会有人想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情记录下来。
除非你住在乡下,如果你住在城市,你早晚会写到它,其实台北市也很不乏这些作品。比如我在写《古都》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写的台北是很消费的,好比哪一个咖啡馆很好,哪一个书店很好,哪一个街景拍一拍很美。可是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东西正在快速流逝,那时候陈水扁是市长,他擅自把一些地方的地名改掉。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地方的名字就是人的记忆,所以他是在擅自改动记忆。好比台北有一个新公园,日据时代叫台北公园,在国民党时代叫新公园,陈水扁把它改成二二八公园,二二八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的一次跟民众冲突很严重的事件。名字不是不能改,可是这是一代之人处理他们记忆的问题,不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我要形塑一个什么历史,就把它改成一个什么名字,从此大家的记忆就只剩下这个,忘记了日据时代台北公园是怎么样的。
在那时候我感觉到,要是时代自然地进步或者改变和流逝,老树被砍掉,道路被扩宽,老房子被拆掉盖大楼,社会要进步,商人要赚钱,尽管我很讨厌这些,可是我勉强可以接受。但我很受不了的是政治力的介入,像刚刚举例的,把一个公园改名,把一些公共地点擅自改名,就是要从此改掉一代之人的记忆和历史,所以那时候写《古都》,是在记录下这些,把看到的正在流逝的老房子老树记录下来,我很好奇它们之前是什么样子。

朱天心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2月
可是我真是觉得内举不避亲,近来看到的最好的写城市的作品,是我儿子盟盟写的一个作品《舒兰河上》,他索性把台北整个掀起来,写它的地下水阵。清朝的一个官员去台北的时候曾经留下文字“康熙台北湖”,那时候台北是一个湖,后来康熙年间的一次大地震让官渡那边裂了一个口,水就大部分排进海里,可大部分还是留了浚沟。所以清朝时候开垦它,日本人统治时期归并它,到国民党时期基于城市进步,把这些已经没有农业价值的沟盖上,到了近代又要盖房子。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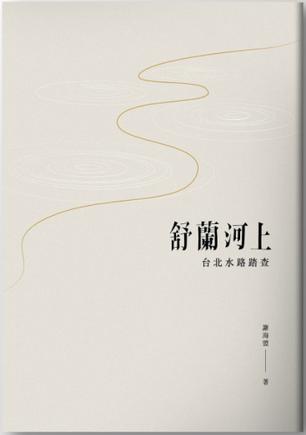
谢海盟 著
印刻出版公司 2017年7月
海盟就是把地都掀开来,他看清朝台湾的地图,看美军轰炸时候的地图,看现在的卫星图,看google地图,看把这些都叠加起来,看明明该在的一条河流到哪里去了,是怎么流的。我也和他走了很多地方,我们像探案一样有几个线索,看那条河究竟去了哪里,留下了什么痕迹。我觉得他写得超好的,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而是因为有人这样深情款款对待他所居住的城市。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因为当时看宫崎骏的《神隐少女》很感动,失了名字就是失了记忆,就像里面那个白龙,完全丢失了记忆,到有一天女孩子想起来了,告诉了他他的名字,他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身世。海盟也说,他很想告诉那些在台北,人人不知道的那些地下河流:你的名字其实叫什么什么。
可能是非得时间够长,那个城市蛮值得人家爱它,或者是疼惜它,或者是因为它快速的流变让人家不舍得,才是一个比较有可能的书写的开始。
胡兰成对文字、对文学超认真,认真得有点傻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非常在意人格与作品之辩,因至今我仍相信,此二者不可能可以断裂的,人好都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但人格自私卑劣扭曲阴暗的终有一天是无以为继的。”这让我想到台湾之前的林奕含自杀事件,林奕含在一个采访视频中曾经说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国华的原型是胡兰成,林奕含继而发问,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更进一步,艺术会不会从来就是巧言令色而已?对此你如何看待?
朱天心:我觉得林奕含的问题是她想要开脱自己,就像有些人,明明喜欢的在我们看来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但她把自己想成林黛玉,对方是贾宝玉,很不幸他每一个女生都爱。有人也许会在这个上头把自己的感情给举起来,这个我可以同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说回到胡兰成,胡兰成在政治上的部分我完全地、一点都不介意。我是念历史的,我们都是从后头看回去,会觉得那时候你当然要主张抗战,抗战八年就能打赢,所以事后回看,你当然应该站对边。可是从当时来看,是“天下可以共逐之”,谁的路线都难说。当然我完全不排除,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阵营都会有那种幸进之徒,甚至是靠着出卖来谋求升官发财。
我其实很耿耿于怀这一点,大家说你们怎么会认一个汉奸当老师呢?我很在意这一点,所以我看了非常多他当时候写的政论,这个政论是白纸黑字留下来的,日后没有机会去选择性的涂改。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只是选了一条不同的主张。后来历史证明了是蒋赢得了那一次的胜利。可是把镜头再拉远一点,可能又不一样。所以要看要让历史停在哪一点。
从这一点来看,胡真的是好幸运,能够留下当时的呈堂口供,可以有清楚的轨迹看到他的想法。当然大陆在民族大义上是比台湾还要抓得紧。在台湾现在已经是很虚无了,觉得都无所谓了,所以我已无意在政治上或者历史上帮胡辩护。
至于感情上的部分,那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了。我是那种有感情洁癖的人,会很在意他东爱一个、西爱一个,唐诺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唐诺会说胡毕竟是伤害到别人了。尤其是看张爱玲后来的一些出土的作品,可以看出来。
我看过他最后在日本和胡奶奶一起的三十年,我难免也会觉得,他以前真的是因为战乱,一战乱真的不知道明天还活不活。后来他在日本,跟着胡奶奶,就老老实实,安安分分,三十年到死。我也不是要帮他说话,在感情上头,我无意说服任何人,可是对我来讲,那大概跟人品不是很有关系。因为他真的是我看过的一个真的像贾宝玉的人,他真的对每一个都是百分之百,照理数学上这是不成立的,不可能有好几个百分之百。硬要问我的话,我大概目睹到的是这样子的。
界面文化:所以在你看来,他对文学的态度是怎样的?
朱天心:我倒是觉得他对文学、对文字超认真的,大概认真到有点傻。虚无的话看起来多轻松,永远不会有失败。我也有几个很虚无的朋友,种种都会令你着迷,但胡是一个对文学、对文字、甚至对政治是一个认真到蛮傻的人,不会保护自己。倒很多事情其实可以盖一盖,或者不说出来不会有人知道的,如果他不说他在逃难时候遇到的范秀梅,谁会知道啊。
所以我看林奕含的时候是很同情的,觉得她好像把那段其实是很丑陋的感情,借着文学的飞跃把她抬起来,让自己比较好过,让自己比较能对自己交代。
界面文化:我第一次看那个视频的时候特别震撼,我觉得她经历的困惑确实也是大家有时候会经历的,如果一个人很认真对待文字,某一刻发现作者的言行是有出入的时候,会比较痛苦。你对这个怎么看?一个人的作品和人品的关系。
朱天心:只能说有时候看你幸或不幸,我的很多朋友都写作,我常常觉得,最好不要认识他,只当他的读者就好了。认识他就觉得,明明这么笨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或者明明是一个很胆小怯懦的人,为什么能够写出非常豪勇的作品。
可是我多少会觉得,就像书里提到的,如果断裂是这么的巨大,其实是很无以为继的,也许他的聪明和才情可以使得他掩盖一时,可是很难走完整个文学的路,他很快会撞到屋顶。
界面文化:对你自己而言,作品与为人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朱天心:我会非常要求这个,不关乎你在写作的作品,你写的可能是男盗女娼,可能是乱伦,写的是很猥亵很不堪的,但是这跟你的为人处世是不同回事。因为我也很怕会误解说,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道德表率,真正的道德表率,那些人写东西一定超难看的。所以中间很微妙,我也很难去说什么事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可是我很在意这一点,非常在意。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对族群、对血缘、对种族有歧视、有误解,我都会说个不休
界面文化:你年少成名,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冠以“美女作家”的称号,在之后那么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你如何和“美丽”和“女性”这两个标签相处?
朱天心:“美丽”其实还好,因为始终有比我美的天文或者是天衣存在。而对于描述我是一个女作家,我早年是会很不平的,我会觉得为什么不说男作家,作家就该天经地义是个男的吗?包括我早期的作品被王德威批评说写猫狗小事,生活琐碎不堪,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对女作家这个部分是在意的,尽管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当然我不是一个很激进,或者是很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有我的理由。我们家三个女生,爸爸永远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到有唐诺和我们一起住,做饭的是唐诺,我们其他女生都不会做。所以我们家始终是一个男女非常不平等,是一个女权高涨的家庭。再加上我是写作的,也不大会感觉到公司里、职场里那种性别歧视。这会使得我在女性主义上头缺乏动力,它在我的价值序列里是排在很后头的,我得承认这一点。可是对于其他的,就真的比较不是我在意的。我甚至好高兴我做的是这一行,除非老年痴呆了,不然可能是年纪越长,越是黄金时期。可是对一个模特、影星或者是运动选手,可能到25岁,不管多努力,就是一个往下坡走的状态。所以我好高兴我的行业是一个可以寄托在不用注定是往下走的状况。
界面文化:也有人评价你,长期以来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文化象征,已经被用户与批判阵营双方的大量论述淹没、以致本体难现。”对此你有何看法?如何在政治、社会思潮的洪流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朱天心: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如果有余地,我一定会选择人多的那边,安全的那边,历史之后会证明是对的那一边。可是这好像由不得我。我也被王德威批评说,台湾已经大步地向前走的时候,你还在后遗民,可是我觉得确实是,我会有那样的心情,我觉得在台湾,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对族群、对血缘、对种族有歧视或者有误解的时候,我都会说个不休,哪怕历史列车已经轰然开走了,或者这一页已经翻过了,我都会说且慢且慢。说得连我身边的人都不耐烦了,连天文都不耐烦了,天文说你应该不要停在那边了。所以好像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界面文化实习生刘雯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
更多专业报道,请点击下载“界面新闻”APP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