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比较文学。每一学期开始的时候,如果我计划在这门课上讨论我自己的作品,我总是会给新来的学生们讲一个关于写作和教学的老故事。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很可能不是真的),是一则关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轶闻。1957年,有人提议让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担任俄语文学教授,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个决定。“如果俄语文学要由伟大的俄国人来教,”据说哈佛大学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当时是这样跟自己的同事说的,“那么我们必须得请大象来系里教动物学了。”
学生们都笑了,接着我提起了手头的话题。“这一学期,我站在这里讲课,就像是一只大象,但是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一名教授。”
大象并不知道是什么使它们成了大象,它们就是大象。同样,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当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想要去描述和表达的东西,他们希望概括的范围,可能会和读者、学生关注的不同。作者通常不是解读自己作品最好的人选,最终其他人可能会比作者本人对文本更熟悉。
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多数聪明的学生都非常清楚这些悖论,因此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尽管之后我偶尔会提醒他们:“现在我所要说的话不是站在一个教授的角度,而是教室里的一只大象。”
比如说,在我解释之所以写《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这本书的原因时,我可能会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我22岁,想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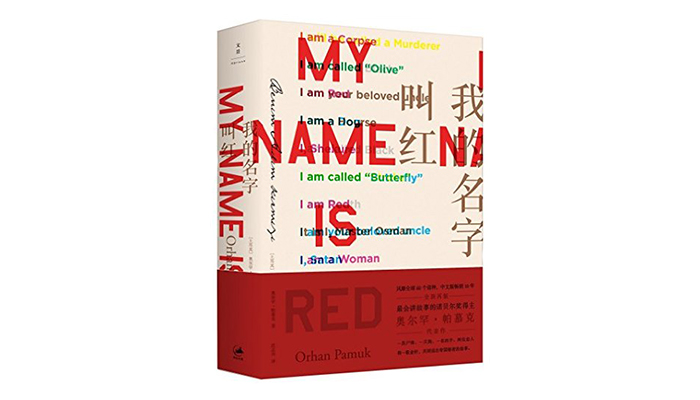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沈志兴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2月
“在这本书里,”我说道,“我尝试着去构造一个故事,故事的灵感来源于画家所预想的,和他自己的手有时自动画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反差。”
接着作为教授的那个我插进来了,说道:“这种反差就像是一名小说家和一名教授在讲授小说的艺术时之间的差别。”由此也导向了约翰·伯格提出的问题——“观看的方式”,约翰·伯格自己是一名小说家。它还让我们思考东西二分法——东方波斯的细密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历史。
或者在讲到我的另一本小说《雪》(Snow)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作为教室里的大象,我能告诉你的是,发生在小说主人公卡(Ka)身上的一切,也就是书里提到的前200页,几乎就是1999年我去土耳其的卡尔斯市(Kars)时所经历的东西,卡尔斯是书里的背景。像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他将小说的背景放在贫穷而深受困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想写一本政治小说,这本小说能够涵盖整个国家。”
尽管我试着去抵御这样讲述的诱惑,在课堂上,我还是比学生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民族小说”(novels of a nation)看作是对土耳其文化准则,特别是土耳其灾难、以及中东地区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介绍。原因是我对“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很感兴趣,有时我还会将自己的作品“理论化”。
“在这一段中,作者是想要探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和商店的历史。”
又或者,我会说:“在伊斯兰社会里,男人和女人很少打交道,除非他们结婚了。男孩和女孩会发展出一套相替代的语言系统,由特殊的语法、沉默的注视、皱眉、片刻故意的静止和一些针对性的问题,类似于‘你想再要一个肉丸子吗?’组成。”
但是究竟要将多少注意力放在土耳其历史、伊斯坦布尔变革,或者伊斯兰教和现世主义上,学生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小说的逻辑呢?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同压缚在文学上的政治压力作斗争,在课堂上讲授小说的社会背景、政治反讽,而不是品味文本的细微区别,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叛徒。不管我是在讲自己的小说,还是在讲《安娜·卡列尼娜》、《达洛维夫人》或者《红与黑》,不论我讲的是什么,我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在背叛真正的文学。这种感觉停留在我体内,它让我心痛。
十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避免这些焦虑和冲突的最好方式是远离理论和社会背景,是同我的学生一起重新发现文本自身的微妙,不管这文本是我自己的作品还是别人的作品。因此在每堂课开始的时候,我会找出一些时间仔细研读那一天我所安排的任务。
“让我们来分析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会说。“为什么你认为卡要将会议安排在亚洲旅馆?”“这一节里有哪些重要事件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在这几页中,你觉得占主导的情绪氛围是什么?”
像大多数中上层阶级的土耳其男人一样,我身上也有一种威权倾向。尽管我喜欢在对话中教学,我总是忍不住告诉学生们我的小说的“事实”是什么。即便如此,当有学生指出了多年前我所写的一部小说中的怪异之处时,我仍然会感到惊奇,怀疑自己当初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过。
任何时候,只要当我把理论和社会背景放在一边,选择对小说进行“细读”,寻找其中的微妙之处和内部对称时,就会发现我对自己的小说竟然这么不熟悉。有一天,在快要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看到了我在教室外正疯狂地翻着《雪》,他开玩笑说:“这就是不阅读的后果。”
他脸上那副带着揶揄和淘气的表情,我有时会在其他学生身上看到。当这个表情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我的小说中注意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或者他们不认同我所说的小说的逻辑是什么,并且向我指出了其中矛盾和含糊的地方。但是在多年讲授自己的小说之后,当我再看到这样的表情时,我的学生们教会了我这样去思考——“或许他们宁愿教室里站着的是一只大象,而不是一名教授”,这个想法是令人欣慰的。
(翻译:朱瑾东)
来源:洛杉矶时报
原标题:Orhan Pamuk: Sometimes, to teach a novel feels like a betrayal of literature
最新更新时间:09/01 10:21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