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作者:(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译者:周全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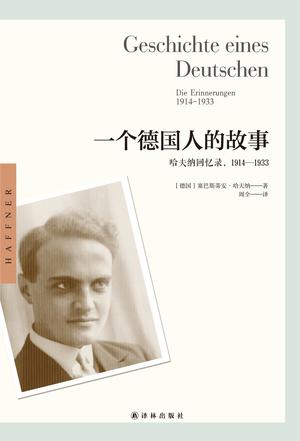
2000年,德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本“爆款”回忆录作品。已于1999年逝世的德国历史评论作家、记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1907-1999)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被家人整理后交由出版发行。
哈夫纳所著的这本《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之所以会在几十年后出版成为名动一时的畅销书,并引发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的热烈讨论,主要是因为书作者作为德国一战战败、20世纪20年代经济困难及30年代初期纳粹夺权、迫害犹太人浪潮等历史进程的亲历者,详细描绘了这些进程中他本人、他的家人、身边的普通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一个理性节制的民族如何卷入政治和种族狂热,并一步步滑向排外狂潮和世界大战。这本书以极其细密翔实的“在场”叙述,揭穿了日后那些宣称对于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和杀戮真相一无所知而不愿承担责任的德国人的无耻谎言。
有意思的是,因为《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是在战争开始前就作出了纳粹必败的精确预言(这看上去有点像是事后诸葛亮),书作者当时身边聚满了被战争狂热挟裹的德国平民,但他自己保持着超然冷静(这看上去有点不太真实),所以,这本书出版后,一度引发是否伪作(他人伪作或作者在战后以战前时的口吻撰述)的争议。直到哈夫纳的家人将书稿送交警方勘验,证实原稿最晚于1939年完成。
哈夫纳的青少年时期,曾一度作为欧陆最强国家的德意志帝国遭遇了最为重大的国家危机。凡尔赛和约的核心就是肢解、羞辱和削弱德国,这使得德国经济陷入分崩离析,背负着失败国家耻辱的德国人并不甘于接受命运。极端民族主义在持续经济危机期间进一步发酵,演化为纳粹法西斯主义,这个国家相当数量的民众至此已经形成了极其浓厚的排外和对外征服复仇的冲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发动二战,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意志驱动的结果,不能用历史的偶然来加以解释。
等到哈夫纳大学毕业,进入柏林高等法院实习,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党在德国肆无忌惮的展开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还诉诸暴力来清算德国政治左翼势力。整个德国因此陷入排犹、极端“右转”的狂热之中。连一向被认为能够独立于王权或世俗政治权力的法院,也屈从于纳粹党,用希特勒的旨意来替代法律。在经过几年的无效抗争后,哈夫纳追随身为犹太人的女友移民英国,之后成长为一名历史评论作家。20世纪50年代之后,哈夫纳返回德国,曾出版《解读希特勒》、《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等畅销名作,还长期撰写政论,对于(联邦)德国政治领域任何可能导致重蹈历史覆辙的迹象发出警告,并因此赢得了崇高声誉。在他去世后,德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德国)最严厉的批判者”、“最聪明的捍卫者”。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这本书开篇是从哈夫纳童年时期(1914年一战爆发)谈起的。相比二战,一战时期的德国,尽管居民也涌动爱国主义热潮,并因此对于德国的战争前景保持着盲目乐观,但还远没有进入后来的那种疯狂状态。当然,这场战争中,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在二战后又会重现——“这在日后演变成一种憧憬,而纳粹主义的吸引力、简单性,以及对幻想及行动狂热所产生的要求,也就来自这种憧憬”。哈夫纳坦言,战争及封锁带来的饥饿,并不足以遏止战争的延续,事实上,在战争结束时,人们所感受到的却是恼怒、恐惧、“没头没脑的射击事件和混乱。”
一战结束后,德国一度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但很快就被遭残酷镇压。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处决。哈夫纳认为,这开启了之后德国政坛清算政敌的暴力模式。实际上,战后不久,德国国内就已经出现了法西斯社团的雏形,只是参与人数还没有发展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的那样多。
战后的经济崩溃,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德国民众“心灵上的器官”被“摘除”,从此不再像过去那样“脚踏实地、保持平衡及稳重”。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德国遭遇的经济困难有关,德国马克在短时间内发生多次的、幅度惊人的贬值,以至于数万马克的月薪拖上几日,就只够孩子买一点儿零食。为了尽可能降低货币贬值的影响,当时的德国民众竞相购买股票(股市升幅与货币贬值幅度大体相当),并在发薪日一口气买齐一个月所需的生活物资,哪怕部分食品无法完好的储存一个月。
美国借助道威斯计划让战后德国摆脱了困境,之后的几年,德国经济重新进入平稳阶段。哈夫纳意识到,尽管德国社会重新进入安宁状态,但知识阶层也好,其他阶层的平民也好,都进入一种可怕的空虚和无聊状态。人们看不到国家发展的前景,不知道哪一天会再次发生与英法俄等国的战争,所以甘愿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或参加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机会,用民族主义符号给自己打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段时期(1924-1926年),德国的年轻人突然热衷于各种体育项目,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国内外体育大赛,并将能够获得国际大赛奖牌的运动员奉承为民族英雄——当时的德国被限制了军队规模,还没有洗刷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耻辱,所以体育比赛中夺得良好成绩,就被看成是在另一个战场为国家争夺荣誉。书中提到,尽管当时德国的主政政客施特雷泽曼意识到了体育狂潮滋养了民族主义狂热,但他为此发出的警告已经不受欢迎。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为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创造了绝佳机遇。《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书中记述了这期间,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大众、德国政治团体、德国媒体是如何一步步在希特勒及其统御的纳粹政治势力面前作出让步,一步步放低底线。这样的绥靖妥协姿态,不但没能换取纳粹抱以慈悲,而且还助长了更多的粗暴甚至杀戮。哈夫纳说,纳粹非常精明的把握了战后德国人内心的恐惧,“与其被围殴,那么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去揍别人”,这样一来,在“一种没头没脑的飘飘然感觉”之中,逐渐的是“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觉”。
书中也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是如何从极端化政纲主张,变成大众赞同及驱动行动的信念。实际上,德国人对于纳粹宣传的反犹主张认识得清清楚楚,甚至将之列为纳粹政治观点中的瑕疵,但就是因为信服纳粹所制造出的民族狂热愿景,所以人们甘愿忍受这样的“瑕疵”,配合执行对犹太人的排斥、压制以及之后的屠戮。反犹主义就是这样从纳粹党的魔瓶中流出,扩散到德国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各行业企业及社会的各个角落。
希特勒上台后,发生了疑点重重的“国会纵火案”。但当时的德国公众已经宁可相信案件就是纳粹党的敌人所为,或者虽然不信,但不愿以自己的力量去表达反对。哈夫纳曾与其他一些德国青年组成学习小组,讨论政治、哲学、社会问题,但这样一个可以说由当时的德国青年知识精英所组成的松散团体,也发生了危险的分化,小组中的多数人陆陆续续成为了希特勒的拥趸,热切的投入自己之前绝对不屑为之的“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崇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