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受到热议的两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呈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交锋。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两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话题,首先是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发表于“腾讯·大家”上的《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一文所引发的争议,其次是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南希·弗雷泽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历史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暧昧关系的梳理。
将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有几个有趣的发现。首先,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权理论脉络的无知与漠视是他们误解、曲解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先不谈对西方女权理论的涉猎程度,田文中列举的一些国内女权主义者的言论也大多来自她们接受采访或者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但事实上,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专著或文章中对女权理论和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做出过专门的论述,如果对这些论述稍加了解,便不至于写出这样漏洞百出的“纠错”文章。
其次,性别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性别议题,它从来都与阶级议题纠缠在一起,这正是性别议题的复杂之处。田文充满了低级错误,产生这些低级错误的原因不仅是作者治学不精,还有假装“理中客”的作者政治立场先行,才导致其对于许多问题的片面理解。从田方萌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他与他批驳的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分歧,不仅在于女权男权,而且在于左翼右翼,例如他肯定自由迁徙的价值,却忽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外来劳工的剥削,他信奉个人主义,赞颂个体的自由选择,却对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结构性的歧视和压迫视而不见。
而弗雷泽的文章正提醒我们,在左翼浪潮中诞生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也曾在阶级和“经济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导致了女权运动内部的分裂,厘清这段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权理论和实践的现实困境和未来挑战。
错的是女权主义者,还是男公知的无知和傲慢?
3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虽然自己也信奉性别平等的原则,但对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论调实在难以苟同。
文中列举了戴锦华、李银河等数位知名学者、女权主义者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言论,并认为这些言论中存在“轻视事实”、“忽视异见”、“漠视成因”、“无视后果”四类“错误”。文章刊发后不久,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专业在读硕士王笑哲就在一篇题为《“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的文章中对田文抛出的这“四大罪状”进行了逐一的回应和反驳。
首先是“轻视事实”。田方萌举出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戴锦华表示,“研究发现,一个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抱着一个婴儿的母亲是一种‘社会隐形人’,她随时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关心她。”田方萌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女性的自杀率,就会发现戴锦华所言不实,例如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加拿大自杀率最高的女性并非幼儿的母亲,而是更年期女性。而在我国自杀率较高的1999年,65-74岁的老年女性为每十万人39.2人,远高于25-34岁育龄女性的18.3人。
在另一次访谈中,戴锦华将女性移民称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田方萌认为这一论断是戴锦华本人的偏见,她将女性移民全部想象为低技能的打工妹,而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往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中就有一半是女性了。而一旦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力,女性就有机会移民到在性别平等上做得更好的国家或地区,借此她们才得以逃离“最深重的剥削深处”,而不是相反。

但在王笑哲看来,田方萌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歪曲了论题,虽然他引用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都没有问题,但“女性有迁徙自由”并不等于“女性没有受到剥削”。事实上,移民到美国的女性中,有41%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工作,而在所有因移民身份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中,女性受害者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接下来,田方萌将矛头对准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女性与哲学》一文中,崔卫平认为,在历史上,女哲学家凤毛麟角的原因是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具备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田方萌针对这一论断举出了两个反例,首先,如李清照和勃朗特姐妹这样不仅受过教育,而且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的女性也并没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其次,男性哲学家也并非都生活宽裕,被驱逐出境、靠磨镜片维生的斯宾诺莎,以及出身贫寒、疾病缠身又遭遇十年牢狱之灾的葛兰西也都曾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借此,田方萌打开了对男女差异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造成的这一根本问题,它涉及到性别不平等的源头。王笑哲的文章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他认为,一些女权主义者承认,两性差异部分是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但关键不在于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而在于哪些差异被我们政治化了。例如,女性由于是潜在的孕妇而被一些企业在招聘环节歧视,“能怀孕”的确是女性与男性在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但这一差异本身不应该被加诸任何的价值判断,因为这种价值判断是社会化的,性别不平等也必然是社会化的。这是美国哲学家、性别研究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朱迪斯·巴特勒对于“如何确定两性差异完全是社会化导致的”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漠视成因”中,田方萌就女性的就业率、生育率和收入水平等问题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数据做出了错误的解读和归因。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认为1990年代国企改制之后,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因为有数据显示,与1990年代相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相对收入都大幅下降了。而田方萌则认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其社会地位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因为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7年的数据是61%)实际高于美国(56%)和欧盟(51%)等发达国家,而在非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埃萨俄比亚、卢旺达等),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反而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田方萌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夫妻双方不得不同时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而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女性就有了更多选择,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就足以维持家计,而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不难看到这样的男女分工,因此,劳动参与率低,很可能说明女性的经济状况实际改善了。至于女性的相对收入下降的问题,田方萌采用了同样的解释,即为了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女性可能会选择工资较低但相对轻松的工作,回报高责任也更大的工作则交给男性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妻子的可支配资产更少了。
田方萌指出,妇女回家并不一定是社会的倒退,女性退出工作场域,也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下降,成为出色的职场女性和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两者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而贬低家务和育儿的价值是女权主义者偏狭的看法。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选择的权利。
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举出了日本学者仙田幸子在2015年出版的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英文专著,他认为,在这本书中,仙田幸子将日本1980年代出台的禁止性别歧视的立法及其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冲击作为日本低结婚率和少子化的原因,正是因为女性在工作和婚育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才会出现晚婚少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现象。
北大飞在其个人公众号上指出,田方萌对仙田幸子著作的解读是“匪夷所思的断章取义”。北大飞指出,近年来,对于日本和韩国社会少子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主流学界对其基本成因的看法高度一致,那就是由于职场上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对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婚育。尽管1980年代开始落实的一系列平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风气,让女性在职场上有了更多机会,然而,传统的男权社会并没能跟上女性进步自强的步伐,全职女性的丈夫们仍然顽固地拒绝承担育儿义务,企业也拒绝为女性员工提供育儿上的福利与保障。这种状况导致了女性必须面对工作、家庭二选一的难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不断推迟婚育年龄,甚至干脆不婚不育,低结婚率、少子化的问题由此产生。
北大飞指出,仙田幸子的著作一共分为六章,除了第一章的简介和最后一章的总结之外,第二、三章讲的是日本社会的变化促使更多女性走向职场,而第四、五章讲的则是日本职场对已婚已育女性的不友好又如何导致了部分女性放弃婚育。而在田方萌的引用中,不仅第四、五章的内容完全消失,第二、三章的内容也被严重歪曲。事实上,仙田幸子本人在书中明确提出职场应该为雇员的家庭-事业平衡提供方便,并呼吁相关政策出台,这一立场的前提是充分接受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参与劳动的权利,而并非意图通过牺牲女性的职业发展,来解决低结婚率和少子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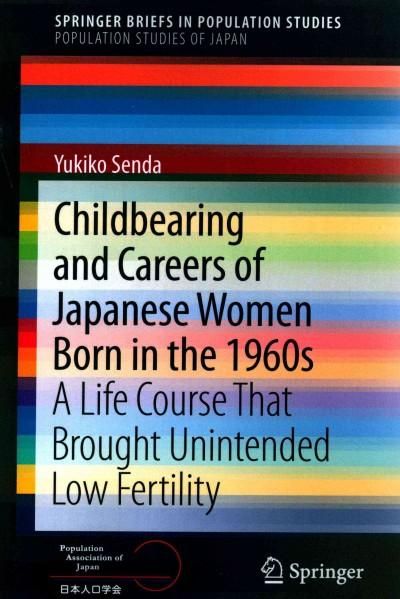
而对于田认为女性退出工作场域,回归家庭是其“自愿”选择的看法,北大飞在另一篇文章(《令人啼笑皆非的女性“看娃比较优势”》)里也做出了批驳。北大飞指出,田方萌的误区在于,所有的“自愿”,都是在目前的现实条件约束下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如果社会结构改变,就可能出现新的“自愿”,我们对女性的选择本身应该尊重,但这并不代表不应该审视相关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而至于女权主义者是否预设了在家带娃不如出门上班有价值,北大飞认为,不论在家带娃有多么高贵,不利于女性的社会结构都在事实上降低了全职妈妈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复出职场的选择机会——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女权主义者对现实的诚实评估。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中,田方萌攻击了保证女性参政的“配额制”。作家淡豹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支持配额制,她认为,配额制能让女性进入她们传统上被歧视或被排除在外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女性声音有机会被听到,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而田方萌则认为,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只宣传配额制的正面效应,即“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而忽视了它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对女权主义核心价值的伤害。
田方萌认为,虽然意图在于实现平等,但配额制却是一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制度,它不仅会使一些更能胜任的男性利益受损,还要面对如何对待其他弱势群体的难题。例如在印度,议会席位最初给予低种姓群体和少数族裔特殊照顾,而当女性议员推动性别配额的时候,三种标准就变得难以协调,还可能使议政能力不足的女性当选。何况,性别只是一个人复杂身份中的一种,女政治家也未必能够代表女性。女权主义者只关注群体层面的性别平等,而忽视个体差异,会导致旨在扶助弱势群体的矫正机制反过来成为精英女性的特殊上升通道。
王笑哲在文中对田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早在1995年,政治学家安妮·菲利普斯就已经在其著作《在场的政治》中解释了配额制的逻辑原理,简而言之,女权主义者并不需要去论证为什么女政治家应该享有配额制,而是配额制的反对者们需要先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政治代表结构是以男性为绝对多数的。安妮·菲利普斯认为:“正因为对现有的不公平的政治结构缺乏严谨科学的论证,配额制这一选择才自然负向成立(is thus negatively sound)。”按照这一逻辑,举证的责任并不在女权主义者一方,而在于反对配额制的一方。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暧昧共舞
在田方萌与其反对者交战正酣之时,“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编译了美国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南希·弗雷泽为《南大西洋季刊》撰写的文章,文中梳理了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几次转向及其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暧昧关系,其中涉及到的性别议题和阶级议题的复杂纠葛同样对我们理解田方萌引发的论战,以及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现状有所启发。

第二波女权主义源于1960年代的全球性解放能量:当时的青年男女走上街头,创造出新形态的抗争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横跨北美、南美,也蔓延到欧洲和所谓的“第三世界”,人们反战,反帝国主义,追求种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和参与式民主。这在波被称为“新左派”(New Left)的革命浪潮中,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它集结起不同阶级、年龄、种族、国籍和性取向的女性,成功地改变了社会途径,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人对自我的定义。
然而,弗雷泽认为,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场运动,就会发现,它必须放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来检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迸发,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在战后的逐渐式微有很大关联。
在196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形态:金融化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与之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运动,实际上呈现了两种发展方向:一方面,它揭示了一个可能借由参与式民主和社会团结来实现解放的愿景;另一方面,它接受了修正自由主义,赋予女人和男人同等的自由财产、职业选择和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等等。这就是弗雷泽所指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矛盾”,它同时象征着两种社会发展的想象。
事后看来,历史显然偏向了后者,这波女性解放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危险的结盟”。然而,这并不代表第一种社会想象从此销声匿迹,相反,当代的危机为女权主义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会,它可以再度与社会正义运动结盟,同时,女权主义如何摆脱消费、投资等市场逻辑的桎梏,也至为关键。
第二波女权主义崛起时,当时的西方国家仍享受这战后的经济红利,即通过凯恩斯主义对抗经济危机,一些国家也发展出福利国家的政策,以重建跨阶级的社会联动秩序。诚然,这样的秩序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性别、种族不平等之上的。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深感福利制度下的家长主义和中产家庭中充斥着资本主义拥戴的男性中心主义,因此试图将性别平等的议题从“社会经济资源分配”向私领域(家务劳动、性生活、生育等)延伸,但也因此被迫面对一个难题:是否应该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

最后,大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了先追求经济自主,来对抗父权对个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福利制度开始瓦解,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新自由主义给了社会平等的理想重重一击,让女权主义者们不知所措。从此,女权主义运动进入了“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时代:强调文化差异多于经济平等,重新定义性别正义。
这一路线上的转移,让女权主义者们不再专注于挑战市场经济中的性别结构,转而挑战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果有好有坏:新路线延展了原本“性别平等即阶级流动”的政治议题,却也分化了社会抗争的动能,同时,这种转移也恰好符合了个人认同结合消费主义的逻辑,正中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怀。结合田文我们可以发现,当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自由等同于“购买口红的自由”和“买房的自由”,市场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也正在以“自由选择”之名使更多女性退出竞争,回归家庭。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