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丽有穷尽,丑陋则无边,如同上帝一般。”历史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曾经这样写到。从18世纪利物浦的丑脸俱乐部到19世纪美国法律中的《丑陋法》,从2001年出现的毛绒玩具“丑娃娃”到电视剧《丑女贝蒂》风靡全美,一直以来,我们究竟是如何面对和认识丑陋的?丑陋与美丽仅仅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吗?二者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又该如何被定义?
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美国乔治敦大学讲师格雷琴·亨德森(Gretchen E. Henderson)试图通过《美妙的丑陋》一书,一探“丑”的文化史,将艾柯在《丑的历史》中所作的探讨推向更深处。格雷琴提到,“丑”这个概念由来已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从中世纪时期奇形怪状的怪兽状滴水嘴到玛丽·雪莱笔下由死尸拼凑成的怪物;从安徒生童话中的土黄色丑小鸭到纳粹主义的堕落艺术展览;从日本的‘侘寂’概念到粗野主义建筑。长久以来,丑陋挑战着我们的审美和品位,许多哲学家被其吸引又深受其扰,有关人类现状与生存互动的广阔世界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她观察到,近年来的文化借用现象将丑陋推向了一个新领域,“人们不再用消极的方式对待丑陋这个话题,而是将其自然化,甚至有些平淡化。”
值得注意的是,格雷琴不仅探索了丑的变化演进,以及“丑”与“美”这两个标签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抵触与互动,她还借由揭开“丑”的定义与对“丑”的恐惧和歧视,揭示了人类社会真正丑陋的一面——我们的社会习俗是否有失公正?我们剥夺了与自己不同的那一群人的哪些生存权利?品位的偏见应该成为剥夺他人的理由吗?“‘丑’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迫切的、强烈的、必要的提醒,”《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评价《美妙的丑陋》一书时说:“它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这本书中节选了格雷琴·亨德森的前言部分,以飨读者。
《美妙的丑陋:一个文化问题》(节选)
文 | [美]格雷琴·亨德森 译 | 白鸽

丑娃娃(Ugly doll)、《丑陋的美国人》(Ugly Americans)、《丑人儿》(Uglies)、美妙丑陋俱乐部(the Pretty Ugly Club):从现代电视到玩具,再到文学和音乐,近年来人们对丑陋这个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前不久,莎拉·克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美人,让一让,丑八怪来了》(Move Over, My Pretty, Ugly Is Here)的文章。其实“丑”这个概念由来已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从中世纪时期奇形怪状的怪兽状滴水嘴到玛丽·雪莱笔下由死尸拼凑成的怪物;从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童话中的土黄色丑小鸭到纳粹主义的堕落艺术展览;从日本的“侘寂”概念到粗野主义建筑。长久以来,丑陋挑战着我们的审美和品位,许多哲学家被其吸引又深受其扰,有关人类现状与生存互动的广阔世界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

《美妙的丑陋》(Ugliness: A Cultural History)旨在回顾“丑陋”这一概念发生变化的历史瞬间。与其将众多含义填充到一个单一而无趣的概念中,我更注重于在历史长河中发掘“丑陋”的近义词,将这个词的词源激活并充实:即“使人害怕或畏惧的”。由于许多恐惧最终都像孩子的噩梦一样,因为未知或误解而显得很危险,这次对丑陋的回顾涉及对其漫长的谱系历史的介绍以及最近对丑陋和美丽产生的“审美疑惑”。“我们无法将美丽视为无辜,”哲学家凯瑟琳·玛丽·希金斯写道,“蘑菇云的恢宏壮观伴随着道德沦丧,美丽华服和精美首饰是青少年杀人的动机。”近年来的文化借用现象将丑陋推向一个新领域,人们不再用消极的方式对待丑陋这个话题,而是将其自然化,甚至有些平淡化。丑陋这个概念从其令人畏惧的词源上继续发展,如伦敦和纽约的艺术馆宣传有关“丑陋”的展览,孩子们拥抱丑娃娃,意大利有一年一度的“丑陋节”(festa deibrutti)以庆祝丑陋,这些活动帮助我们用变化的视角看待世界,其中包括看待丑陋事物的视角,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那些让人感到恐惧和无须恐惧的事物的存在和偶然。
如果我们认同亚里士多德或阿尔贝蒂的说法,相信美丽的事物自身具有整体协调性(即一种理想的形态,自身与世界之间有清晰的界限),丑陋群体的界限相对模糊且不协调,相对夸张或处于一种毁灭的状态。畸形的、奇形怪状的、野兽般的、堕落的、不对称的、病态的、凶残的、怪异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比例的、残障的、混血杂交的:这一长串术语伴随着丑陋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时代和文化中由不同的表达方式变化而来,发展出更多变体呈现在观察者面前。 庸俗的、粗野的、腐朽的、凄惨的、无用的、杂乱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牛津英语词典》为“丑陋”一词绘制出一幅完整的谱系图,其词根来源于古诺尔斯语,在中世纪英语中发展出许多派生词汇,拼写多样,如 igly、 wgly、 vgely、ungly、vngly、oggly、oughlye、hoggyliche 等等。与这个语言学演变一样,我个人对丑陋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尤其在我梳理完关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脉络之后。
“从没听说过丑术!”《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狮鹫惊呼道:“你大概知道美术是什么意思吧?”这个问题一向有所争议。伏尔泰(Voltaire)说过:“问一只蟾蜍美丽为何物,它会参照母蟾蜍的样子回答: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两只突兀的圆眼睛。” 量化丑陋无果后,翁贝托·艾柯称:
“美丽有时很无聊。尽管不同时代对美丽的定义有所变化,但美丽的事物总是遵循一定的标准……丑陋却无可预计,带有无限可能。美丽有穷尽,丑陋则无边,如同上帝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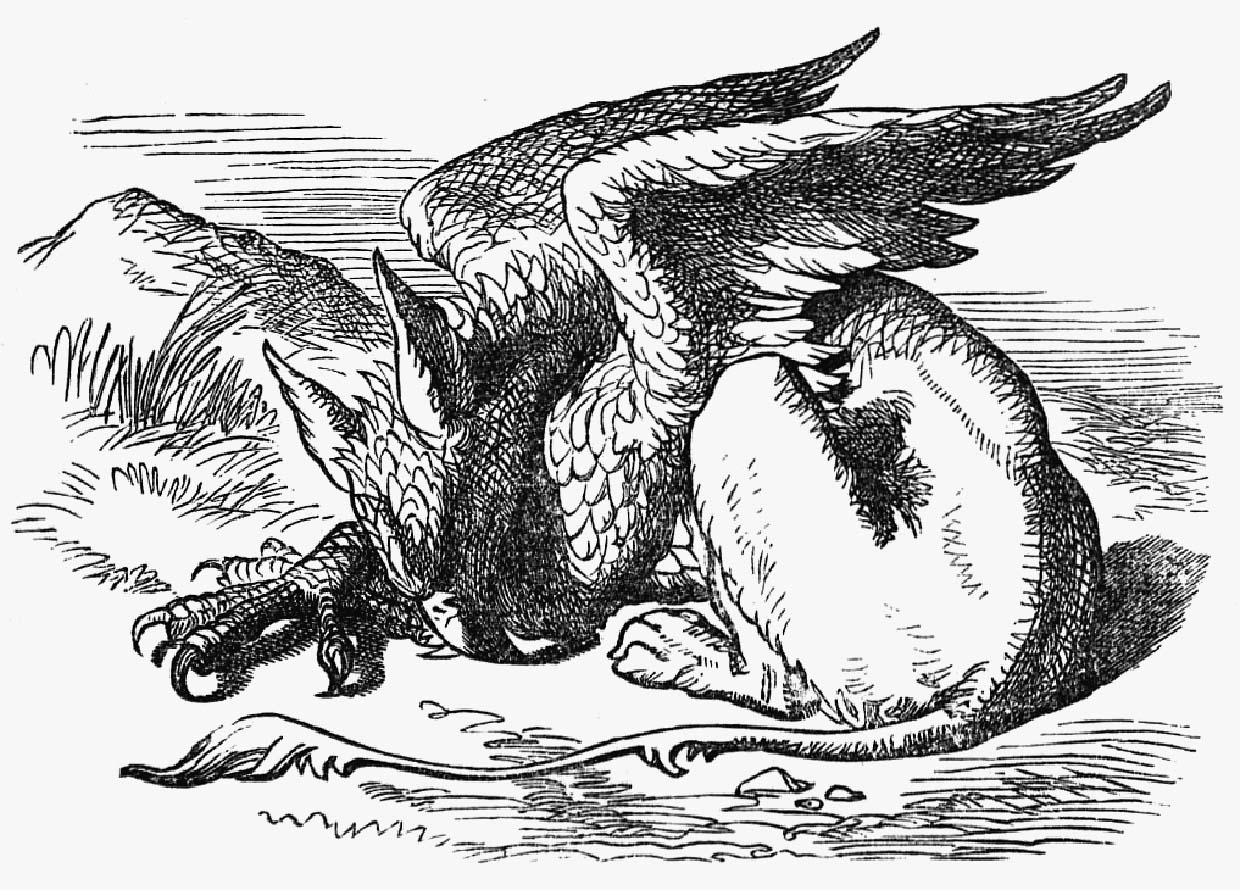
克里斯平·萨特韦尔试图在六种语言中寻找“美丽”的同义词,在英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梵语、纳瓦霍语和日语中寻找不同的概念——他将日语中的“侘寂”定义为“枯萎、沧桑、暗淡、伤痕、私密、粗糙、世俗、易逝、暂时、短暂的事物所具有的美丽”。在其他文化背景中,这些定语可能会被归为丑陋的范畴,然而在日本,它们的意义是美好的。
与其说丑陋和美丽仅仅是二元化的概念,不如说它们更像一对联星,彼此受对方引力和轨道牵制,与其他星体处于同一星座当中。通过拉近乃至模糊丑陋与美丽之间的界限,我并非想要在丑陋宇宙中的每颗星星上找到美丽的特征,反之亦然。如果这么做,这两个词都会失去各自的意义,陷入混淆的境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受不断变化的文化借用影响,在被接纳与被排斥的同时不断演变。正如建筑理论家马克·卡曾斯所言:“所有对丑陋的猜测都要经由非丑陋领域。”丑陋是美丽的对立面。除了这点互斥之外,传统的美丑对立可能会陷入一个误区,无限循环往复却无法达到“二者真正的对立”[引自艺术批评家戴夫·希基的一句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立的舒适感”。如果丑陋引起了超出舒适感和积郁的范畴之外的转变,按理说它会改变些什么。
卡尔·罗森克兰茨在《丑的美学》(Aesthetics of Ugliness,1853)中阐述道,丑陋并不仅是美丽的反面或是消极的整体,而是其自身所有的一种状态。回顾公元3世纪的罗马,普罗提诺将丑陋比为在污泥中打滚的身体,与其他有机异物混在一起。然而,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巴曼尼得斯篇》认为“哪怕是最低等的事物”,也不应被忽视,包括“污秽”。卡曾斯后来从建筑术语的角度重新审视“丑陋”,在玛丽·道格拉斯对污秽的人类学探索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将其视为“失序之物”。丑陋作为“失序”的事物,中断了我们对某事或某人的感知。它与周围事物息息相关,不断改变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空间,抗拒一成不变的形象,帮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持续变化的感知。心理反应可能催生“丑陋的感觉”,但亲身体验之后不会简单地将某物定义为“丑陋”,这样的矛盾意味着我们作为认知的主体,也许也是“失序之物”。随着“丑陋”及其相关表达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其用法千变万化,促使我们不仅考虑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二元关系,还要思考二者间的中间地带。“丑陋”在意义发生改变并突破重重约束的同时也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打破,启示我们再次审视文化边界,包括那些被接纳和被排挤的人,以此来探讨自身在这个混合整体中的位置。

我对丑陋的兴趣源于艺术史、文学和残疾这三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我在研究“畸形”这个概念时,偶然发现在18世纪的英格兰利物浦,有一个名为“丑脸俱乐部”(Ugly Face Club)的鲜为人知的兄弟会。其夸张的历史来源于“丑八怪俱乐部”(Ugly Club)这个更长远的谱系,分布于英国、美国和意大利,传承至后世。可笑的是,这个俱乐部声称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女人是畸形的男人”这个著名论调的时期。到了18世纪,“畸形”和“丑陋”两个词可以交换使用,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两个显著特征:畸形人成为笑柄和公开恶作剧的主角,同时又有许多人在众人的奚落中流落街头表演或乞讨。旧时的观念在循环往复中再次苏醒,例如“母性想象”(怀孕妇女接触丑陋的事物会影响胎儿的形态)和外貌学(丑陋的外表反映内心的本质,也被称为遗传特征)。19世纪,“丑陋”与“反常”混为一谈,不断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争议。维多利亚时期(the Victorian era),表演的商业化与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从怪胎秀到世界集会上的异族表演,还出现了解剖病理学博物馆和其他许多机构。美国法律中曾经有一条《丑陋法》(Ugly Laws)[或叫作《有碍观瞻人员法令》(Unsightly Beggar Ordinances),在19世纪80年代实施],该法律禁止身体畸形的人出入公共场所,使历史上将丑陋与畸形混为一谈的做法延续了一段时间。
在某些城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项法律仍然在法规制度中出现,直到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兴起,才对其做出反抗。纵观历史,丑陋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使这一概念复杂化且发生转变,甚至起到积极作用,冲击了既有的审美标准和社会惯例。20世纪丹麦艺术家阿斯格·尤恩提出:“一个时代没有丑陋,就不存在进步。”
丑陋是一种文化探索吗?随着时间推移,丑陋的用法混入了一些艺术人文中的相关表达和观点之后,又向我们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当亨利·马蒂斯的作品于1913年在军械库展览会展出时,《纽约时报》的一位批评家指出:“首先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丑陋、粗糙且狭隘的,其野蛮风格令人反感。”而《民族报》报道:“就算冒着重蹈覆辙的风险,我也要坚持丑陋的表象。”这些艺术评论与1937年的“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或“堕落艺术(degenerate art)”这些纳粹主义的展览有何区别呢?“堕落艺术”展中有德国最优秀的表现主义作品,这些作品被集中冠以带有轻蔑意味的标题,如“极度疯狂”,将其“疯狂与空虚的丑态”与“疯子和白痴”做类比,以此针对犹太人艺术家。由于“丑陋”及其相关词汇已经将其触角伸向不同的人群和习俗,使得有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中国有缠足之“美”,维多利亚时期有破坏骨骼的塑身衣,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东肯曾说芭蕾舞会把女人的身体变成一具“畸形的骨架”。

法国很受欢迎的概念——“美妙的丑陋”(jolie laide)可以追溯至18世纪。但是更多时候,“美妙”与“丑陋”总是站在对立面。令人震惊的是,20世纪中期美国南部的一项有名的研究显示,美籍非洲儿童觉得黑色的娃娃是“丑陋的”而白色的娃娃是“美丽的”,揭露了“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谬论,这也是最高法院在审理“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关键点。这些“丑娃娃”与汉斯·贝尔默的超现实主义球状玩偶有可比性吗?除此之外还有最近出现的丑娃娃,是由大卫·霍瓦斯和金鲜珉在2001年发明的毛绒玩具,其中包括动物形状的玩偶和书,书名叫《丑陋宇宙的丑陋指南》(Ugly Guide to the Uglyverse),宣称“丑陋是新型的美丽”。当电视剧《丑女贝蒂》风靡之时,美国广播公司发起一场类似的运动,号召人们“勇于变丑”,就像《史莱克音乐剧》的宣传语所说:丑八怪归来。这些流行文化现象是如何融入丑陋谱系学历史的?发生在这段历史中的,有人们为“一战”期间毁容的人进行整形外科手术,现代心理学对“丑陋幻想症”[1987年被正式命名为“身体畸形恐惧症”(dysmorphic disorder)]的诊断,以及现代行为艺术家奥兰(ORLAN)(在根据西方名画中的美人形象为自己进行面部整容手术后还是被人称为“丑陋”)。据估计,在2005年,美国人在整容手术上至少花费124亿美元,超过包括阿尔巴尼亚和津巴布韦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达10亿人以上。在其他众多案例中,丑陋到底该身居何处?要讲述丑陋与审美和文化影响紧密联系的故事,这些例子只是一个开头。
……
早在玛丽·道格拉斯和马克·卡曾斯在人类学和建筑学术语中将“污秽”“失序之物”和“丑陋”联系起来之前,英国作曲家查尔斯·休伯特·H. 帕里就已利用这几点在音乐中渲染丑陋的美学价值。在其他支持者中,艺术评论家罗杰·弗里在视觉艺术中对丑陋大为称赞, 20世纪的许多艺术家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我们该如何协调越来越多的审美变化与更加负面的社会内涵之间的冲突?文化与美学的旋涡是否会将丑陋席卷而入,利用革新的力量脱离老旧的想法?对“丑陋”的认知是否给 “中和的舒适”(Neutral comfort)这一陈腐概念造成潜在威胁,以此来支持多元化理念?当下文化中被认为是“丑陋”的元素在未来是否会有改观?丑陋像隐形的致命病毒一样散播,还是在帮助人类适时重新调整主体和客体的位置,提醒我们在这大千世界中的独立性?本质上来讲,人性是由丑陋维持的吗?我希望后续的内容可以让大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对丑陋形成一个广泛的认识,同时保持一定的概念化,以跳出单一的文化和历史限制——以及我个人想象力的局限。丑陋从不归顺于单一的定义,如果更多人能感受透过丑陋这个不明确又受争议的表面,发现文化上也有一些共通之处,这样丑陋可能就会被重新构建。
书摘部分及插图节选自《美妙的丑陋》一书前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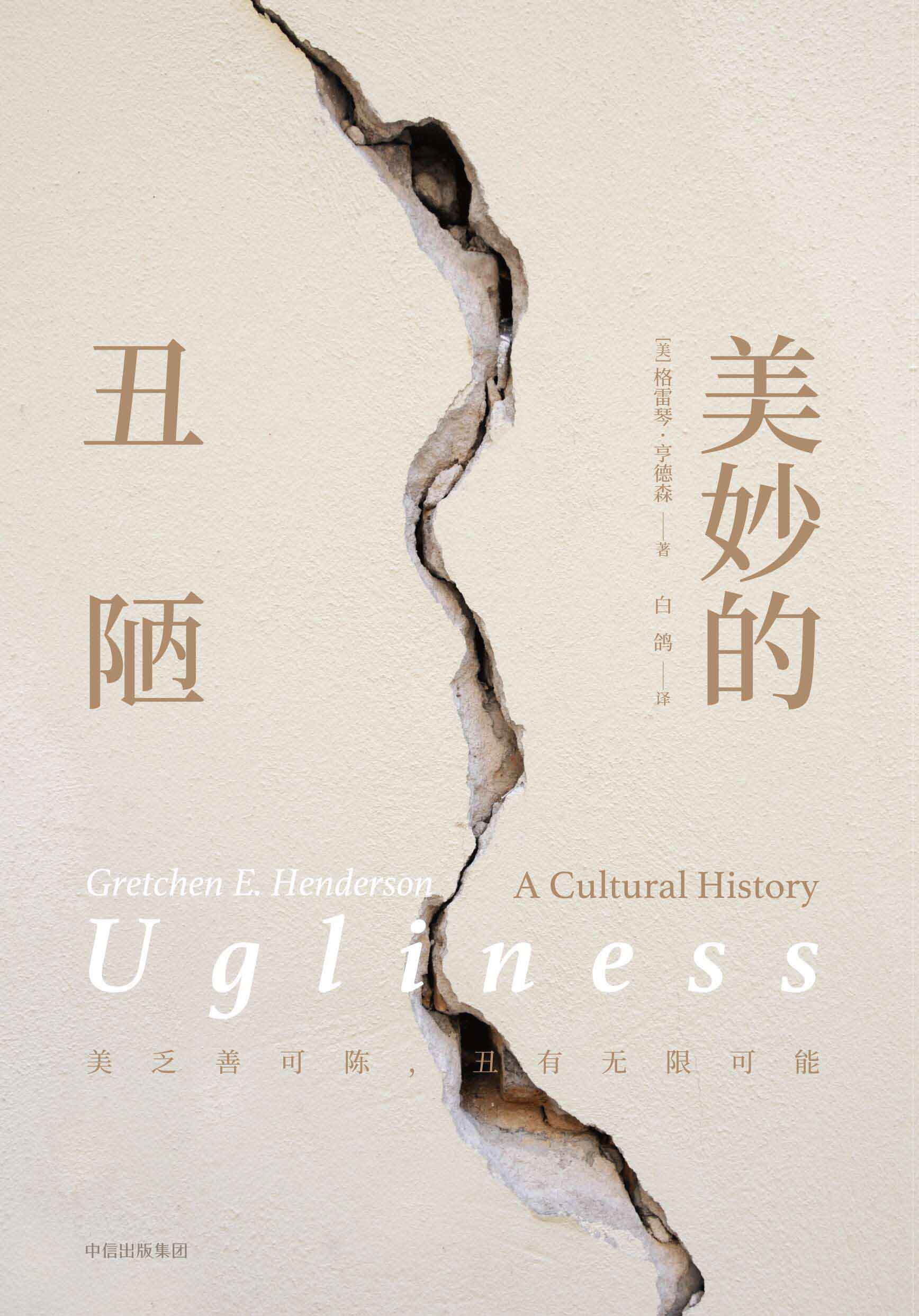
[美]格雷琴·亨德森 著 白鸽 译
楚尘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