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马原带着只有一位摄像师的摄制组,走访了一百多位作家,回顾他们的八十年代,采访对象包括孙甘露、王安忆、格非、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等人。这一行留下了时长共计120小时的影像资料,文字出版成书名叫《中国作家梦》。然而,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购买视频版权,图书印数也很低,影响很小。此书在新世纪再版时,更名为《重返黄金时代》,明确地将八十年代的文学定义成了“黄金时代”。
这本书虽然仍旧没有什么影响,但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的说法还是引起了文坛亲历者的共鸣。冯骥才去年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激流中》,他写道,“他(马原)竟然用‘黄金时代’来评价那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只有俄罗斯把他们的十九世纪称为‘黄金时代’。”冯骥才说,“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八十年代果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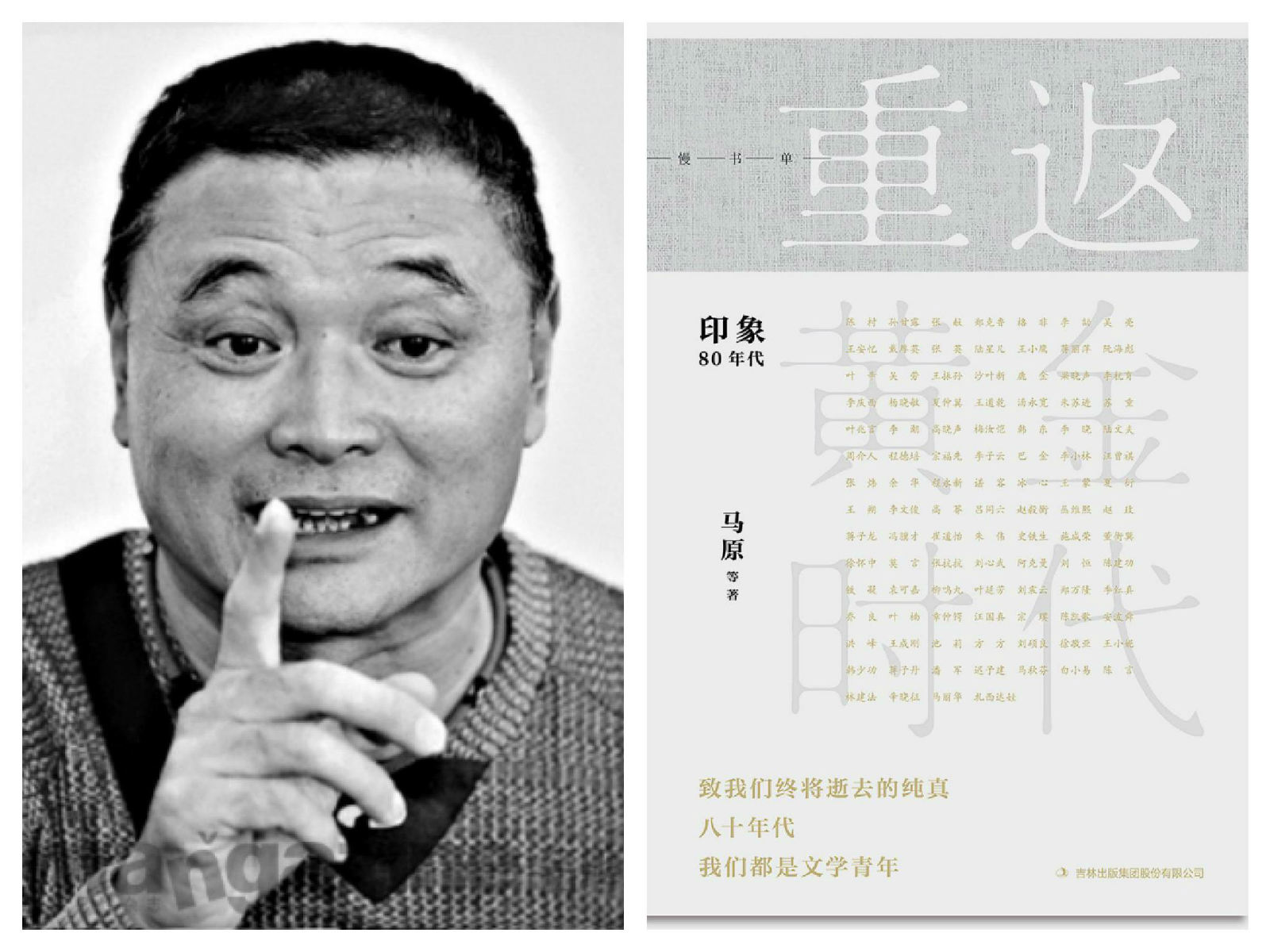
《重读八十年代》一书日前出版,作者朱伟从文学编辑的视角出发,回忆和还原了他当年骑着自行车一家家上门约稿的情形,并重现了当年的作家们彼此交往与写作发表的经过:当年的莫言,刚刚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正在创作“红高粱”系列;那时的余华,从第一篇作品《星星》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
在这些单个的成名成家的叙述之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重读八十年代》对彼时文学圈子与笔会的记述。圈子通常有固定的成员,在李陀家中,就是陈建构、郑万隆、冯骥才等人,他们经常见面,吃饭聊天,亲密无间,也能从聊天中迸发出灵感。而笔会是更大范围的、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发动纠集起来的“官方”相聚,为了出作品评奖项,青年作家们朝夕相伴、同吃同住,讨论起文学来,或者同声应气,或者面红耳赤。
圈子
在《激流中》一文中,冯骥才忆起了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经常去的地方,那是北京朝外东大桥一栋楼的十二层——李陀的家。比冯骥才更早去的是陈建功与郑万隆,李陀与这二人在“文革”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年代,陈建功凭借“京味小说”出名,郑万隆则以“寻根小说”闻名,后来因担任电视剧《渴望》的编剧而为更多人所熟知。这四人观点相近、关系要好,形成了一个“小四人帮”。冯骥才说,与李陀要好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前卫精神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二是他对文学有责任感,也是正因为这两点,李陀才会成为现代文学的“推动者”和“布道者”。

对于李陀的文坛位置,朱伟是这么评价的:李陀,人称“陀爷”,是牵连文坛四面八方的人物,不光作家找他,外地来京约稿的编辑和评论家也找他,而他的家,也就成了一个“文学交流所”。八十年代中后期,李陀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先后推出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苏童的《桑园留念》。

李陀的家是凌乱的,被子常常不叠,书堆得乱七八糟,却经常聚集着来自各处的青年人物。有一次,冯骥才在李陀家见到了一个“清瘦男子”,“脖子很细,戴一副圆眼镜,”这人正是已经凭借《棋王》轰动文坛的阿城。当时他正在跟众人讲述云南马帮的“溜索”,故事讲到马被绑在山谷之间的绳索上吓得屁滚尿流的场景,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阿城讲的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小说《溜索》。在李陀的家里,圈子聊天可以变成小说,无名之人可以一鸣惊人,冯骥才将之称为“民间作协”。
作为“民间作协”,李陀家孕育着文学从圈子聊天向公共领域发展的生机,这不仅仅是冯骥才的观察,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一书里也为“民间作协”的存在作了证。朱伟写道,“在我的感觉中,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子’里开始的。”就像《溜索》源自于聚会聊天一样,朱伟提到,阿城的名篇《棋王》也是在李陀家和陈建功、郑万隆吃涮羊肉时吃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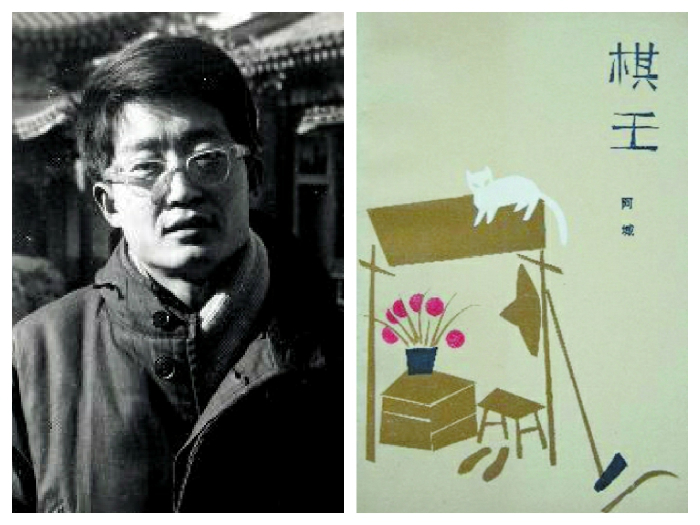
在《1985》一文中,李陀本人是这么回忆那次颇具文学史意义的涮羊肉的:“屋子小,桌子也小,大家只能紧紧地围桌而坐,手和脚乱打架,很是不便,但是桌子正中那个闪闪发亮、冒着热气、把羊肉香和燃烧中的木炭香混在一起去勾人的大黄铜火锅,使人兴高采烈……”当时的阿城虽是“星星画派”的成员,但已凭讲故事出名。他当年在云南插队,就靠着给老插队的讲故事混些吃的,所讲的故事段子里竟然还有经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当天的涮羊肉吃了一个小时,阿城才开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慢悠悠地讲起一个“下棋的故事”。故事讲得精彩,李陀等人便催促阿城把故事写成小说,后来,这篇小说经陈建功、郑万隆推荐发表在了《上海文学》上,这便是被视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棋王》。
八十年代文人之间的“圈子”怎么来的?李陀在《1985》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小圈子”文学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对“集体主义”存疑,却仍将写作视作“集体事业”,所以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李陀写道,不光北京有“圈子”,成都也有,诗人张枣就向他讲述过,一个人写好一首诗,坐火车赶到朋友家中,激烈讨论彻夜未眠的桥段。
1985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文坛同时迸发出了“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小说”两束光芒,诞生了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同样认可1985年的转折点意义,可是,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转折,亲历者们怀有不同看法。
冯骥才说,“1985年,真正的中国文学的头长出了一对漂亮的耳朵,一个是实验小说,一个是文化小说。”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实验小说和文化小说共同推动了转折。朱伟认为,韩少功那一年发表的《爸爸爸》《蓝盖子》和《归去来》构成了1985年的文学转折。而曾在“圈子”中心的李陀,则将文学转折与小圈子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因为小圈子持续不断地发酵,文学革命才发生了。他写道:“我敢说在在1980-1984年那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不在。它们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卷起一场空间的文学风暴”。
友谊
李陀认为1985年文学转折源于小圈子,毫无疑问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当时,除了常来常往的郑万隆和陈建功,李陀家中还聚集着许多人物,其中一位就是作家马原。在查建英与李陀的访谈中,李陀说起过与马原的初遇:那是1984年的秋天,北京已经很凉了,他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高个子的小伙,上身只穿一个背心,下身是一个短裤,“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这个人就是马原,约好跟他来谈他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1985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刚坐下来,马原就以不容驳斥的口吻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不同意,马原仍是以不容驳斥的口吻批评李陀,“你根本不懂小说!”

作家之间不光有毫不留情的争论,还有亲密无间的“协助”。李陀回忆说,有一次,张承志十二点敲开李家的门,就为了找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来帮助他的《金牧场》写作。李陀穿上衣服帮张承志找到了书,还坐在一起聊了聊《马丁·伊登》的写作调子。在李陀看来,“那时候,人们没有什么privacy(私人空间)的概念,这恰恰是‘公共空间’形成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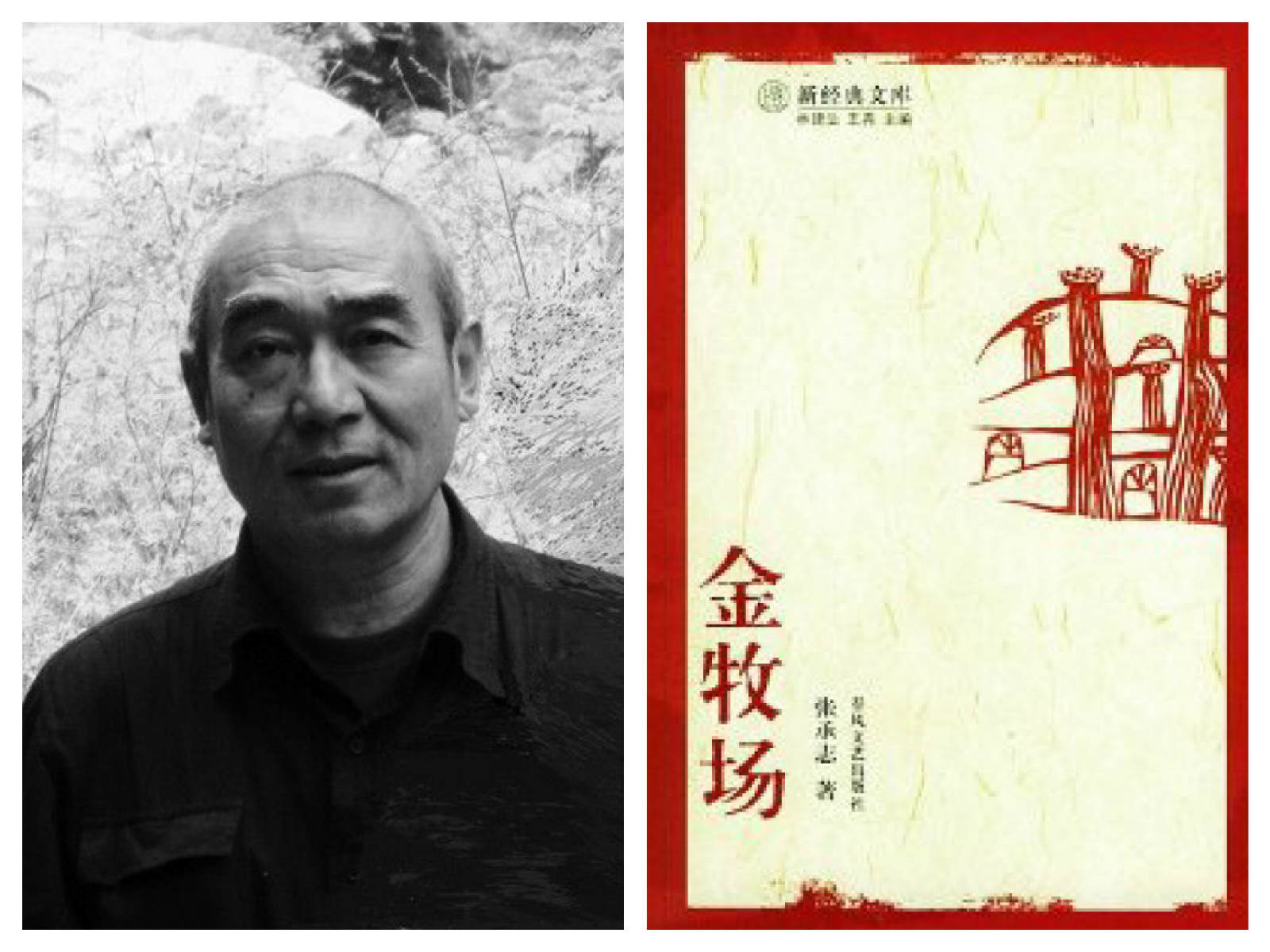
李陀所举的例子十分适合拿来印证八十年代作家之间的亲切情谊,而这份友谊,他觉得,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渐渐淡掉了。“现在我们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像80年代那样: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是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发现,“你说谁的作品写得不好,有毛病,那个脸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这些话不是很方便说了。”
朱伟也十分怀念八十年代没什么“privacy”可言的情谊,他写道,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很近,骑着自行车,不用打招呼,说到就到。在李陀家这个“中心”以外,朱伟还标识出了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地图的其他“散点”。这些“散点”不光是地理上的坐标,还是情感上的联结点。他这样写道:“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李陀坐两站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小圈子”和亲密友谊并不专属于八十年代。早在1948年,穆旦在上海霞飞坊巴金家里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时的巴金和萧珊家也是“很不讲究”,“又黑又烟熏”,但因为常有同学朋友往来,包括一帮西南联大的“小字辈”如汪曾祺、黄裳、王道乾等人,便常常热闹非凡。穆旦还记得自己在巷口买油炸臭豆腐,带回去大家一起吃。在二十几年后,穆旦也怀念起了那时的情谊来,“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同样在场的黄裳在后来悼念巴金时,也讲到了这一段“沙龙”年代,并引用靳以的话,将这一群环绕着女主人萧珊的人形容为“卫星”。可以说,穆旦和黄裳怀念他们的“卫星”时代,与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之后李陀、朱伟怀念起八十年代的友谊,本质上是相通的。
笔会
在“小圈子”密会之外,八十年代,笔会与创作班也是培养作家的一种方式。朱伟在书中提到,那时各地的作协和刊物都曾通过办笔会来培养作家。1982年,朱伟所在的《中国青年》为“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在桂林办班,邀请了上海的陈村,还有江苏的赵本夫、徐乃建,有些人却没有到——韩少功到了创作班结束才抽出身来相聚,陈建功也因为工作分不开身。
朱伟认为,笔会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作家们日夜厮混、谈天说地,听起来更像一个“人为催熟”的“圈子”。此外,笔会还赋予了作家在当地体验风物的机会,朱伟回忆道,借着当年的“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笔会,这一群年轻作家也有了许多相处的机会——他们沿着榕杉湖散步,去南溪山、象鼻山看石刻,坐在靖王府的古城下、大榕树下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一年,“五四青年文学奖”的“笔会”环境还没有那么优雅,只是简单设于《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宿舍楼里,朱伟把李陀和陈建功拉过来关门写稿,为的是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午,他们三个一起“用调羹敲着饭盒到食堂买饭”。
桂林笔会的众人如同一幅青年作家群像,朱伟写道,有的作家已经在关注存在主义,随身携带者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有的作家热爱深夜交流写作,陈村是最不纠结、最不费劲的一个,他还申请要体验生活,“去手术室看医生做手术。”那时朱伟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出建议,逼出最好的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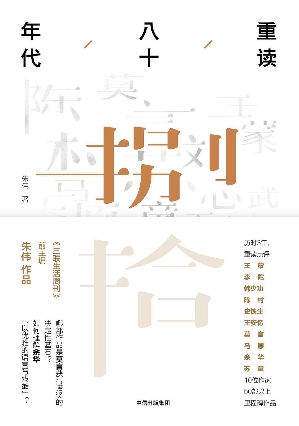
朱伟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5月
笔会是要出作品的。二十多天过去了,陈村一开始交的小说被朱伟毙掉,后来又在“逼迫”下交出了《花狗子嘎利》。陈村后来对朱伟诉苦说,“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后来再不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不上当了。”陈村交上来的是一篇知青小说,却被认为“基调太灰暗了”;朱伟只得说服陈村修改标题、增加议论,把“灰暗的调子”扭转回来,才最终获了奖。 可见,在笔会之中,不仅作者与作者之间可以彼此熟识,作者与编辑这种建立在监工与被监工基础上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此外,会议也是联谊方式的一种。在李陀的回忆中,一次官方会议,不光有官方会场,还有回到房间以后的“会中会”和“会下会”,而这些借着官方会议机会开展的“会下会”,对他们来说才是会议重头。他写道,人们会凭借着平时的友谊在此找到自己的“圈子”——比如他会要求和陈建功、郑万隆住一个房间,他们之间的讨论和会场上的内容完全不同。作家徐小斌也曾写到过《十月》杂志组织的一次“会下会”。会议结束时,一个身着军装的男孩主动过来找她,这男孩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带点儿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说话)连珠炮似的”,还有点儿“人来疯”,这个人就是王朔。他们从会议结束一直聊到宿舍间,从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最后彼此留了地址和电话。
“在那些会上发表意见自然受限制,不过谁也不在意,因为散会之后回到房间,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开始,常常彻夜不眠,”李陀一边强调着“会下会”与官方会议的区别,一边延伸了那些年那些小会的意义,“要是没有这个空间,不要说 ‘新启蒙 ’,就是主要由官方推动的 ‘思想解放 ’,大约都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产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