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非虚构的写作中,梅丽莎·哈里森(Melissa Harrison)都被一种深刻的感觉推动向前,这种感觉包括大自然的重要性、四季的轮转,以及人们身处其间的环境的运作。《黏土》(Clay)是她的首部作品,讲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城市野生物种中寻找慰藉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山楂树时代》(At Hawthorn Time)曾入围科斯塔图书奖(Costa novel award),同样描绘了不同类型的主人公,而这一次故事的发生地变成了当代乡村,在居于其间的复杂又彼此冲突的人们之外,她还想写一些别的东西。
她最近的一部作品《大麦中的一切》(All Among the Barley)继续着与自然世界深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1930年代初成长在萨福克(Suffolk)农场的青少年伊迪的故事,涉及民族主义与怀旧,行文极具富有哈里森特色的精确散文风格。哈里森在萨里郡(Surrey)长大,现居萨福克和伦敦,在《Mixmag》做兼职产品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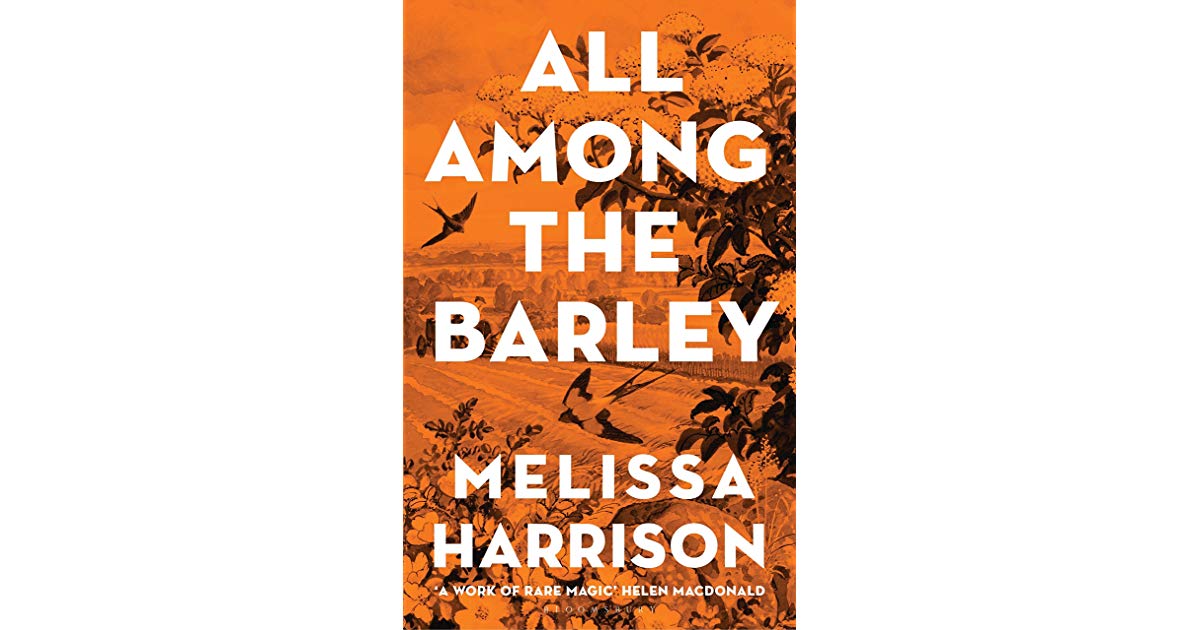
《卫报》:你为什么决定要写193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
梅丽莎·哈里森: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30年代会变成如此热门的话题,因为脱欧的全民投票那时才初现端倪,我还天真地假设我们会留下来呢,而特朗普能胜选这种想法在当时简直是荒谬可笑的。我开始写作1930年代,是因为我想写从马匹到拖拉机的转变。我还想写,在那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和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卫报》:这是一部既切中要害,又与今天的英国相去甚远的小说。
梅丽莎·哈里森:我感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夹着一个非常脆弱的世界,我的直觉是,它曾经存在过很长时间,但随后又迅速地消逝了。在我看来,这与一个强大的、吸引人的英国风格有关,但它同时也很危险,因为它满载着怀旧情绪。很多人都在讨论“正统英格兰”这个观念,我也问过我自己,随后我意识到这个观念既危险又排外。我想探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二战前时代(译注:pre-Windrush age。由于1948-1971年间由英属加勒比海各国乘船到达本土的一代移民所乘坐船只的名字,这群人被叫做“Windrush”一代,在此之前即是二战前时代)的怀旧情绪。

《卫报》:你在书中有创造法西斯运动吗?
梅丽莎·哈里森:对,我有,尽管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法西斯组织的历史原型在全英格兰活动。他们中有一些真的很高效;另外一些则仅仅是景观化的神秘论者,他们想要重回昨日辉煌;还有的则凶残至极。小说有个地方比较有趣,里面揭示了一些法西斯主义运作的原理,但它们不是基于连贯的信仰体系,而是寄生于其他诸如思考、恐惧等形式中。它就像真菌一样,你稍不注意,就左右疯长。
《卫报》:在这本书中,就像你之前的其他作品那样,充满了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信息。你是如何决定在作品中收纳多少细节的呢?
梅丽莎·哈里森:我一直都很担心写自然事物写得太多。有的读者会直接跳过那些段落,我对这点有足够的意识。但那些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当我散步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看看周围景物,然后拍拍照。重点不是非要散步到终点,而是我沿路看到了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也是同样的。你得根据你自己对世界的激情和经验来写作。我没办法为市场写作——那样子写出来的东西不真。

《卫报》:你搬到了萨福克,这本书的写作在其中有起什么作用吗?
梅丽莎·哈里森:是的。我是十二月搬的家,那时候这本书正好快写完了。在萨福克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那里没有家人,那是一个与我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如果我不是为了研究写这本书而花了时间,我也不会朝那个方向走。
《卫报》:你对社交媒体感觉如何呢?
梅丽莎·哈里森:我喜欢推特。有的时候确实会失去平衡,在那种时刻,我感觉我把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脑子里写成了一条推文。也正是在那些时刻,我知道应该往回退一步了。这就像一个操场。我不喜欢被怨恨和争论缠住,因为我知道这等于是在喂养一头愤怒机器,我不想参与其中,但是我很享受那些与陌生人用文字起舞的欢乐。
《卫报》:你旁边桌子上的那本书是什么?
梅丽莎·哈里森:帕拉希·奥唐奈(Paraic O’Donnell)新书《晚霞沙上的房子》(The House on Vesper Sands)的试印拷贝,以及王海洋(Ocean Vuong)《伤口隐退的夜空》(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
《卫报》:你还欣赏哪些作家?
梅丽莎·哈里森:不管以什么形式讲,艾丽丝·奥斯瓦尔德(Alice Oswald)都是我们尚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
《卫报》:你都如何组织自己的书架?
梅丽莎·哈里森:我几乎还没做呢。我刚刚搬了家,不——我根本搞不定。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一片粗糙之地中自然写作,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卫报》:你会给孩子们推荐什么书呢?
梅丽莎·哈里森:布莱恩·卡特(Brian Carter)的《黑狐狸奔跑》(A Black Fox Running)。
《卫报》:你收礼物收到过最好的一本书是什么?
梅丽莎·哈里森:是“瓢虫”系列的一本,《春天应该找什么》(What to Look for in Spring),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把这个系列的四本都集齐了,但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在曼彻斯特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发现在那个简陋的学生宿舍里也有一本那个书,它掀起的汹涌回忆几乎要把我击倒。我跟我朋友艾利克斯兴奋地讲起那本书来,她就说,我可以拿走它。我把它带回了家里,买了系列中的其他几本,它们真的将我对季节以及一年轮转的兴趣重新点燃了。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但我住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把它们全部抛诸脑后了。这应该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它成为了我与自然世界重新连接的一环。
《卫报》:纯为消遣的话,你都读些什么书呢?
梅丽莎·哈里森:美国小说家的作品,比如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
(翻译:马元西)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