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球握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感受着网球的皮质表面。球在地面上弹击,一下、两下、三下,右手转拍。”球网的另一面,站着正等待他发球的对手。这个嘟囔了几句意大利语的男人眼神忧郁,有红色的胡子和分外显眼的鼻子。这是一场“跛子”和“娘娘腔”之间的对决。
即将发球的“跛子”是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诗人克维多。他生于官吏家庭,曾任外交官、国王秘书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也用笔名写作,讽刺宫廷腐败,揭露社会黑暗。他著有讽刺文集、流浪汉小说、诗集还有神学和哲学论著。球场另一边那位被克维多嘲讽为“娘娘腔”的意大利人,则是十七世纪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马耳他和西西里的画家卡拉瓦乔。与克维多的保守、在体制内亨通的官运不同,卡拉瓦乔一生动荡、危险、神秘,在失控的边缘游走。他好争斗,杀过人,这些都无法掩盖他的艺术才能。他依靠物理意义上的精确观察以及明暗对照法,开创了自然主义的新风格,也启发了现代绘画。而卡拉瓦乔身上最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他是一个狂热的网球爱好者。
墨西哥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在小说《突然死亡》中,虚构了西班牙诗人克维多和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之间的一场网球赛。随着那颗网球一来一回,在球场上来回弹跳、滚动、被球网拦下又或者是越出边界,一段十七世纪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教皇,在不久之后对新教徒发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而在英国,稍早之前,亨利八世处决了王后安妮·博林。在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摧毁了阿兹特克古文明,建立起了西班牙殖民地。多年后,埃尔南的外孙女嫁给奥苏纳公爵,后者为逃避通奸惩罚,携诗人克维多逃往意大利。在那个不同文明开始逐步交融、沟通、碰撞的年代,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的交锋轮番上演。

[墨]阿尔瓦罗·恩里克 著 郑楠 译
中信·大方 2018年7月
虽然关注点落在十七世纪欧洲和美洲的历史进程上,但恩里克声称,这部小说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实际上是关于当下的。他试图以十七世纪为切入点,探讨当下墨西哥所遭遇的暴力问题,以及如今欧洲各国之间藩篱再度竖起、民粹主义抬头的状况。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同时发生的世界”,过去持续对当下施加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过去的奴隶,”恩里克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这样说道。
一方面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回溯历史、寻找当下种种现象的根源,这是恩里克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在写于1996年的小说《一名装置艺术家的突然死亡》中,他还原了1990年代墨西哥刚刚融入世界体系时一群艺术家的故事。1994年是墨西哥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那一年,墨西哥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突然向世界开放。他回忆道,“一夜之间,电视上充斥着美国电视节目,大街上也随处可见美国进口的轿车。这一切都有点吓人。”当书中描写的这群艺术家突然被抛入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艺术世界,他们做出了一些看似荒诞不经、与国际艺术环境完全错位的选择。恩里克对于文化冲击、碰撞的持续关注,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密不可分。在他成长起来的1970年代,墨西哥仍然十分封闭,直到1979年,他才第一次接触到了英文版的《国家地理》杂志,“当我开始学习英语之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即便怀抱对于现实的高度关切,恩里克却拒绝使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我无法阅读任何一本和墨西哥毒枭或者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相关的小说,它们经常让我感到无聊。”他所信奉和秉持的小说创作有一种装置艺术的意味,写一本小说仿佛创作一件艺术品,而艺术品创作的步骤和过程有着某种不可估量的重要性——这是他从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身上学到的一点。“我希望读者打开我的小说,像打开一个冰箱,里面有不同的隔层,读者各取所需,然后自行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概念,来重新排列组合这部小说。”

“一本像苹果手机一样运作的小说”
界面文化:我十分感兴趣《突然死亡》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很明显这并非一本传统的小说,它更像一个实验,或者是一件装置作品。所以你最初是对网球感兴趣,还是先有了关于历史上不同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碰撞然后找到了网球作为依托?
阿尔瓦罗·恩里克(以下简称恩里克):我对网球没有任何兴趣,我从来没看过网球比赛。我对十七世纪感兴趣,而网球和十七世纪的关系就像英式足球和二十世纪的关系一样,它在当时是一种让人为之疯狂的运动。另一方面,我已经研读与卡拉瓦乔相关的资料很多年了,我并非要写一本关于卡拉瓦乔的书,而是要借助卡拉瓦乔写一本书,卡拉瓦乔在这本书中就像一个中介工具一样。
在关于卡拉瓦乔的海量书籍和资料当中,有一本传记,也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于卡拉瓦乔的书籍之一。去罗马的时候我第二次读这本传记,并遵循传记去寻找一些和卡拉瓦乔相关的线索。这一次,我发现了一些在第一次阅读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卡拉瓦乔成为一个画家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网球运动员。读到这里,我心想,就是它了!并非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刺客又或者是同性恋者的卡拉瓦乔——这些都是他为人熟知的一些身份,而是一个极其微弱的、边缘的、容易被忽视的身份,作为网球运动员的卡拉瓦乔。
界面文化:那你是怎么想到让卡拉瓦乔和西班牙诗人克维多打比赛的?
恩里克:他们俩都是我的偶像,都有强烈的道德人格。卡拉瓦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有流动的性倾向,以一种十分诗意的方式与国家进行对抗。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充满了创新精神,他像一只黑色的蛋,他爆炸,然后真正改变世界。我们如今对于艺术的很多认知都来自卡拉瓦乔,他是当代艺术的导师。
而克维多则恰恰相反,他是个紧绷的人物,一个为帝国服务的人,一个贵族人物。克维多用笔名写作诗歌,他发表揭露丑陋的长诗,讲述帝国主义的伤痛,如今看来这些多是无人问津的糟糕作品,但是穷其一生他都在匿名创作这样的诗歌。他也创作色情诗歌,并因此进了监狱。事实上,他写作最强有力的色情诗歌,还有一本《梦之书》,我认为这本书为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因此克维多这个人物颇具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但同时他也具备强劲有力的黑暗面,这让他成为一个现代人物。
卡拉瓦乔和克维多两个人的对抗,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两种方式和路径之间的对抗。卡拉瓦乔代表着我们的现代性,克维多则代表着另类现代性——是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更加保守的一种现代性。

界面文化:那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本书是关于这两个人的?
恩里克:不,这本书是一本物件之书。书中充斥着非常多历史名人,有卡拉瓦乔,有克维多,有伽利略,有英格兰王后安妮·博林,还有很多传奇的主教。但这本书并不是关于这些人物的,这些名字无法阐明这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物件的历史。一个物件是用博林的头发制成的网球,这是一个缓慢地滚进画面的物件;另一个物件则是织羽艺术——这两个物件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小说中有两个主角,而没有一个是人物,人物仅仅是物件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有人会说这是一本后现代小说,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标签。
界面文化:但在你的阅读体验中,你确实受到了很多后现代文学的影响?
恩里克:对。在1970年代末期,英文刊物和作品开始涌入墨西哥,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在阅读英文杂志和英语文学作品。在我成为作家的那段关键时期,我阅读了很多英美文学,尤其是后现代作品。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对我而言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除此之外,唐·德里罗、朱利安·巴恩斯对我影响也很大。我觉得如果不是得益于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本书是很难构思成型的。我们经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品钦就是巨人之一。
不过,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这本书的成形过程,它应该是一本像苹果手机一样运作的小说,你可以通过排列和改变各种元素的顺序让它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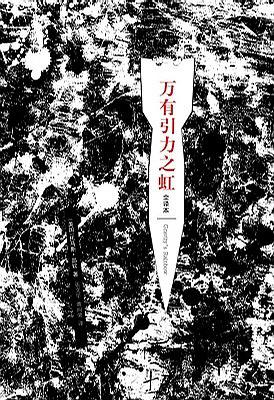
[美]托马斯·品钦 著 张文宇 黄向荣 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
界面文化:所以这本小说更像一件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关于空间的而非平面的?
恩里克:的确是,这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希望读者打开我的小说,像打开一个冰箱,里面有不同的隔层,读者各取所需,然后自行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概念来重新排列组合这部小说。因此是的,它更像一本与空间相关的小说,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这样的。
界面文化:你的作品真的很像当代艺术。
恩里克:是的。卡拉瓦乔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是艺术步骤的大师。对于卡拉瓦乔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艺术作品时候的步骤,他利用自己的朋友来组织表演。他把他的朋友们安排在一间黑暗的、墙上仅有一个小孔的屋子里,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上演《圣经》中的场景,他把这个场景投射到帆布上,并在此基础上作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拉瓦乔是个骗子,因为他的画作很多都是这样产生的。他复制这些场景,然后制成油画,卖给主教,这就是十七世纪以来艺术运作的机制。
“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历史的奴隶”
界面文化:你之前还有一本小说《一位装置艺术家的突然死亡》,是一群1990年代面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两本书有某种内在的延续性,比如它们共享一些相似的主题,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和碰撞、关于墨西哥的历史等等。
恩里克:对,我对这些话题的关注和我出生的年代有关。我出生的时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所经历的墨西哥全球化的过程是暴烈的、野蛮的。我们赤身孤胆,在全球化时代赤手空拳地打拼自己的位置,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和一个突然间如此巨大的世界舞台共处。因此,我对于十七世纪墨西哥所经历的剧烈动荡的兴趣,或许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剧烈变动有关。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个国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像卡拉瓦乔、克维多这样的网球选手和年轻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可能就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面对国家巨变时的状况类似。

[墨]阿尔瓦罗·恩里克 著
Mexico City: Joaquín Mortiz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你们这一代有着类似成长背景的墨西哥作家在写作上有某种共性,或者共享一些共同关注的写作命题?
恩里克: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我从来没归属过任何一个群体。我的学术生活大部分是在墨西哥以外度过的,但我父母还在墨西哥,所以我经常回墨西哥,也在那里居住了两三年。但我不认为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什么相似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我的同代人十分关心他们所经历过的墨西哥政治问题,而我选择把目光拉远,通过挖掘历史来映照当下。
界面文化:那是否可以说,你写作的路径和方法是十分与众不同的,因为你试图通过对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分析和理解,来触及墨西哥当代的暴力和政治问题?
恩里克:我并不是一个艺术的狂热爱好者,我关注艺术,正如我也关注文学和音乐一样,这是我想要身处其中的世界。但我觉得“与众不同”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形容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到与众不同;当我们长大,我们就知道独特性其实并不存在。
我当然也担心,我写出来的东西会让自己感到无聊。我很容易感到无聊,我无法阅读任何一部关于墨西哥毒枭的小说,那对我来说很无聊,因为我完全可以从报纸上获取那些故事。同样我对描写美国纽约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说也毫无兴趣,如果我想了解这样的生活,我只需要到纽约的街头去看一看,为什么我要读一本与此有关的小说呢?
因为我努力触及那些让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主题:我们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应该怎么做?我们在这样一个国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的年代、一个逐渐欧洲内部逐渐建起藩篱的年代,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些是我关心的事情,也是这本小说所关心的事情。我的这种写作区别于新闻写作,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漂亮但奇怪。如果你想表达A=A,那么你是一个记者;而我想说的是A=Z,这就是我在这本小说中所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同时发生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回溯历史的写作是否也是问了回应现实问题?
恩里克:确实是。这本书绝非一本历史小说,也不想成为一本历史小说。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会在书中直接出现,他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我要书写这个。这是一本有关过去的小说,或者说是利用过去,就像一个文化会利用铁和铜等材料,但这是一本谈论当代世界的小说。这本书讲述了国际化时代的道德问题,你可以利用它来谈论贪婪的华尔街商人,也可以用它来谈论美国的帝国主义,又或者是西班牙帝国的崛起。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过去持续对当下施加影响?
恩里克:是的,过去附着于我们身上。有传统,有不可遗忘的历史,有时刻提醒着我们过去历史的博物馆……我们持续地回到过去。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那是四年前了,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并非同一个人。但我仍然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历史的奴隶。
“我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感到愤怒和厌倦”
界面文化:《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说,你的小说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你在书中也强调,这本书“并非意在解释美洲大陆是如何缓慢而神秘地被并入所谓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这个错误概念令人愤恨,因为从我们美洲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明明位于东方”。
恩里克:我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感到厌倦。很多年前,美国就已经不被称为欧洲的殖民地了,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讲述那种关于欧洲的充满谎言的历史。欧洲确实很富有也很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存在的历史比欧洲悠久,为何我们还要一直跟随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和历史书,描述一种文化从以色列传到地中海再到西班牙再到美洲的过程?事实并非如此,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追随这种单调的论调?
我认为,当下这种欧洲中心论应该被扭转,视角应该发生转向,如果更多地从非欧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遭遇,欧洲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最新的一些研究也都显示,欧洲对于美洲的征服其实并非十分明确清晰的。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没有赢得那场战争,而是说他们对于美洲人的统治并非立刻发生的,而是由一系列连续的事件构成的。因此,如果我在小说中挑战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纯粹是因为这种观点让我愤怒。
界面文化:书中有很多色情描写,而你在书中也强调,“小说让一切伟大的人与物分崩离析:因为所有小说,包括最纯洁的那种,都稍许色情。”为什么会这么说?
恩里克:我用的是色情(pornographic),而不是情色(erotic)。其实,我认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更多地揭示了个人写作行为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这是超乎写作者本人预期的。语言通常被政府、被公司使用,来确保和确认某些事情。但当一个人使用一种语言进行文学写作时,语言被操演的那种本质,语言那种特定的使用方式、句法、语境和语法等等,就揭示了一种文化的方方面面,仿佛所有东西都是裸露的。你从事写作的语境以及你所在的文化通过你的语言、通过你使用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形容词的方式、你连接一个句子中不同部分的方式展露无遗。因此,这个过程是十分色情的。不论你多么渴望通过语言掩盖自己的文化渊源,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总是在向他人展示自己是谁。如果你阅读莎士比亚,你看到的全是赤裸的灵魂。当然裸露的不是语言塑造的角色,而是根植于不同文化的使用语言的方式。艺术从来都应该是关于展示的,而非关于隐藏。我觉得小说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读小说的原因,一切都是敞开的,是暴露给读者的,在小说中我们无法隐藏自身。

界面文化:那么你是否认为翻译会损害这种小说的色情性,鉴于你的作品是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的?
恩里克:我相信翻译。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所有的翻译都是原创的,我认同这种看法。在墨西哥,我们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有些研究者指出,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西班牙语译本第一次传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人们觉得那是和原著完全不同的一本书。但不管怎样,我小时候读过的《罪与罚》真的很好看,因此我不知道翻译会对原著有多少改变,我只知道它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原创的作品。
西班牙语来自一个语系,而中文来自另一个语系,这并不否认它们都是语言这一事实。因此我认为,所有书写都是可被翻译的;当然了,这其中有好翻译和坏翻译的分别。我知道我的英语译者非常棒,我的意大利语译者也非常棒,但我的德语译者就很糟糕,他没能成功传达我原来书中那种幽默感。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译者如何,但我有种感觉,他的翻译应该挺不错的。通过翻译,我们和彼此联结,否则我们就是一座座孤岛。通过翻译,我们西班牙人还是可以读到古罗马的史诗,可以了解不同地方、不同语系的文学、史诗等等,而这也让我们看世界的观点产生了变化。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