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天,乔尔·伯格(Joel Berger)和同事马西·约翰逊(Marci Johnson)在北极亲眼目睹了一桩惨案。结了冰的湖面上,散落着断肢残体和一簇簇棕色毛皮。两名生物学家追踪一个为数55头的麝牛群已有多时,最终得来的却是这般景象。
后来他们才确定,这桩惨案的始作俑者是一场冰海啸,罕见的风暴把海水和冰块一股脑地吹到了麝牛所处的湖面上。伯格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其工作环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恶劣的,而他所研究的那些生活在此环境中的种群,大都披着谜一般的面纱,例如麝牛。他的新书《极限保护》(Extreme Conservation)记录了他在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纳米比亚、西藏、蒙古和不丹的工作历程。他目前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资深科学家。
伯格也坦诚地谈到了自己的担忧,他追踪、安抚以及为动物装上无线电项圈的行为也许会对动物造成创伤——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资料,以便帮助整个种群。“保护也可能有血腥的一面,”他说,“现在就仍然是这样。”下面是一段笔者与伯格的对谈,为求简洁而略有编辑和压缩。
莎拉·张:你的书一开头就提到了麝牛。这些生物一度被赶出了阿拉斯加,到了1930年代,又因为一项计划而得以从格陵兰返回至此。请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事情经过。
乔尔·伯格:年幼的麝牛大概是这么被抓的:猎人会先杀掉所有的成年麝牛(因为太过危险,连成年人都对付不了),然后再抓捕剩下的小辈。这种场面是很悲剧的,大概类似于当着大象宝宝或者婴儿的面杀死他们的父母。
成年麝牛在格陵兰被杀掉了,幼年麝牛则被捕获并装上了船,运到挪威。接着它们又在挪威换乘别的船只,去到了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和新泽西。再接下来,通过火车——请牢记在心,这一切都发生在1930年代——坐火车一路到西雅图。它们在西雅图上船,被运到阿拉斯加州的西华德,再乘火车到费尔班克斯。然后它们会坐育空河上的船,一路穿越白令海,换乘最后一趟船到达这座岛上。后来到了1970年代,它们又被装上飞机,被分别投放到阿拉斯加州的三个地点。

张:这种办法居然会有用,真是神了!
伯格:是,确实很神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人都知道野牛的故事。比较起来,野牛虽然也有悲惨的历史,但由于生态的恢复,仅美国一地目前就还有将近五十万只野牛。我觉得麝牛的困境是一般人根本理解不了的。现在它们回家了。身为原本就在阿拉斯加安家的生物,被赶出去又被请回来,这段历史真是让人扼腕。
张:显然,我们现在绝对不会杀掉父母来捕捉宝宝了。如今在保护区里,我们会在直升机上让动物镇静下来,然后给它们戴上无线电项圈,这种行为十分常见——这一点让你十分苦恼,后来你就不再这么做了。为什么?
伯格:保护也可能有血腥的一面,现在仍然如此。那既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血腥,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要获取特定种类的资料,明白动物迁徙的去处以及它们生活得是否舒适是很重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时给动物戴上无线电项圈。在我们与美国地质学调查(USGS)合作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固定了(immobilized)200只以上的动物。但有时候我们没法让单只雌性动物回到群体当中,这个比例不大,大约占总数的5-10%的样子。麝牛高度依赖群体生活,这与大象类似。
这些动物会独自四处漫游,它们会住进我们所称的雪洞(snow hole)里。你可以想象一间厕所或盥洗间,长宽大约10英尺,高6到8英尺——雪洞差不多就这么大。这些落单的动物——之所以落单是因为没法再跟动物群会合——会在雪洞里住上最多两个月。当我们回去追踪这些动物时,我们会收集它们的排泄物,检视其中的荷尔蒙,以对比动物在独居和群居状况下的差别。我们发现,它们的紧张程度和皮质醇指标比原来高了五倍。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动物也是有情感的(sentient),它们在没法过群居生活的时候会变得高度紧张。而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正是我们,对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骄傲。

我们不再对动物使用梭镖(这里应当是指远距离为动物注射镇静剂之类的药物——译注)和无线电项圈了。我觉得这对它们很不公平,哪怕因此而牺牲一点资料的质量也是无所谓的。这么做有一定残酷性,我想尽量小心一点。我很难面对自己,所以后来就不那么做了。我们找到了一些变通的办法。
张:那你现在是如何研究麝牛的?
伯格:北极圈里没有道路可言,动物的密度也非常低,要找到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会租一架小型飞机,尽量把飞行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确保既能观察到动物,又不至于惊吓到它们。我们会记录下地点并且乘坐雪地车回来。我主要在冬天工作,方便靠雪地车来机动。我在阿拉斯加工作的时候会雇一些当地人,还会和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一同工作。加拿大和育空北部的工作内容也大概类似。原住民在那里居住了一万年有余,他们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并且他们也精通机械。因此我平时都是靠雪地车出行,并且和熟悉地理的人们住在一起。我们外出野营的时候会住在打鱼的小屋或是林间的小木屋里,我们一般会把雪地车开出一英里左右,然后下车去观察动物。
张:你的研究内容之一是考察麝牛对熊的反应。显然你没法靠自己来让野生的熊放松警惕,你必须变成一只熊。
伯格:(笑)精华部分来了(原文为elevator-pitch,“电梯间演说”,商界俚语,要求在极短时间内以富有吸引力的方式陈述要点——译注):等到冰稍微融化,我们就能在大陆或者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上看到更多北极熊,后者属于俄罗斯管辖,我恰好有去上面工作的特权。我们还发现了更多向北迁徙的灰熊。我们试图弄清麝牛能否准确判断熊的危险性。北极熊和灰熊的互动是相当少见的。从科学研究的需求出发,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样本量,而获取足够样本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做所谓的实验。于是我自己变成了熊。穿上披肩,戴上熊的头套,还要用四只脚走路。
张:等等,你用来假扮熊的外套是什么做的?
伯格:我会把它做得尽量轻便,头部用了泡沫聚苯乙烯,外面覆盖有白色或棕色的毛皮,具体颜色取决于要扮北极熊还是灰熊。俄国人送了我一套狙击手套装,所以我是一身白衣加上熊的头套。在美国,我会穿上棕色的披肩。我用滑雪杆充作前肢,后肢则是轮子——穿这么一套实在很累人。这听起来很有趣和疯狂。它也许很疯狂,但谈不上有趣。扮熊的时候是高度紧张的,但我们的确通过这种手段取得了资料,样本量也相当喜人。
张:麝牛对“熊”有什么反应?
伯格:出于严谨的考虑,我们扮熊做研究的时候也要有控制变量。这个控制变量就是北美驯鹿,它是不会吃麝牛的,和麝牛一样是食草动物,不会有什么威胁。如果我是只北极熊,并且有雪景做掩护,那我可以前进到距离麝牛非常近的地方,它们是看不见我的,因为我一身雪白。但如果我在雪地里扮灰熊,那走不了多远就会被它们发现。它们很不喜欢熊,反应非常激烈。如果有灰熊来袭,牛群不会逃跑,而是会聚集在一起摆出防御的阵形。由于灰熊跑得很快,可以一直追逐猎物三英里,麋鹿和北美驯鹿就会被这么追上。从另一方面看,北极熊就不太擅长追猎。麝牛能识别出这一点——它们知道自己可以跑得过北极熊。


张:你也曾在诸如喜马拉雅山和中亚的草原以及其它许多极端环境下工作过,在动物保护和当地人的生计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譬如克什米尔山羊的问题。
伯格: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世界上90%的克什米尔山羊都来自蒙古和中国北部。整整占了九成。养这种羊的人本来就是牧民或者过着半游牧式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就不怎么好过。如果让他们来打理羊群,那是不会缺乏动机的,因为他们会养出更多的羊来卖钱。
这么一来,要平衡这两方面就并非易事。随着牧人数量的增加,翻个四倍乃至于超出群体的承受能力,山羊也会很快把地上吃个精光。大约有10-12种富有魅力的种群生活在印度北部的拉达克-西藏-蒙古一线,譬如野生牦牛、濒危的大夏骆驼以及生活在超高海拔地区的(大约有15000英尺高)西藏野驴,还有雪豹、塞加羚羊等等。那里的野生动物种类多到数不胜数,而且很多目前还不为人知,毕竟那片地区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动物也大都处在濒临灭绝的状态。
在西方,鉴于山羊的这些特性,克什米尔山羊的消费性使用对生态环境尤其具有破坏作用。要让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些消费克什米尔山羊最多的地方对此产生警惕,并且在山羊产业里为牧人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是相当困难的。

张:你的书侧重于关注有蹄动物,然而——无意冒犯——它们似乎不那么有魅力,在动物保护的行当里算不上什么明星。你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些动物呢?
伯格:不少动物都可以说有专属粉丝了,特别是鲸鱼、企鹅、老虎、大象和犀牛这些。它们有专门的支持者群体,而它们的确也需要帮助,这不是说别的种群就不需要帮助了。许多种群生活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如果你在街头拦下某个人,向他们询问有关老虎的事情,他们一般都明白老虎是濒危动物,他们也知道北极熊日子不好过。但如果你提起马驼鹿、扭角羚或者麝牛,那他们就没什么概念了,遑论其它一些更不知名的动物。这些种群需要有人为它们发声。
张:你的书用一只北极熊做封面,这有些讽刺。
伯格:是啊,而且我不是专门研究北极熊的。(笑)我觉得那张照片暗示了某种现实,北极熊站在逐渐消失的冰原边缘。而我们也留意到其它一些种群的危急处境,那将是我接下来的工作去处。我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关系很好,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下面的话说出来也许会有点让他们没面子,但我在这里就不遮遮掩掩了:我们双方讨论封面的时候情况有些不同,我原本想要别的动物来当封面的。书传递的信号不一定非得是关于北极熊的。它牵涉到所有生活在极端环境下且濒临灭绝的种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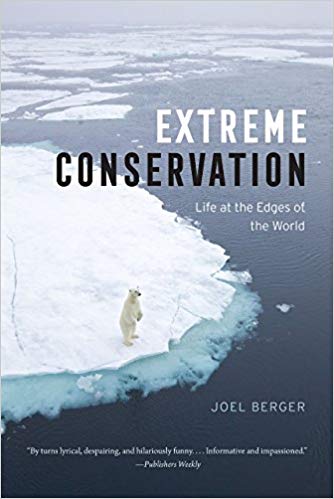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