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人类想象与图像学(iconography)中经常占据关键地位。在绝大多数语言里,心脏都被视为灵魂与情感的居所。这毫不奇怪——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当自己焦虑或激动时,我们就会有“心跳到嗓子眼”的体验。我还记得,在我做神经外科顾问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当要做高风险手术时,胸腔里便会有某种东西在弹跳的感觉,在忽然发觉自己要独力支撑起父母的生活时也是如此。
借助于对现代人而言高度敏感、几乎无法忍受的动物实验,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7世纪创立了血液循环理论,但科学的医学及其对人类生理机制日益系统化的解释,则要到19世纪才真正起步。在现代以前,医学史的重要侧面之一正是其缓慢的进步速度,如果不是全无进步的话。譬如,帕拉塞耳修斯(Paracelsus)在16世纪就能用乙醚对小鸡实施麻醉,但麻醉大规模进入临床实践则是在20世纪。安东尼·凡·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在17世纪发明了显微镜,但它在医学中的运用还要等到19世纪。
随着科学化医学的兴起,心脏开始被视为某种泵(pump),人们会“因为心碎”而死或诸如此类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想象遭到了抛弃,其地位与民间故事无异。心脏病乃是一系列物理变化的后果,譬如心脏供血、导电系统或瓣膜等出了问题。不过,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又重新开始认可传统观点的正确性,即心脏与情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状态对心脏的健康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心脏与大脑息息相关——用术语来讲,居于其间的乃是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们也负责激素的循环,激素的分泌则由大脑来控制。在高压状态下,交感系统会活跃起来,心跳也随之加速;在放松的状态下,副交感系统则开始活跃,心跳因之而慢下来(只有在性高潮期间,两套系统才会同时处于活跃状态)。当某人患上章鱼壶心肌症(Takotsubo cardiomyopathy)之类的疾病时,在极端的高压之下,心脏的形态会变得像同名的日本渔具一样。这种病跟心脏病的发作高度相似,它最初被发现于诸如地震或海啸等大灾大难的幸存者群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有致死性。某项针对117名曾得过急性心律失常的病人的研究显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经受到过公然的羞辱、丧亲之痛或在病发前24小时内碰上过类似的高压事件。另外五分之四的人则没有这种情况,但这不过表明几乎所有疾病都是多因素的(multifatorial),这个概念让经常倾向于把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单一因素的人类大脑和《每日邮报》有些抓狂。
美国心脏病学家桑蒂普·乔哈尔(Sandeep Jauhar)在《心的历史》(Heart:A History)一书中对此有相当漂亮的分析。他回顾了心脏病的历史——这是一部用动物、病人来做实验的历史,有时医生们也会亲自上阵。例如,魏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在1920年代曾对心脏病学做出革新性的贡献,当时他就把一根导管插入自己手臂上的血管里,一直通到心脏——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万分危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一个技术迅猛进步的故事,但乔哈尔也总结道:“我们远离了情感化的心,开始狭隘地关注生物力学意义上的泵。”他告诉读者说,这种思路对病人是有害的。他更倾向于同意莎士比亚在喜剧《心的徒劳》中所提出的“豁达者长寿(A light heart lives long)”。
乔哈尔和几名杰出且天赋优秀的亚裔美籍医生一道面向公众写作,其中还包括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和新近的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这种现象可能跟美国的医学只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有关——这与欧洲迥然不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美国医生的教育程度比欧洲同行更高。

当今医学类科普写作一般会涵括作者自己的个人以及家庭故事,这几乎成为通例,乔哈尔的作品也不例外。他出色地完成了这种整合。书的开端描述了他自己的CT血管造影片,其中有早期冠状动脉疾病的征兆,这跟家族遗传有莫大关联。“我觉得自己好像对今后如何死去有了一丝预见。”他看着自己心脏的影像说道。这无疑为整本书注入了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全书以心脏病学迷人而美妙的历史为主干,结束于乔哈尔对自身心脏病以及必死性(mortality)的接纳,但他同时也表示要加强锻炼,在工作上也许不必太拼。
乔哈尔特别提到,他的书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伟大的美国心脏病学家伯纳德·劳恩(Bernard Lown)于1996年出版的《失落的疗愈艺术》(The Lost Art of Healing),后者发明了直流电心脏除颤器,并以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的名义获得诺贝尔奖。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也对所谓心脏功能的身心相互作用(psychosomatic)一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劳恩讲述过许多这样的故事:表面上看来快要因心力衰竭而死的病人们因为有了希望而复苏了。劳恩(如今仍然健在)曾公开承认,对病人说谎也是一种治疗策略。他认为,希望是一种强有力的药物——所有愿意在此方面有所思考的医生都明白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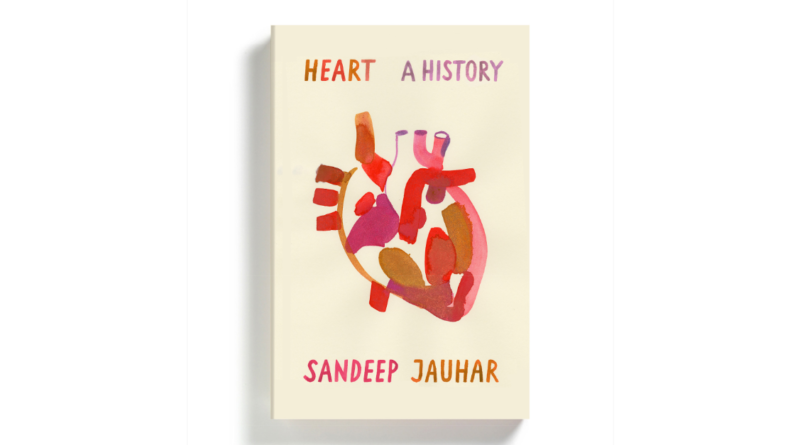
罗恩写道,在现代,医生对被指父爱主义(paternalism)以及犯错误的恐惧有过度之嫌。他们日渐依赖于昂贵的技术和调研,在不少国家还涉及到盈利的动机。其代价则是忽视聆听病人心声,不把他们当成人类同胞,仅视其为患病的躯壳,忘记了他们在诊断和治疗之外还需要希望和心理支持。这并不是说对病人以礼相待、富有亲和力,把希望带给他们,就可以治愈癌症或者让我们永生,但的确有无可反驳的证据表明:精神状态对心脏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免疫功能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后者不那么确定。当然,身体和社会环境对我们精神状态的影响都不可小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59年曾在《护理笔记》(Notes on Nursing)里写道:“我们知道,形式、色彩和光线可以感染到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切实的影响,但具体作用机制则不为人知……”自笛卡尔以来根深蒂固的心物二分论总归是错误的。
罗丝·乔治(Rose George)的散文集《九品脱》(Nine Pints)就或多或少地与血这个主题相关。书的封底告诉我们,她之前还涉及过有关人类垃圾和远洋运输方面的主题。她的研究——读起来经常让人有种类似于略显急促的纪录片旁白的感觉——把她带到了世界各地。
她去到了尼泊尔的一个偏僻角落,并与那里的人展开对话,当地文化教导女人说月经是不洁的,经期女性必须单独居住在彼此隔绝的小屋里。她将这一现象与现代世界与月经有关的诸多禁忌联系在一起(显然,在向议会陈述2000年度的预算时,戈登·布朗对于自己慷慨地把卫生棉条的增值税减到5%这件事有些难以启齿)。她在加拿大得知了血浆(也就是在血液整体当中去掉红细胞和白细胞之后的剩余)可以被收集起来服务于商业用途,然而献血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志愿性的。
有许多血友病患者因输了携带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血浆而死亡,卫生部门对此的回应却是出了名地拖沓,这些血浆大多来自美国社会中的底层群体,而该群体一般是此类疾病的温床且经常靠卖血维生。
在美国输血服务的历史中,有一个颇为有趣的桥段,主角是名不见经传的公务员佩西·奥利弗(Percy Oliver)和稍微有那么点名气的简妮特·沃恩(Janet Vaughan)。在男性主导的医疗行业里面,沃恩不得不去克服四面八方的偏见,乔治对此多有记载。回望过去,女性的智慧在以往是相当容易遭到轻视的(如今在世界上不少地方仍然如此),不过这本书也在多处表达了对女性智慧的承认以及对轻视的愤慨。譬如,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就因其对月经的偏见而被批评为“犯了错误……错得彻头彻尾”。
乔治还曾去南非考察过艾滋病的影响以及政府多年来拒绝批准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根源。她在伦敦的医院了解到了大量输血和积极手术在重症创伤病例中的角色——艾米莉·梅修(Emily Mayhew)最近在《沉重的计算》(A Heavy Reckoning: War, Medicine and Survival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这本出色的著作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探讨。
乔哈尔和乔治的书在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哈尔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心对我来说是一种困惑”,而他描写心的书也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他在这个主题上是不折不扣的专家,且文笔优美。罗丝·乔治的书则是细致的新闻报道的产物,涵括了许多本质上不相干且有时显得极为复杂的主题。
心和血在以往被视为是人类存在的核心因素。实际上,它们的重要性并没比其它主要器官高出多少——没有肝和肾(除非依靠透析)我们同样无法生存,大脑、皮肤或肺也是同理。我们是由细胞、器官和细菌共同构成的一个高度复杂的共同体。微生物——或者说人们所称的肠道里的万亿小虫——之于健康和疾病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譬如它与帕金森病的关系。但话说回来,也许某些器官就是比其它器官要更有诗意一点。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