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本书,改变你对经典文学的看法。1941年,伍尔夫去世。几十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日记被拆分为五卷,在1977至1984年陆续出版,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换一个眼光打量她漫长而充满活力的事业。最早开始整理伍尔夫日记的是她的的丈夫伦纳德,在1953年,伦纳德编整出第一册日记选集,完全聚焦在伍尔夫的写作过程,避开了一切私人细节。然而正是后来伍尔夫的日记完完全全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才能稍微窥见她写作时那复杂的思想珍宝。
在这些日记里,伍尔夫的生活时而妙趣横生,时而平淡无奇。“现在我得整理一下我做过的那些事,”1922年8月22日,她在日记中写道,“6月10号,我这一天都在拍照。而现在我要再添上一项,昨天一整天我都泡在衣橱前。然而这一切都是败笔——这些奉承、华服、建筑和摄影,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没办法继续写《达洛维夫人》的原因。”从她的日记里,我们还能看出伍尔夫时而毒舌,时而刻薄。她如猫般刁钻,而且还时不时带上一点种族歧视。鲁斯·格拉伯(Ruth Gruber)的第一篇博士伦主题就是伍尔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和伍尔芙曾短暂而愉快地通过一阵子信。然而后来伍尔夫日记出版后,格拉伯才发现她轻蔑地将自己唤作“德国犹太人”(尽管格拉伯出生于布鲁克林)。格拉伯对这段经历的评论一语中的,“日记能撕下其作者脸上的那层面具。”
许多其他作家也出版过自己的日记,但这本《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伍尔夫小说的注脚,其本身就是一部文学作品,让读者拥有独到的目光,了解这位女作家在这样戏剧化的时代,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并为之讶异。“我不会变成一个‘名人’,也不会是‘伟人’,”伍尔夫在1933年写道,“我会继续探险,继续改变,开拓自己的视野,也展开自己的思维。我拒绝被定义,拒绝刻板印象。想要释放自我,就得找到自我的各个维度,并且不为之羁绊。”从1897年,伍尔夫就开始写日记了,当时的她只有14岁。往后余生,断断续续,她一直保持这个习惯。1941年3月,她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四天后便离开了人世。伍尔夫这一生单单是日记就留下了超过77万个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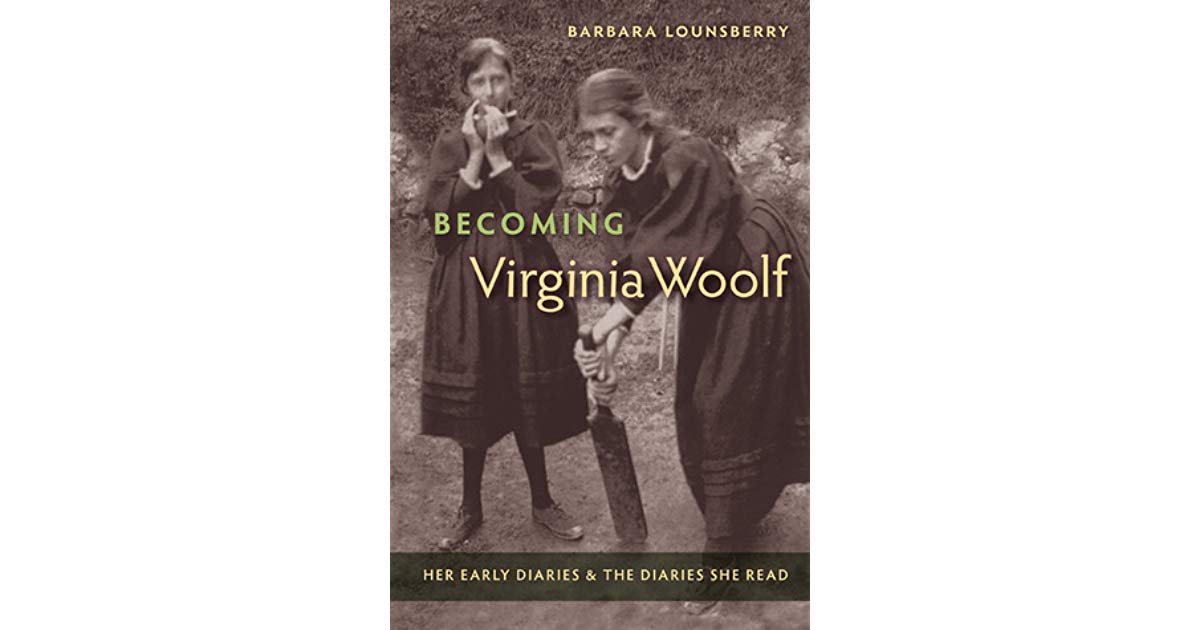
“伍尔夫半私人的日记可以说是她个人潜意识与公开文章之间的临界线。”芭芭拉·劳恩斯伯里(Barbara Lounsberry)写道。劳恩斯伯里是北爱荷华大学英语系名誉教授,也是研究伍尔夫的著名学者。今天,劳恩斯伯里通过三本书,给我们送上了更加全面理解伍尔夫日记的钥匙:它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创作的、我们应该如何解读。2014年出版的《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日记及她读过的日记》(Becoming Virginia Woolf: Her EarlyDiaries and the Diaries She Read)、2016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之路:中期的伍尔夫日记及她读过的日记》(Virginia Woolf's Modernist Path: HerMiddle Diaries and the Diaries She Read)和2018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身外之战,内心斗争:伍尔夫最后的日记及她读过的日记》(Virginia Woolf, the War Without,the War Within: Her Final Diaries and the Diaries She Read),在这三本书中,劳恩斯伯里给读者们献上了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详细而全面的解读,也改变了人们解读这些文字的方式。
劳恩斯伯里从标题开始重新诠释这本书——这并不是所谓的“一本”伍尔夫日记集,而是38册不同的日记,每一卷自成一体,都是一本书,都是伍尔夫一手搭建的一个独立的项目,目的各不相同,写作时期也散落在她写作生涯的不同阶段。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拢在一起,当成一个整体,一本鸿篇巨著来阅读,那伍尔夫日记可能就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十分相像了——成了一种宏大冗长、一贯到底甚至有些傲慢的作品,成了一个从一而终的、规规整整的经典之作。但伍尔夫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连串不同的声音、情感和人物角色的集合,既趋于分离,又互相重叠,兼具实验性和临时性——伍尔夫通过日记,对所有这些声音进行调整处理,让它们同时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冲突,这样的解读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
举个例子,在1917年,伍尔夫单独写下两本日记,并且同时在两本日记上多次记录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篇日记始于1917年8月3日,在“阿萨姆家园”里写成。在这篇日记中,伍尔夫花了大把笔墨在自然世界上,语言简短,断断续续:“男人在整修这阿萨姆家园的墙壁和屋顶。威尔在前边把床都挖出来了,只留下一朵大丽花。蜜蜂藏在阁楼的烟囱里。” 劳恩斯伯里指出,这篇日记“是伍尔夫对1917和1918年的的田野札记,记录着自然,也写下了战争。在日记里,你能看到她对大自然和人类劳动的好奇,自然历史学家和公共历史学家在她的所有日记中也总是占得中心位置,而这些都未曾充分展现”。

两个月后,她又开启了一本新的日记,这次是一个合作项目,伍尔夫和其他人都可以在此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想在日记里进行这样的尝试,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我衣柜里找到的那本旧日记,那是1915年写下的,直到现在,我们读到它依然还会嘲笑沃尔特·兰姆(Walter Lamb),”伍尔夫在10月8日写道,“因此,在这本日记里,我们会照计划来——配上一杯茶,握起一支笔,小心翼翼地写。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连L.(伦纳德)都答应过,如果他有话要说的话,会在日记里写上几页。他就要克服自己的谦逊了。”这些同时写下的日记,各自站在不同的起点,各自有着自己的目的。而这只是伍尔夫利用日记这种题材,尝试发出新的声音探索形式限制的方式之一。伍尔夫通过“一种比她以往读过的日记结构更具实验性的日记”,为自己发声,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创造了一部关于内心状态的杰作。
同时,劳恩斯伯里的这几本书也是读者在研究日记本身时的向导。她留意到这些日记的尺寸:“这本日记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文章。”伍尔夫抱怨起她1897年的一本日记本,只有5.5英寸*3.5英寸大小。这是一本典型的给14岁小女孩用的日记本:套着皮套,配有锁和钥匙,而这种本子很快就被她抛诸脑后了。伍尔夫开始自己装订日记,其中起码有一本是她用来写作的,因为每一页的左侧边距都画了一条红线。虽然如此,它们依然大小相异,大小不一。劳恩斯伯里解释说,“在阿萨姆家园里用的那些小尺寸的日记本,可能就要求她对文本进行压缩了。”劳恩斯伯里认为,她这段时间内的日记风格轻快、精简,也许还得归功于此。
在这三本书之间穿针引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是伍尔夫所写的日记,而是她曾经读过的日记。劳恩斯伯里追踪着她读过的其他作家的日记,以及这些文字对她创作的影响。少女时代的伍尔夫曾经狼吞虎咽,在12天里看完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25万字的日记。佩皮斯和范妮·伯尼(Fanny Burney)、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和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一并,给伍尔夫的日记写作生涯留下了深远影响。她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嫁接其他日记作家的点子,比如说“实验与合作”这个想法就是从龚古尔兄弟哪里借来的,并由此孕育出她与好几位作者共同书写的“霍加斯宅(Hogarth House)日记”。劳恩斯伯里认为,伍尔夫比任何著名的日记作家都要沉醉于日记文学,甚至放到今天,这么说都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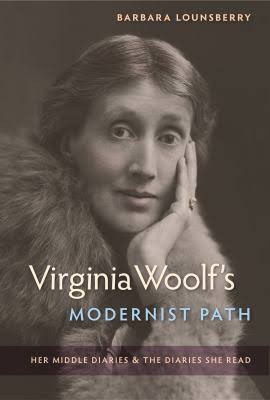
我们已经习惯了文学作品之间交相呼应:《尤利西斯》重新诠释了《奥德赛》,《藻海无边》反写了一个和《简·爱》如出一辙的故事。但这些小说无一不是一本出版的作品和另一本已出版作品的对话。伍尔夫和其他日记作家的对话就不一样了。日记是其作者个人隐私的独白,在去世后才公之于众(佩皮斯就更是如此,他死后好几个世纪,日记才得以公开),伍尔夫呢,她也正是在自己私人的场景下对这些日记一一作出回应。
尽管如此,她的日记从来都不是绝对私密的。伍尔夫似乎打小就知道有一天会有别人读到她的日记:“我做出了一个最英勇的决定,改变我对书法的看法,贴合我的家人。”她在1899年的日记中写道,似乎早在那时,她就意识到她希望自己这些私密的想法能有读者。伍尔夫还重写了自己的日记,劳恩斯伯里在这三本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随着“她不断带着批判和好奇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日记”,它们也在不断丰富。
传统意义上讲,伍尔夫的众多日记可以一分为二。其中之一就是她思想成熟时期写下的文字,由1977到1984年出版的五卷组成。这些日记始于1915年,也就是她第一本小说《远航》 (The Voyage Out)问世的这一年,似乎是在强调,这些日记并不是什么无名的年轻女孩的絮语,而是出自一位作家之手。这些早期的日记在1990年出版,届时编排已经井井有条了,这卷日记文集也被命名为《炽烈的艺徙》(Passionate Apprentice)。然而对于这种两段式的时期划分,劳恩斯伯里不以为然,她更倾向于将伍尔夫的日记分为三个阶段,这一点在她的伍尔夫日记三部曲中充分体现:她的第一本书焦点是伍尔夫早期的实验性日记,到1918年为止;第二本则是她现代主义巅峰时期的作品,覆盖了往后的十一年;第三本则记录了她人生的最后十年。在《岁月》、《三枚金币》和《幕间》(Between the Acts)这最后几本杰作的创作过程中,伍尔夫不断挣扎。法西斯一路高歌,世界走向分崩离析,这位作家也在努力抵挡着巨大的绝望。
劳恩斯伯里的三部曲的第一本大概是最有趣的,在这本书里,年轻的伍尔夫还在摩拳擦掌,拿日记做各种实验,探索更多可能性。在这段时间,伍尔夫的前两部小说《远航》、《夜与日》(Night and Day)都已经完成,但并没什么出格之处。从形式上看,它们依然遵循着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惯例。直到1922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出现,我们才看到伍尔夫对小说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大尺度的实验和探索。这与她的日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时的伍尔夫已经在日记上大胆实验了许多年,尝试了各种全新的形式,把她从佩皮斯和博斯韦尔身上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变出了全新的花样。
中间的这些年也是伍尔夫创作的鼎盛之年,也是她最高产的几年,相对应地,她这些日子的日记本也变薄了——只要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文字转化为能赚到稿费的小说,对自己秘密花园的思想之井就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了。她“空闲的第二个日记阶段”在三段时期中大概是最平淡无奇的了,原因很简单,这时候她写出最好的东西大多都集结在20年代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比如《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一间自己的房间》、《奥兰多》、《普通读者》和一众这个时期的散文和其他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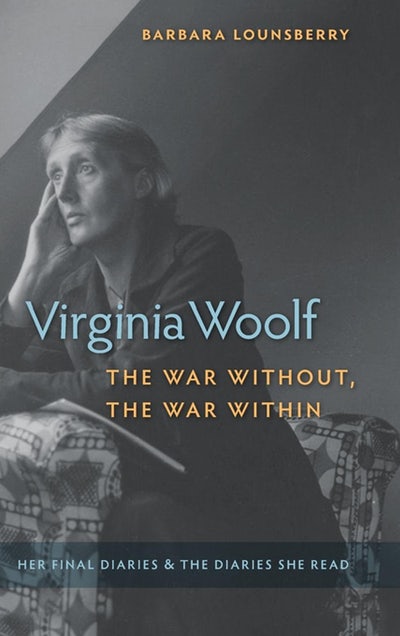
在第三本书中,伍尔夫的创作之舟搁浅了——《浪潮》(The Waves)尽管精妙依然,却得来不易。1937年历经挫折写出的《岁月》就更是如此,差点把这位作家击溃。于是伍尔夫越来越经常地投入日记的怀抱,摆脱公众形象对她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倾诉。1935年3月18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想要具体表达所有这些想法真是一件苦差事啊,我不断地对外界暴露自己的想法,任它舒展,让它强化,就像是被那创造的光热暴露在外在世界的冲击之下。” 劳恩斯伯里认为,在这些年里,伍尔夫的日记中“出现了一场斗争,这是她对自由的激烈追逐”。
在这些晚期的日记中,遗漏的内容和记录在纸上的东西同等重要。1937年6月8日,侄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奔赴战场,参与西班牙内战;7月20日,伍尔夫便收到了噩耗。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伍尔夫都没有再碰她的日记。终于,朱利安去世的17天后,她写道:“好吧,人还是得重新开始的。奇怪的是,我天生絮叨,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基因,却没办法逼自己写一写朱利安的死。”如果说这些私人日记曾经让她将秘密思想转化为文字,那么到三十年代晚期,她脑海里的东西已经无法倾注于纸上了。随着伍尔夫内心世界的斗争和恶魔逐渐将其吞噬,她晚期的日记里空白也就越来越多。
劳恩斯伯里这三本书按部就班,有时甚至有点沉闷无聊。循着时间的轨迹,劳恩斯伯里在一本本日记里向前推进,其中穿插着当时伍尔夫所读的其他作家的日记。有时你会觉得这不是别的什么文学作品,而是一套档案集。她的目标受众也主要是其他研究伍尔夫的学者——当然,所有伍尔夫日记的粉丝,以及那些想知道女作家如何驾驭公共角色和私人写作的人,都能在劳恩斯伯里的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如现代主义学者伊丽莎白·波德尼克斯(Elizabeth Podnieks)所说的那样:“许多女性在写日记的时候虽然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被发表,却还是会假装这是完全私密的。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得以和读者沟通,表达她们过于个人化,或者饱富争议,不能在小说中呈现的观点,但同时她们又希望并且需要被聆听。”伍尔夫就是一个典例,她在日记中时而狡猾,时而平凡,有时展露出她刻薄的自我,与呈现在公众面前悉心雕琢的形象迥乎不同。在劳恩斯伯里的书中,伍尔夫日记不再只是小说的幕后花絮,而是记录了这位女作家在私人生活和公之于众的写作之间的来回拉扯,给读者们描绘出一幅更全面的画卷,展现伍尔夫的真实生活。
幸运的话,这几本书还将继续推动学者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重新审视伍尔夫日记。也许我们还能看到专门分析一本日记独立成书的作品——尽管美国和英国有着版权法的限制。出现“阿萨姆自然离世日记”、“1905年康沃尔日记”和“1903年草稿本”这样的作品也并不是不可能。芭芭拉·劳恩斯伯里对伍尔夫日记的意义,就跟当年伍尔夫日记之于其小说的意义一样,所有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所追求的也正是如此:通过标准规范的文学研究,提供一种阅读日记的全新视角。
本文作者Colin Dickey著有《鬼蜮:闹鬼之地的美国历史》(Ghostland: An American History inHaunted Places)及另外两本非虚构作品。迪基目前正在创作一本关于阴谋论及其他错觉妄想的作品,书名为《不明之物》(The Identified),预计将于今年出版。
翻译:马昕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