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吴梦
编辑 | 黄月
如果做一名花匠就能够养活自己,并且能从照料植物中获取自足的快乐,那何必去做一份自己不那么喜欢、却拥有更高社会评价的职业呢?
2012年,City & Guilds发布了职业幸福指数报告,报告列出了英国人认为促成他们工作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在接受调查的2200名工人中,园丁与花匠是幸福感最高的职业,其次是理发师和水管工,毫不意外的是,银行家、IT专业人士和人力资源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最不满意。具体的生活经验与人们的社会认知相抵牾——金融工作者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社会地位显然高于“卖花的”,这既是基于收入的判断,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判定常规成功职业的思维惯性。
关于“好工作”的叙事往往不在意人们真实的感受,而十分重视某种身份地位秩序。如果这仅仅是关于“幸福生活方式”的其中一种叙事,也许会有一些人因践行此种价值观而感到幸福,但一旦某种单一的幸福叙事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进而被认定为拥有特定合法性的权威,它就会创造痛苦与不和。
我们对这样一套完美生命历程的叙事并不陌生:恋爱必须放在大学,因为你应当在学有所成后再谈恋爱而且毕业后马上结婚,对女生而言最好硕士文凭就封顶,“超级妈妈”则是她的理想目标和最终使命。在这一趟充斥着各类默认惯例的生命旅途中,还有一些频繁出现的劝诫,比如“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当……”,比如“接受它,因为我们从来都是这么做的”。生活里充斥着无数人为制造的同意(managed consent),它们被赋予道德依据并构成了一种被广泛认为是“正确”、公正、合理的对于世界的安排。这些弥散性的“安排”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无处不在的幸福叙事替代了迷茫现代人的主动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成为了RPG(Role-playing Game,即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人物,需要扮演特定的功能性角色,升级打怪换装备只为通向被设定好的完美结局。
幸福叙事的陷阱:被垄断的价值,被压迫的个体

有更多的收入、拥有社会地位更高的工作,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职业满意度?离婚,或者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是否是一种“浪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为科学教授Paul Dolan在他的新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完美生活的神话》(Happy Ever After: Escaping The Myth of The Perfect Life)中主张,是时候揭穿这些“幸福叙事的陷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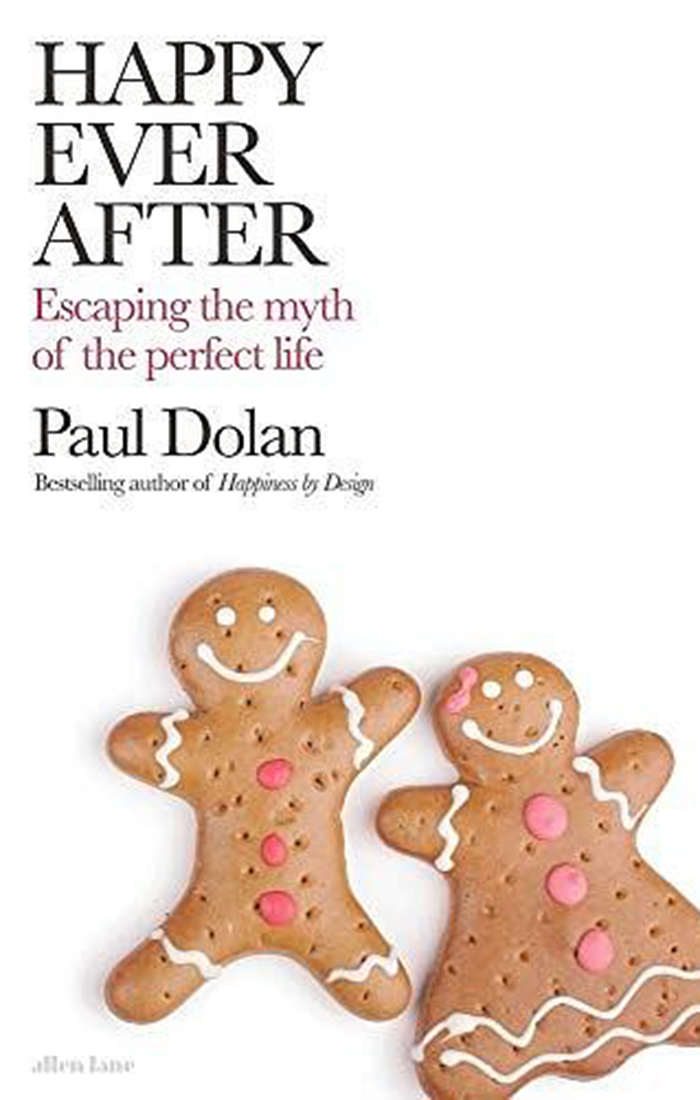
Paul Dolan
Allen Lane 2019-1
在书中,Dolan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所谓的身份标签与对应的社会期待对人造成的压迫与伤害。在一次关于“情感与理性”的小组讨论会上,Dolan因为在持续一个小时的讨论中说了两次“fuck”,在会后被一名男子拦住质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扮演工人阶级的英雄呢?”并被教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不该说脏话”,他需要“修正自己的行为”。在Dolan看来,这次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反映了由权力结构、历史实践、文化期待等所堆叠而成的社会叙事的强大有力与无孔不入。在那名男子指责他的行为与身份不符的语境中,说脏话是词汇量不大和智力不高的表现,也是工人阶级的特点,与此同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则应负担起某种公认的社会责任——树立一个素质良好的、用语优雅文明的高知好榜样。这些规训人们举止行为的“叙事陷阱”加到一起,就构成了完美生活的神话,规训甚至强迫人们以一种特定的、符合其身份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Dolan在书中引入了详实的数据调查结果,以揭示各类叙事暗含的虚伪性。比如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人,并不比那些收入少于两万五千美元的人更幸福,他们还会有更强烈的“人生无意义”的虚无感,也更不关心与家人、朋友的相处;总裁和其他资深要员的收入最高,但他们的满意度并不比他们的秘书高,尽管后者的工资要低得多;神职人员和健身教练则是幸福度高于银行存款水平的典型代表。关于爱情的童话叙事也是危险的,毕竟,“在英国,有五分之二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崩溃与破碎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基本事实,这些信息也应该传递给正在学习社会知识的年轻人。

由此可见,主流的幸福叙事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幸福事实,而幸福叙事也并非平白无故地产生,其指向的往往是“物尽其用”、“压低成本高效运作”的市场经济逻辑以及对一种特规训形式的维护,比如“拼命加班会给你带来辛劳工作的满足感”之类的说法——自发性过劳已经构成了“成功叙事”的核心内容。毫无疑问,过长的工作时间会降低工作者的幸福感以及行业生产力,而与工作相关联的一系列词汇——“献身”、“荣誉”、“自豪”、“成就感”等等——也揭示了该行为所依附的价值观。仔细想想不难发现,这套“加班时间长=个人价值感高”的逻辑实则漏洞百出,但长久以来仍被用作为长时间工作正名的理由且被视作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种幸福叙事的陷阱通过外界标准帮助人们确认自我价值,这虽是对高风险现代生活的一种回应方式,但一旦用流行的幸福神话替代具体的生活本身,被模糊或公约的个人幸福的意义也就不再独特或真实了。
“幸福就在于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花时间与谁共事,它不存在于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认为应该让我们开心的一些故事中。”Paul Dolan在2014年接受《卫报》采访时对“幸福”下过如此定义。然而在理解与行动之间仍有一条难以跨越的沟壑,何况“满足社会期待(尽管有时不合理)”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浅尝辄止并怀有反思意识地“嗑”流行的幸福叙事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动力,让人们按图索骥地用主流定义的“幸福生活”与“成功的应有之义”来打理自己的生活。
焦虑的经纪人:按照社会期待,经营精致自我
当“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故事被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般的规训,“焦虑”的情绪便频繁见于被密密匝匝话语管辖的群体,为了让各个身份维度达到某一主流标准,他们遵从幸福叙事陷阱与身份设定,成为精心经营自我的经纪人。
在发表于“界面文化”(BooksAndFun)的文章《都市丛林求生录:有钱又有颜的女性,育儿焦虑一样比海深》中,记者傅适野在介绍人类学家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的著作《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个耶鲁人类学博士的上东区育儿战争》(Primates of Park Avenue)内容的同时,也提出了对被重重加码的美国上流阶层母亲身份的思考:Burberry、J.Mendel和Tom Ford是上流社会女性心照不宣的着装符码;年轻、苗条与性感等符合上流男性审美的性资本是软实力;密集育儿(intensive mothering)是模范妈妈的职责,因为孩子的健康与成功是妈妈们地位的象征。无处不在的攀比与较劲,使得上东区的妈妈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一场“准备好撕碎他人的竞争”中,这些“冷酷、无情,用眼神可以杀人”的女性一边遵从上东区的游戏规则,尽职尽责地扮演“完美母亲”的角色,一边与持续存在的焦虑搏斗,因为她们既永远无法满足层层叠加的母职要求,也不具备与男性对等谈判的条件和资本。

[美]薇妮斯蒂·马丁 著 许恬宁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11
琳琅满目的奢侈品、精致的妆容、优秀的子女、受人歆羡的社会地位……与其说这是某种彰显优越性的嘉奖,不如说是跻身上层社会的代价。社会对于理想母亲的角色期待使得女性的焦虑情绪蔓延,在马丁所描绘的上东区育儿战争中,母职不仅仅包括母亲的抚育职责,还需要以炫耀性消费的手段维护阶级区隔,父权体系的性与性别宰制也被编码入“超级妈妈”的形象塑造中。
任何构成一种类属的身份或经验都存在着被话语封锁的风险——除了母职,爱情也变成了一份复杂、精致、专业且消耗巨大的工作,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怎么做都不够称职的境地。
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在其著作《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以名为《接吻的艺术》与《恋爱术》两本民国时期的小册子为例,分析了这些与爱相关的法则与建议是如何帮助确立“爱情的新正统”的:年轻人们不仅必须学会用“接吻”代替俗气的“亲嘴”,还需要了解所有关于接吻起源、技术、姿势、礼仪以及“为什么接吻必须成为一门艺术的伟大问题”的一切;而《恋爱术》中的规则、技巧以及格言的形式,假设有一整套广泛共享的前提存在——爱情拥有了自己的规则,就意味着爱情在社会秩序中已占据了特定的(虽然可能是模糊的)位置,而这些从高处抛下的真理却避开了爱情如此定位是否合理的问题。

[美]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7
李海燕认为,这类监管式话语的风行对亲密的经验进行了殖民。这种“确立成规化方式”的做法在当代也屡见不鲜,人们也倾向于寻找一种整体的可被实践与评价的生活方式——某种一元的道德——来抵抗被多重社会空间分割的日常生活,并借助这些技术性话语寻找“该怎样生活”的线索。某种“完美母亲”、“完美爱情”、“理想形象”的符码服务于一场仪式化的公开亮相,是必须加以演示的东西,与天性无关,更与“应然”无关,它们俱是一种需要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被建构的形象,有着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因素。“钱越多越幸福”、“婚姻是幸福的要义”等世俗信仰与之同理,其本质是一系列社会叙事的偏见。
比比皆是的社会规范与叙事陷阱使得人们一出生就被迫参与进一场RPG(Role-playing Game,即角色扮演游戏),按照时间顺序,每个人从生到死的完美走向已被安排妥当,性别、年龄、阶级、职业等元素被建构成一套由一连串期待所生产的编年史之中,以社会惯例的面目要求人们亦步亦趋。对身份表演的社会期待使得人们做起了自己的经纪人,焦虑地审视自己未达标的身份维度,并将“自然的”观念与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引生活方向的信条,将自己的生活纳入“标准的”(文化的)期待模式中去。
幸福叙事的另一面:悬浮于当下,无为且焦虑
关于“什么是幸福/理想/应然模样”的叙述督促人们殚精竭虑打造精致自我,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这些流行叙事也使得一部分人与这种主流生活方式保持一定距离,以“无为”对抗风险和失望。
前段时间,原载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The Sex Recession》的中译版《性爱降级》刷爆朋友圈。文章指出,在社会环境第一次对性关系的多样性展现出如此宽容的面目之时,美国青少年的性生活却越来越少。作者Kate Julian继而分析了造成性萧条的诸多因素,其中一个便是,不论男女,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和人们对自身身体的不满意度呈现出了相关性。

“性心理学”、“恋爱入门”等课程的火爆以及糟糕的性经历说明,人们对于恋爱关系的了解与体验普遍缺乏,但弥补这种知识与经验缺口的方法,不是高质量的性教育以及恋爱双方的坦诚交流,而是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关于爱与性的社会叙事,包括但不限于广告与小黄片中模特般的身材、影视剧与言情小说中的爱情模式、博人眼球的明星八卦以及奇观式的典型报道。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流行的社会叙事为青少年提供了启蒙的素材,而网络使得这些信息的获得变得十分容易。一边是空白的生活体验,一边是泛滥的媒体话语,青年人愈发焦虑:在强化社会理想叙事的同时,他们为自身的“不合格”而感到焦虑不自信,在行动与思考时趋向于模仿已有的模板,且对现实生活投射了过高的期待与预设,认为生活处处不尽人意。一些典型的负面报道则以反向叙事的方式渲染了现实生活的险恶以及理想叙事的不可得,这也加深了青少年对于实际体验的恐惧,于是一部分人选择以遁入私人领域与虚拟空间的方式,逃避能够预期到失望与受挫。
“无为”不仅包括行动意义上的不作为,也指代一种不关注现时价值的眼光——虽然当下在“忙碌”,在“工作”,内心其实并不认可此景此事的意义,所以焦虑状态无可缓解。去年年末,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在名为“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的讲座上,阐述了国人一种普遍的“悬浮”心态——当人们仅仅把现在所做的事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时,“当下”就被悬空了。他列举了一些亲身观察与体验到的例子来印证这一点。比如1994年在东莞进行田野调查时,他了解到很多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并无体认,他们的思维是“赶快跳槽、赶快赚钱,积蓄尽量多的钱,以后不用再当民工”,在这样的心态下,工人们团结起来改变工人境遇与工厂管理方式只能是一种天真的臆想。知识分子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许多大学教师明知道自己的研究没什么意思,却不得不完成发表任务,一边忙忙碌碌,一边认为自己毫无作为,并安慰自己:“等五年之后,再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现在先不要问太多问题。”

在项飚看来,这种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未来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未来是有追求的,而是人们首先认为当下没有意义,然后告诉自己,当下所做是为了未来。人们对于模糊未来的想象势必包括更多的收入、更加优渥的生活条件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对于“当下无价值”的判断则是焦虑心态与“线性进步”意识形态的延异结果。他继而指出,“悬浮”心态与一种线性的历史想象密切相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进步”是存在的意义来源,人们的竞争意识活跃,担忧自己如果不朝向世俗定义的“成功”进发,就会惨遭落下。
狭隘的未来想象使得历史进步变成了纯粹的物质改善,对于应然幸福生活单一扁平的判断维度使得人们感受不到“正所为”的价值,在认知层面经受“无为且焦虑”的折磨。
由此可见,除了将人们变成竭力经营自我的“焦虑经纪人”,理想/幸福叙事设立的明确框架也为人们提供了“不作为”的选项,它既是行动的替代物也是思考的替代物,一方面填补了具体可感的生活空缺,另一方面也省去了人们为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所需做出的意志努力。
这并非完全否认幸福叙事的积极意义,它或许是多年来人类探索“如何获取幸福感”的智慧成果,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对于特定角色的公共期待也拥有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其合理性是需要被持续考察的。任何一种流行的叙事都应被视作一种观点,理想的效果是引人深究,而非通过构成一种人为的强制同意来创造表面的幻觉。
个人如何对幸福叙事进行辩证抵抗?Paul Dolan在其关于“幸福科学”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设计出来的幸福》(Happiness by Design: Change What You Do, Not How You Think)中给出了他的建议:“更多地倾听你真正的幸福感,而不是你对你认为或应该如何快乐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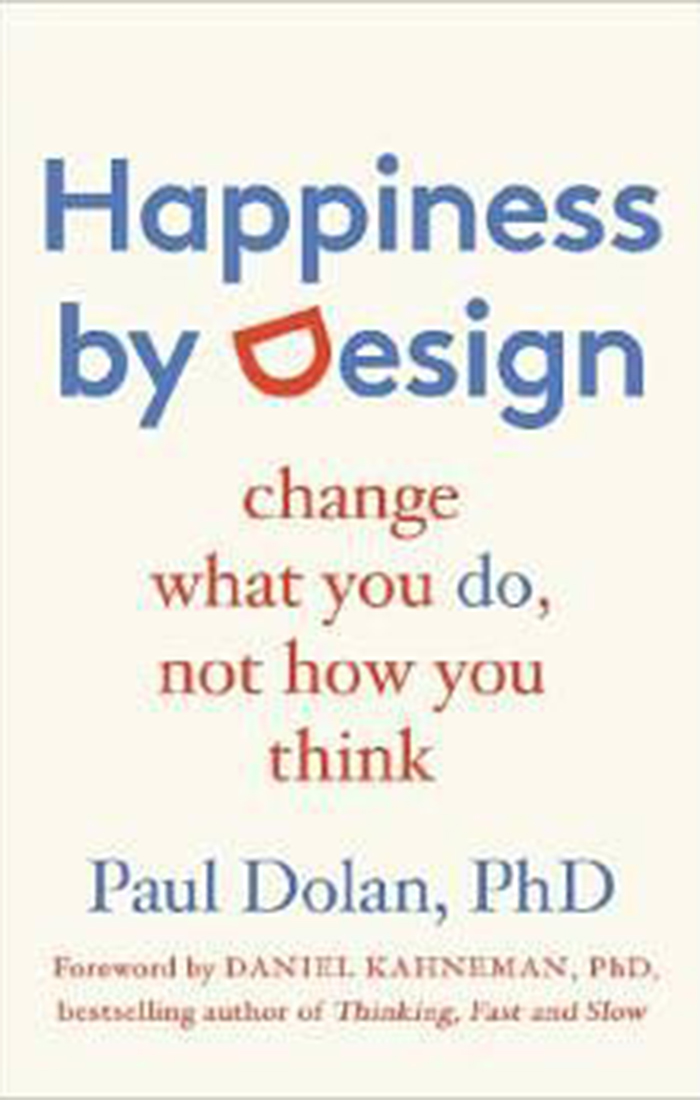
Paul Dolan
Hudson Street Press 2014-8
而在后续的《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完美生活的神话》一书中,他调整了单纯强调个体的视角,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其中:“我们需要自己决定以尽可能减少痛苦的方式过我们的生活,并得体地为我们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负责,”同时也“对那些抛弃不适合他们的社会叙事的人表示尊重”。这看上去似乎又是以自我消解的方式对待不公与偏见,但作为一种思考路径,在当前的社会阶段或许也有一定的价值。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