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跟这只阿根廷蚂蚁打个招呼吧。它是一个不起眼的家伙,真的不过是只蚂蚁罢了。在基因层面,我们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但美国生物学家、蚂蚁摄影家马克·墨菲特(Mark Moffett)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蚂蚁和人类十分相像,连我们的表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难以企及。他说,这个物种“代表了社会进化的顶峰”。
像许多其他的蚁群一样,阿根廷蚂蚁的社会秩序极为复杂,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和人类社会如出一辙。同时,他们还会用气味来做标记,由此区分外来殖民者。我们的发型、文身不也是类似的标记吗——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东西,这一点先搁置一旁,稍后再谈。不过,最能拉近我们和蚂蚁之间联系的两样东西,就是战争和殖民的野心了。我们一股脑前仆后继,在这一点上和蚂蚁并无二致。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阿根廷蚂蚁的社会由许多分离的“超级殖民地”组成,几百万只小蚂蚁走到一起,形成了强大的聚合,能占据好几平方英里的领地。而今天,我们发现,如果这样的蚁群不受邻近殖民地的影响,便会发展成横跨大陆的巨型殖民地。墨菲特说,假设他在旧金山见到一只蚂蚁,然后一路南下八百公里来到墨西哥边境并“把它放下,这只小东西还是会活得好好的”。
然而,她要是被扔在了加州其他三个巨型殖民地的领土里就没那么好运了,估计只有死路一条。在不同殖民地的边界,有的只是一战般恐怖而无谓的征伐:“一个又一个月,边境前线如漂浮的冰盖般移动,一会儿向这边推进几米,不久又被怼了回去。”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敌人”身上不同的气味。
撇开别的不说,《像人一般的蚂蚁》(The Human Swarm)首先就是一本奇观之书。密密匝匝关于阿根廷蚂蚁的故事瀑布般倾泻而出,起初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到底想说什么?除此之外,墨菲特骨子里的反叛也展露无遗。其他学者对于社会的观点被他批得千疮百孔,就连著名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没能幸免。戴蒙德的作品《崩溃》被他称作“变化莫测的社会里几个极端的例子”,迅速扔到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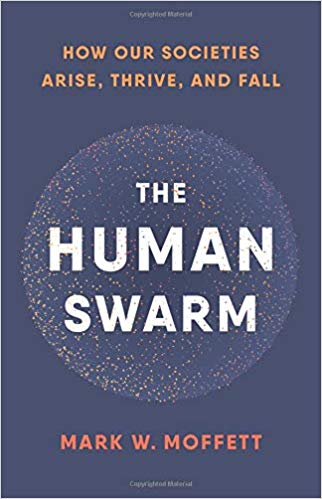
贯穿全书,墨菲特都在调侃。在书的开头,他说,“先神秘地偷瞄一眼结论吧:黑猩猩需要了解所有人。蚂蚁一个人都不需要知道。人类只需要认识某些人。”

言下之意是什么?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社会在人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试想,当你走进一间咖啡馆,身边环绕的都是陌生人,但你并不会去威胁他们,更不会拳脚相对,这正是“我们这个物种最缺乏重视的一个成就之一”。对许多其他的脊椎动物来说,除非他们认识咖啡馆里的每个人,才会安心点一杯拿铁。而阿根廷蚂蚁呢,如果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味道,他们就会坐下喝一杯。只有人类能在完全陌生的个体面前放松,因为这正是我们社会运作的方式,同时这也是我们架构历史的基石。正如墨菲特所说:“能够在不熟悉的社会成员之间泰然自若,从一开始就让人类受益无穷,也让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
对这种社会形式的需求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类经验。人们大可以说,我们用来区分社会的各种形式,无论是宗教、政治、道德,还是国旗国歌,都是偶然的、非理性而不真实的。话是不错,但要是没了这些标记,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人类走进咖啡厅,感到安全,全凭想象。墨菲特引用了哲学家罗斯·普尔(Ross Poole)的一句话:“每个人想象中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大家都在想象同一个国家。”
和蚂蚁一样,我们也需要标记,但仅凭这些标记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社会还要能接受“社会控制欲领导,需要越来越坚定地信奉专业化,比如说职业分工和各色社会群体”。
墨菲特的理论不无争议,其中隐含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时,永远都会是外邦人,不可逆转。在墨菲特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真正融入周遭的世界。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浸没在社会的风俗人情和道德文化中。到了成年时期,这些社会给予我们的身份已经成了一种绝对值。作为外人,我们能够成长发展,但归根结底我们仍然不是自己人。

相信流动身份的当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太晦暗,不讨人喜欢,因为他们认为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社会中无摩擦地浮动。不过大家还应该记住,墨菲特的理论还有另一面:人类社会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吸收外人的能力。要是丢了这个能力,我们到现在依然生活在小团体或是部落中。人类和蚂蚁一样,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物种。蚂蚁通过繁殖“自己人”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我们则是通过拥抱他人。
第二层含义是,普世的人类社会概念是没有希望的。墨菲特说:“世界主义的概念,即世界各地的人能感受到人类这个物种之间存在主要联系,这样的想法就是个白日梦。”
诞生出一个崭新、统一的人类世界的想法,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只能停留于幻想。原因在于,这样的世界不能满足人类定义自我的需要。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永远需要“他人”的继续存在,这个“他们”可以是反叛的,可以是野蛮的,或者只要与我们不同就够了,我们需要“别人”作为镜子,从而了解自己。墨菲特引用了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等待野蛮人》中的一句话:“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那些人,曾经也是一种解答。”
很显然,我们对他者的需要可能是灾难性的。外人常常会成为人类宣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靶子,有时要是稍加政治手段,可能会带来爆炸性后果。看看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就知道了,当时胡图人杀死了近一百万图西族人,其中许多干戈相见的人曾经都是邻人好友。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着“与看似不相容的人建立联系的能力”,但实效如何还有待观察。联合国和欧盟等机构都在努力实现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但墨菲特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不能给与社会成员一个真实的身份。”他认为,欧盟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人们认为可以借此对抗外部威胁。然而归根结底,欧盟永远不能让将其成员国聚合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到这里你也许会说,不同社会在人们的想象中也许是绝对的,这的确不假,但就像世上的所有事一样,这种想象起起落落。我们都应该像雪莱笔下的王中之王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一样,“功业盖物,强者折服/此外,荡然无物!”这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推入一种简单的相对主义中,而这种简化的对立恰是当代话语的默认方式。然而只要坦诚地内省,不难发现,这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成果。
最后,墨菲特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一种能力——“可以通过自我纠正来对抗我们与生俱来的冲突倾向。”这句话有其隐含的科学主义,也许就是这种科学主义,把这位作者带回了传统的当代主流思想上,而这正是他孜孜不倦想要偏离的。同时,这也是对某个社会、某个时代想象世界的一种表达——对一些人来说是绝对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就是陌生的。然而历经这一系列搅动不息、令人着迷的思想冲撞之后,我想他最终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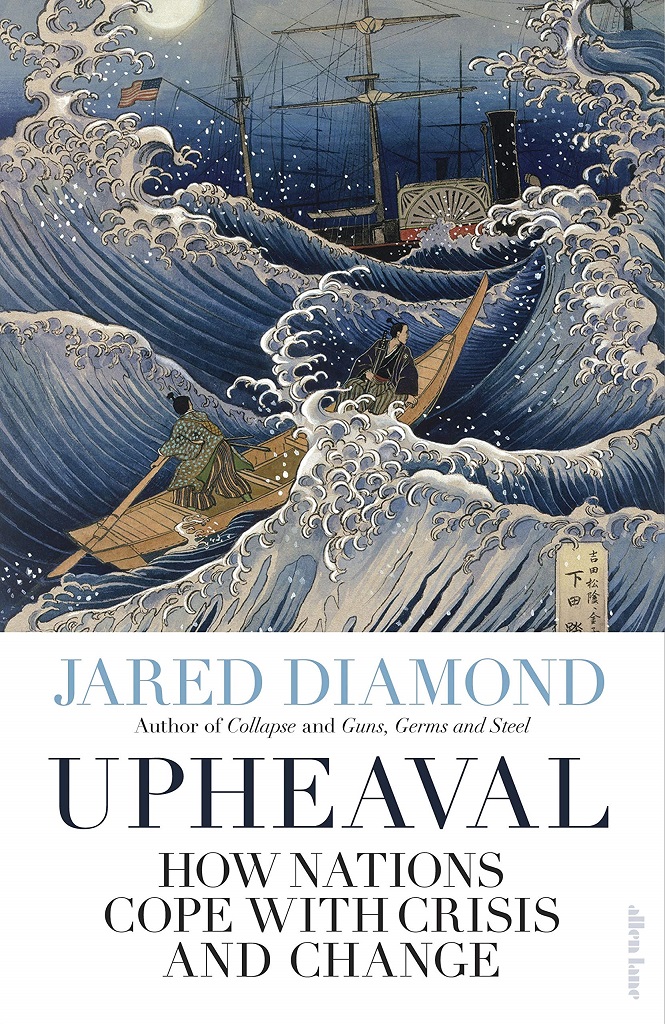
贾雷德·戴蒙德的《巨变》(Upheaval)则全然不同。墨菲特的文字张扬,戴蒙德则沉稳紧绷;墨菲特独辟蹊径,戴蒙德则一直走在主流大道上。戴蒙德已经81岁了。旧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让他声名鹊起,成为了世界一等一的学者以及家喻户晓的公知。但我个人认为,《巨变》这本书相较之下恐怕就有仓促写就之嫌,他的理论还略显踌躇,似乎仍在起步试探阶段,没能在他现有的作品之上增添多少亮点。
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序言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戴蒙德说,他并没有采用定量研究这种基本的统计学方法,而这本书讨论的课题“依然有待将来的细分研究”。与此同时,这本书只给出了一些可供定量分析的“假设和变量”。
戴蒙德枚举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人危机,并将其与国家层面的危机联系起来,他分析了二战期间与苏联交战过后的芬兰、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统治后政治遗产残存的智利、十九世纪外来特权支配下的日本、苏哈托屠杀过后的印度尼西亚、战后重建的德国以及摸索后殖民时代国族身份的澳大利亚和美国——而这些无一不是他熟悉,而且大多都是他通晓其语言的国家。通过这些案例,他试探性地提出了走出危机的办法。
国家与个人之间有许多明确的相似之处。他写道:“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想要成功应对,都需要进行有选择性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国家与个人都一样。”他列出了与个人危机相关的12个因素,包括成人危机、寻求帮助、诚实的自我评估等等。随后他也列举了与之相对的国家危机的影响要素,其中大概有七个点是相同的,其余五个则有着至关重要而且非常显著的差异——比如说社会与经济制度,当我们个人精神崩溃的时候,总不能把这一点作为解决方法吧。
他的所有论证都井井有条,但却略显奇怪。不过戴蒙德选取的这几个国家的历史叙述都非常吸引人,而且信息量庞大。他以自己独特而优美的语言、微妙的文字,捕捉了芬兰在危机中的古怪之处,描述出长久以来苏联在两国陆地边界对芬兰人施加的威胁。
不过在我看来,戴蒙德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美国,他用了整整两个章节预测美国的未来。他瞥见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国家也许会因让位于独裁统治的政治妥协而走向智利式崩溃。“我预见,美国国家政府或是州政府中,某个政党的权力会逐渐扩张,越来越深入地操纵选票,在法院安插与自己裙带相连的法官,让他们来挑战选举结果,然后以‘执法’为由,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或者是出动军队来镇压政治反对派。”
不平等会增加危机的风险,而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糟糕得多。戴蒙德自问,美国什么时候能正眼看一看这个问题,答案是:“当腰缠万贯、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其他大多数的美国人依然愤怒、依然挫败、没有希望,那么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这个国家便会认真对待了。
对我来说,这种焦虑正是联系墨菲特和戴蒙德的纽带。两本书都在努力寻找抵御混乱、暴政及崩溃的方式——戴蒙德通过身心治疗手段,墨菲特则着眼人类学。而二者都不该被泛化理解成一个简单的观点,这其实是迫切而具有话题性的需求。我们的世界似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民主国家的失败、极端政治、分裂言论和裙带资本主义——而这两位作家都大胆站出来,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戴蒙德更加明确,而墨菲特则比较含蓄,要求人们认真对待这个社会——这个暂时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一旦离开便无法忍受的社会。两人都没能给出答案,但至少他们都给我们给我们下了指令:坐起身,注意。这样看来,奥兹曼迪亚斯这位王中之王,应该是两本书都读过了。
本文作者Bryan Appleyard是一名英国记者和作家,作品包括《贝德福德公园》《如何长生不死或英年早逝》。
(翻译:马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