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可以说绝大部分犹太人对民族国家都心有存疑。在他们眼里,自己正是民族国家的二等公民,甚至是受害者。犹太人在当时所居住的民族国家中,往往很难获得合法身份,换句话说,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在他们看来,因为种族或者宗教原因,自己一直处于被流放的状态,被整个社会体制背弃。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忠诚寄托在别处——他们与神性的圣约关系中,也就是说,埋藏在这个孤立群体的深处。
大屠杀过后,一些犹太人看待自己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就成长在这个时代。作为婴儿潮的产物,我和这整代犹太人一样,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犹太身份。我和祖辈不同,自打出生,我就明明白白是个民族国家的公民。除了我的犹太身份,我还是一个被社会同化的美国公民,既虔诚地遵从教义,也与非犹太人通婚。在这个年代,一些资产阶级犹太人甚至成了保守的共和党人,或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1948年以色列建国,一个真正的犹太国出现了,犹太人掌握了主权。事实上,至少对那些重新安置在这片土地上的欧洲犹太人来说,这也许就是新犹太身份的最好代表,或者说是其高光时刻。在以色列,他们有了明确的公民身份。有趣的是,这些新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但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两部文集却不约而同地单单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古老的、基于大流散以及无国家状态产生的犹太身份。
《犹太人与理论的终点》(Jews and the Ends of Theory)肯定了大批犹太知识分子在人文学科的分量。编者沙伊·金斯伯格(Shai Ginsburg)在介绍章节中就抛出了这本书的中心问题:二十世纪理论中,“犹太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被框在了无国家身份、犹太大流散的刻板印象里。在这样的建构下,二战后的欧美社会在这里似乎一点影响都没有,以色列国也没能带来半点好处。在整本书里,耶胡达·申哈夫(Yehouda Shenhav)的文章算是谈论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笔墨最重的一篇了。透过“Nakba”(“灾难”,意指对1948年战争及人们被迫流亡的经历),他描绘了以色列建国的悲壮时刻——几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而在他们土地上新建立的这个国家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申哈夫在文中继续说,1948并没有给“Nakba”画上句号,以色列的“中东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受到的伤害从未间断,这种不平等同时也在侵蚀着国家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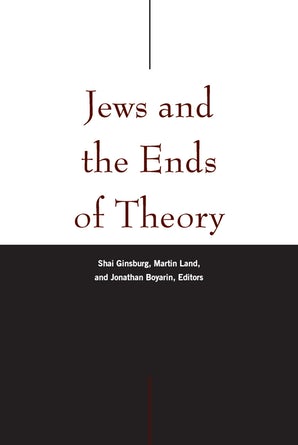
这本书中大多数章节都在讨论知识分子典范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他们有着怎样的不满,又是如何与社会脱节,以及这个群体曾有过怎样的历史性时刻。历史学教授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他的文章中则讲述了德国犹太社会学家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在1933年来到美国之前,是如何站在为取得德国公民身份而皈依基督教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边,又是如何加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efor Social Research)阵营的。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随后的几章里都是重头戏。安德鲁·布什(Andrew Bush)认为,德里达从小就是个被排除在外的异类,是一个成长在法国殖民地的没有归属的公民。他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他说的是法语,而不是塞法迪犹太人(祖籍伊比利半岛,遵从西班牙裔犹太人生活习惯的犹太人)所说的拉迪诺语(Ladino,又称犹太-西班牙语)。但与此同时,他对法语在情感上也十分疏远,德里达常常思考,在这门语言里,犹太人深层的含义也不过是接受着语言上热情款待的“客人”吧。莎拉·哈默施拉格(Sarah Hammerschlag)则在她的文章中分析了卡夫卡给父亲的信,以及犹太传统中的“Akedah”(“捆绑以撒,指”创世纪中献祭以撒的故事)。莎拉总结说,在德里达眼里,二者都是关于背叛的故事。杰伊·格勒(Jay Geller)的文章里也能隐约看到德里达的影子。反犹主义者用动物来比喻犹太人的野蛮化,剥除他们的人性,但另一方面,动物也让犹太作家更好地思考犹太人的处境。卡夫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将《变形记》中的主角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也让《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猿猴“红彼得”开口讲话,展示他作为“表演者”的一生。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从中我们认识了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犹太批评家维克多·斯克罗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和他的朋友,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很显然,斯克罗夫斯基认为犹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疏远与异化,而涉及到了一种自由,让他们燃起对颠覆故事的同情,重启人们的道德思考。埃里希·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绝对是这本书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作为一名德国犹太知识分子,上世纪30年代,他在土耳其过着流亡生活,就是在那里,他发现了“现实主义”,这一点和圣经中的《旧约》相照应。他总结说:“上帝的目的就是……犹太人在丰富而痛苦的历史偶然中的发现。”汉南·赫弗(Hannan Hever)的文章也十分吸引人,讲述了历史、神学家格什松·舍勒姆(GershomScholem)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世纪辩论。两人关于现代哈雷迪犹太教(犹太教正统派中最保守的一支)的看法截然相反。不过赫弗认为,其中更显著的分歧点在于错位的当代犹太人主权。《犹太人与理论的终点》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没有空间讨论,但上面我提到的几篇文章已经大体上覆盖了散居犹太人的边缘身份和焦虑。

另一本书和犹太人也有着扯不开的联系。《弗洛伊德与一神教:摩西及宗教的暴力起源》(Freud and Monotheism: Moses and the Violent Origins of Religion)收录了一系列文章,重读这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故事,他脑子里的怪东西,他提出的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愧疚与压抑感的理论,这些观点是否又能在他的犹太教和犹太人的身份中找到根源?逃离被纳粹占领的维也纳后,弗洛伊德在当时相对安全的伦敦住下,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日子,也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摩西与一神教》——尽管在许多研究正经的学者看来,这本书讲述的不过是伪历史,通篇都是空穴来风的猜想和站不住脚的分析——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个不严格遵守教义的犹太人,还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终其一生都对摩西无比着迷。在他看来,摩西不仅是一个被自己的人民背弃的先知,更是一个强大果敢的斗士和对抗着反犹太主义的异教徒。 加布里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和吉拉德·沙尔维特(Gilad Sharvit)则在各自的章节中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会对摩西产生这样的认同感,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位先知很显然是不愿意当个领导者的。在这位心理学家眼里,摩西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解放者、立法者和国父,更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的世俗宗教——或者是反犹主义者用来攻击他时所说的那样,“犹太科学”——当时也随着流亡的弗洛伊德奄奄一息。弗洛伊德无法来到应许之地,他既没能撑到自己最后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的出版,也没能看到精神分析学病毒般的影响力。

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离经叛道的主张:世上不止一个摩西,而是两个。第一个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贵族。以色列的奴隶置他于死地,但前提是他们已经皈依了一种严格的埃及一神教,然而当他们后来在荒漠漂泊的时候,深感愧疚。后来,第二个摩西走到了他们的面前,还是难逃一死,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接受了他的一神论,甚至是其严格的禁止制作圣像的教条,甚至连上帝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弗洛伊德继续论述,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背负着这两次谋杀的深重罪恶,并且因此顺从于他们限制严格的宗教。这时候诞生的新一神教是苛刻的,要求信徒放弃具体的感官、本能和物质世界。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他精彩的文章中写道,对弗洛伊德来说,犹太教,或者说是宗教从整体上讲,都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深深植根于人类原始杀父娶母情结那被压抑的情绪经验中。
《摩西与一神论》中还有几点贡献——借着这本书,我们还能一窥弗洛伊德是怎么看待犹太宗教与犹太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圣约,上帝给自己“选民”赐予的特权身份,会不会在增强犹太人自尊心的同时,也在排外的异教徒之间徒增了怨恨?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文章就把这一点拎出来理论。对弗洛伊德来说,对犹太人的暴力迫害可能会永远潜伏在社会之中,静候时机成熟,找到一个突破口便一触即发,向那些犹太少数群体开战,因为这些人否认他们的基督,他们的成功也不足以抹去身上的污点。也许对弗洛伊德来说,犹太教最具挑衅意味的一点就是禁止偶像崇拜以及“去除物质化”了。他们信仰一个无形的神,禁止任何描绘其形象的东西。这样一个超现实然而又隐蔽的空间,让犹太教的一种观点得以大展拳脚,批评“存在的现实”,并且与之保持距离。弗洛伊德不相信乌托邦,在他悲观主义的价值里,理性永远不会胜利,这样脱离社会、超然于现实的一个民族永远不会迎来和平。
这两本内容丰富的文集给广大读者展现了许多值得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其中有许多吸引人的观点值得借鉴。这些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影响力巨大但又不被社会所接纳的犹太作家——卡夫卡、肖来姆、巴布、德里达、奥尔巴哈,当然还有弗洛伊德——群星闪耀,通过文字折射出来,就如光明节(犹太节日)奇迹一样。这些文字字字珠玑,文采斐然,每一页我都愿意不吝笔墨,写下大堆大堆的脚注。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大屠杀后时代的犹太身份在两本书中完全是一片空白。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国籍——至少在欧美国家是如此——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不再是被疏远被孤立的外人,不再像从前一样令人费解,甚至有些惹人厌恶。我也曾经提到,这两本书中展现的犹太人身份与十九世纪流散状态下的犹太人身份并无太大差别,其实要是再往前推,也没有多大改变。当然人们也可以解释说,这说明了这些作品的作者和编辑们的观点,他们相信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事实上,美国和欧洲反犹主义的复活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这两本书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正因为此。
本文作者David Lipset在明尼苏达大学任人类学教授。
(翻译:马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