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地时间7月6日,在阿塞拜疆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列世界第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地处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距今有5300-4300年的历史。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馆员施昕更在其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现了良渚遗址。当时,人们认为良渚只是一个古代村庄。1986年,反山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令学界意识到良渚的重要文化地位,玉器也就此成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形象。在《国家宝藏》第一季中,浙江省博物馆选送的其中一件国宝,就是一块于反山墓地发掘的玉琮,其上刻有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纹样“神人兽面”图案。
2007年,考古人员发现良渚遗址上曾坐落着一座史前最大的古城,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良渚古城拥有王陵、宫殿、粮仓、祭坛、作坊、河道等一系列设施,外围则有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时期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同意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良渚文化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意义?良渚玉器如何从金石研究范畴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乃至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之一?良渚遗址考古如何一遍遍刷新学界对良渚文明的认知?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的“良渚文明”丛书中,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学者以及关注良渚遗址考古发现的媒体人撰文回答了上述问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若干片段,以飨读者。
遗址、文化、古城与文明:关于“良渚”的几个概念
文 | 朱雪菲

我们说“良渚”,想要人们铭记于心这中华五千年文明可视可触的直观印象。可到底什么是“良渚”?良渚古城是不是良渚王国?良渚文化又是不是良渚文明?“良渚”这么有名,但为什么重要发现都集聚在瓶窑镇?
理清了这几个概念,我们就会觉得“良渚”更加亲切了。
首先是“良渚遗址”。遗址是一个小概念,内涵分很多种,有可能是一个墓地,有可能是一个古村落,有可能是一个古战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通常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用当地的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山头、一条河或附近某个标志性建筑的名称来命名。让人很容易的就能知道这个遗址大概在什么位置。良渚遗址是良渚镇上一批史前遗址的统称,就是以良渚镇来命名的。当时的西湖博物馆有一位有心人。这位叫施昕更的职员,于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镇一带,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良渚遗址。具体到每一个遗址上,还有一个更小的地名,比如棋盘坟、横圩里、钟家村等。
然后是“良渚文化”。这里的“文化”,和我们平时说一个人有文化、有学识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是考古学上的概念,特指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群具有特点的由人类活动创造的物质文化的总合。当考古学发现,在某个地区,集中、频繁地出土一些具有同类物质文化面貌的遗址时,通常会以首个发现地的名称来命名这种考古学文化。这个地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大的。比如良渚文化,所涵盖的地区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长江下游,又以太湖流域的遗址点分布最为密集。我们对它年代的认识,是距今5300—4300年,如果按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代来算,良渚文化比夏更早。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原始,水稻种植农业和手工业都已经相当发达。日常生活用具以陶器和石器为主,而制玉与雕刻工艺、漆器工艺、大小木作工艺等,均已达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地步。由各处大大小小的墓地显示出的随葬品等级来看,良渚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
然后,来说“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众多遗址中的一个遗址,就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104国道以北。这个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遗址群”,是由许许多多被逐渐发现并认识的遗址点组成的整体,它有城墙、城门,有护城河,有宫殿区,有墓葬区,有手工业作坊区,有外郭城……它的性质不是一个单一的墓地或居址,而是很多不同功能遗址的聚合,呈现出一个古城的形制。称之为“良渚古城”,并不是说它位于良渚,而是因为整个古城的文化属性是良渚文化。
在良渚古城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概念——“良渚王国”。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概念,使得良渚文化升级为一个处于集权统治下的国家。当然,目前还不能够论证,若以良渚古城为国都,这个王国的直接统治范围有多大。我们可以比照一下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当时的一个国家甚至还不如我们今天的一个省。包括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面积都非常的有限。因此,良渚王国是政权组织形式的一种形态,它以古城为都。反之,正是因为具有都城性质的“古城”的发现,才促成了“良渚王国”这一早期国家概念的诞生。
有了古城,有了王国,“文明”的提法才有所凭据。这里的“文明”,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创建卫生文明城市”的“文明”,而是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个社会有没有进入“文明”,国际上是有一系列标准的。比如出现城市和等级社会,开始使用文字、青铜器,出现复杂的礼仪建筑等等。这些标准是国外考古界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情况进行归纳得出的结果,我们也照搬使用了很多年,却成为了对我们自身文明形态特征认识的阻力。“良渚古城”的发现,则打破了文明探源的瓶颈。它的城市规制、社会等级、权力分配、分工体系、组织管理和统一信仰,在玉质礼器的制作、城墙和高台的堆筑、水利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良渚古城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发展高度,可以认为进入了文明。这就有了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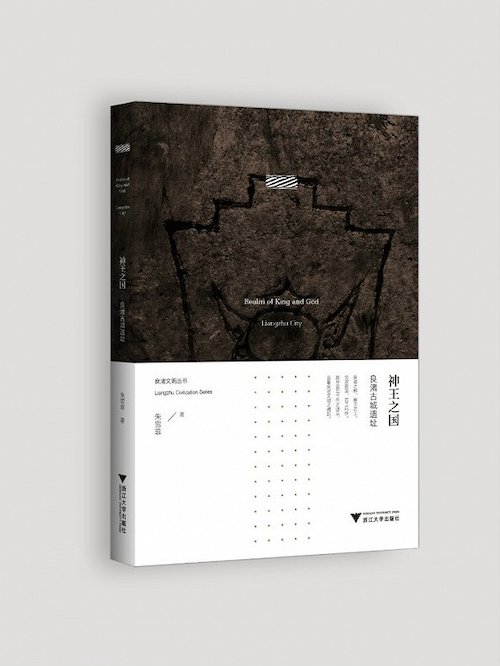
朱雪菲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从金石学到考古学:良渚玉器的出土、传世与研究
文 | 刘斌
由于乾隆皇帝喜好古物,所以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古玉。其中有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三叉形器等玉器。乾隆皇帝还常常为新获得的玉器赋诗作文。从其诗文的内容看,玉琮当时被认作是古代扛夫抬举辇车或乐鼓所用的“杠头”装饰。乾隆皇帝的收藏反映了近代良渚玉器的出土情况。
良渚玉器的出土与传世,几千年来未曾间断。最早也许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的古蜀国。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从形制与雕工看,无疑是4000多年前良渚人的作品。这也许是古蜀国传承千年的传家宝,也许是殷商时期新获得的一件宝物,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忘记它所代表的神性,因此模仿制作了许多风格相似的玉琮。
至西周以后,世人逐渐不识良渚玉琮的本来面目与意义了。江苏吴县严山春秋时代的窖藏中发现,良渚玉琮被当成了可以再利用的玉料,重新被加工和切割,可见在当时,这些良渚玉器并未被当作古物而加以珍藏。因此良渚人发明的玉琮的神性内涵至此已经失传。
但是中国人对玉的情有独钟却并没有间断,对于玉器的研究更是由来已久。早在近代考古学用物质标准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以前,中国东汉时期的袁康就有了类似的划分,他在《越绝书》中记载了战国时代风胡子对楚王说的一段话。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袁康的划分与近代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所划分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江苏吴县严山窖藏作为玉料切割的良渚高阶段及顺序十分吻合。就中国考古所揭示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不仅符合这样的发展顺序和对应年代,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也确实存在广泛的用玉现象,存在一个以玉为兵,以玉为礼的时代。
中国的金石学兴起于宋代,以证经补史为目的,因此,金石学十分重视碑刻和青铜器等有文字的古物的搜集与考证。在金石学的著作中,关于玉器的研究,一直属于次要的地位。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仅选录了圭、璧等14件玉器。南宋的《续考古图》略有增补。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可以说标志着古玉研究在金石学中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
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可谓古玉研究中最为杰出和集大成者。正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言,“好古之士,往往详于金石而略于玉,为其无文字可考耶”,“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古玉图考》在玉器的考据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而且配有相当精确的绘图,大多数的图上还注明比例、尺寸、颜色等内容。这为我们将古文献中所描绘的玉器与实物相对应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在《古玉图考》中,有收录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良渚文化的玉琮,这是第一次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玉琮归属到了具体的实物。经吴大澂考证,才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原来这正是古代经籍中所称的“琮”。虽然良渚玉器在当时还被认作是周汉之器,但就玉琮本身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学术考证,这应该是第一次。
南宋时期有青瓷琮式瓶和石质琮式瓶,外方内圆,四面有竖槽和突起的横条装饰,显然是模仿了良渚玉琮的形态特征。这间接地说明了良渚文化玉器在宋代就曾出土过,并成为人们喜爱的珍玩。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揭开了良渚文化考古的序幕。施昕更先生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也向我们透露出了20 世纪初浙江的盗墓之风。报告中称:“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而玉器所得不易,价值至巨,且赝品充斥,不可不注意,杭县的玉器,据善于掘玉者的经验,及出土时的情形看来,都是墓葬物,可无疑问,而墓葬的地方,无棺椁砖类之发现,据掘玉者以斩砂土及朱红土为标志,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竟达百余件……”从此可知良渚盗墓者对古墓埋藏特点的熟悉程度,良渚玉器的出土与流失也可见一斑。施昕更先生虽然断定玉器为墓葬中随葬之物,但也未敢确定其与黑陶处于同样的年代,而是将其认作是商周之物。
另据卫聚贤在《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1 卷第3 期)中所记,杭嘉湖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曾有多次古玉出土的线索。据记载,杭县安溪有一姓洪的农民,在清末曾掘到几担古玉。1930年,苏嘉公路桥北端曾出土一批古玉。1937年,在嘉兴双桥发现玉璧90余件。张天方先生在《浙西古迹》一文中也记录了嘉兴双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民国二十三年(1934)曾有两次玉器出土。依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古玉基本应属于良渚文化,可惜的是当时这些玉器大部分都流散到了海外。可见所谓“安溪土”和“嘉兴双桥土”之说是有其来历的。

刘斌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良渚遗址与中华文明:良渚遗址的发现意味着什么?
文 | 马黎
2016年,良渚遗址考古80周年,也是良渚古城发现10周年。良渚成了热词,有当“网红”的趋势。
比如11月,跟“良渚”两个字有关系的新闻事件,一连发生了好几桩。
2016年11月25日,由浙江省文物局、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承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开幕。全国34个省区市的考古文博单位、高校,近150名考古界大咖都来了——
84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83岁的良渚考古的开拓人牟永抗、73岁的考古学者王明达,钱江晚报《文脉》栏目曾经专访过的考古前辈,都在这个杭州寒潮忽降的日子里,赶到了现场。
在研讨会上压轴发言的严文明,提笔写下一句话 :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严先生对良渚情有独钟,他说 :“良渚太吸引人了,除了仰韶,良渚是我写得第二多的。”
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在官网公布《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的通知》,浙江有五处遗址成功入选,良渚位列其中。
11月初,翻开 2016年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在第一单元《史前时期 :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第 2 课《原始农耕生活》的知识拓展栏目,良渚文化被写入其中。2017年开始,这本教材在全国统一使用,全国 82% 左右(每年约 1400 万)的初中生使用本册教材,并从中了解、知晓“良渚文化”。
80年来,良渚一直在带给我们惊喜。
1936年12月1日—10日、12月26 日—30日、1937年3月8日—20日,24岁的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通过在此期间的调查,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湮没不彰的浙江古代文化,更得重要的物证。1938 年,施昕更在《良渚》报告中这样写道。
而这10年,从30万平方米的宫城到300万平方米的王城,从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再到 100 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它一次次刷新了学术界对良渚文化的固有认知,一步步实证了中国的五千年文明。
2016年4月,伦敦大学召开了关于水管理和世界文明的会议,对于良渚的水利系统,世界都很关注。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被远远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由于良渚这些年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世界考古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
发现在增多,而人们认识良渚文化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2016年11月25日的研讨会上,好几位考古学者都提到一个问题 :我们研究了80年,怎么向年轻人介绍良渚?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 ppt 上,放了一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照片,奖牌上镶的是玉璧。“到今天,国际上仍以圆璧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对良渚陶器上的旋纹做了解读,他鼓励大家“开脑洞”,比如把凤凰卫视的台标和良渚的旋纹摆在了一起。最后他还公布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让大家到自己微信公众号上了解更多良渚陶器上的美丽纹样。
现场响起了掌声。
说到这里,我刚好翻到80年前,施昕更亲笔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的一段文字。这位当时25岁的俊朗书生,仿佛早已有预知。
插播一句,对于这份报告的地位,在2015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考古学卷(第一分册)》中,有这样的描述 :是揭开江浙地区远古文化面纱的最经典的早期考古发掘报告。
“如果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我们需要广泛地在这未开辟的学术园地做扩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区域的遗址,不同文化的遗物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来建立正确的史观,这是考古学最大的目的。”
如果说,80年前,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是偶然,那么80年后,中国几代学人走到“圈子”之外,发现并确认良渚文明是堪比埃及文明的王国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则是良渚历史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

马黎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