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很多思想,也许大多数思想,都是邪恶的,或者虚幻的,又或者是既邪恶又虚幻的。”对于一本试图论证思想是历史前进驱动力的书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结论,“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环境,也不是经济或人口统计学,尽管这些因素对我们思想的形成都会产生影响。”如果思想驱动了历史,而大多数思想又都是邪恶的,正如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政治又会怎样呢?也许这是一种持怀疑态度的反乌托邦主义,对任何人类进步的大型方案都持怀疑态度。类似这样的思想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译注)的政治哲学,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没有提到。这种思想也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注)的政治哲学,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曾经提到过一次,但是没有将之与休谟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塞缪尔·约翰逊和大卫·休谟都是18世纪的保守派思想家,两人都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的时代,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思想如何转化成极其强大的力量。
这种持怀疑态度的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在发生革命的动荡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意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政治家和哲学家——译注)活着见证了法国的大革命,尽管当时他只是身处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但是他对事件的回应后来激发了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产生。在伯克看来,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对乌托邦的追求并非出自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信仰——具体地说,是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他确信,那些发生在法国的所有的无政府主义暴乱、恐怖镇压和严厉暴政实际上都具有某种救赎的意义。如果不是出自于信仰,历史就只不过是一系列由思想驱动的大变革,而且往往是灾难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不计其数的小变革,但全都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些似乎也是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的观点,然而似乎他并不愿意明确地表达出来。
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多部有关世界通史的原创著作。在《异想天开》(Out of Our Minds)的开篇部分他就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用科学术语来解释,想象力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另一种则可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将其描述为“一种非物质的能力,通常被称为思维或理性的灵魂。这种能力为人类所特有,或者说,人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有这种能力。”他告诉我们,想象力正是“人类思维的特别之处”,涵盖了“幻想、创新和创造力,可以重塑旧思想,也可以产生新思想,是所有灵感和顿悟的果实。想象力是一个巨大而且让人望而生畏的词,但它是与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现实相对应的:它是一种能够看见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例如写于2001年的《文明》(Civilizations)、写于2003年的《思想》(Ideas)、以及写于2007年的《世界:一段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中,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从生物群落或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是生物的社群而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地理学的视角使一些读者将他视为一位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一直认为人类的思想完全是原始本初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而且他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想象力的历史。
这本书内容丰富,而且有大量吸引人的有趣细节,但要对其做出公正的评价却不容易。如果说这是一本研究人类思想的书,那么书中每隔一页就有一种思想被记录下来。例如,在评价霍布斯(Hobbes,指托马斯·霍布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译注)关于人类如何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生活的黯淡图景时,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写道:
也许早在智人出现以前就有过一个那样的时代,那时的生活“贫穷、糟糕、野蛮”,而且“人的寿命短暂”,因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觅食以维持生存,所以那时的原始人类没有闲暇时间可以进行推理论断等思维活动。但是在那之后的几十万年里,我们人类所有的祖先,据我们所知,都是相对清闲的觅食者,他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终日劳累不堪。远古祖先们留下的史前艺术品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证据。生活在大约7万年前的古人类留下了不少洞穴壁画等艺术品,在大约4万年前以及后来的时间里,这类艺术品和人类遗迹更加丰富,证明冰河世纪的原始人类能够通过再次想象将他们看到的事物重现出来。
我们那些靠狩猎和觅食为生的远古祖先远非霍布斯在他的早期启蒙哲学中描述的穷困潦倒的野蛮人。他们留下了明显的证据,证明了人类想象力所具有的力量,本书的作者也认为那是人类思维所具有的最为独特的力量。然而,尽管人类想象力的丰富程度在所有动物之中是独一无二的,但人类并不那么容易产生新的世界观。我们今天仍然遵循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在改变世界的能力方面,人类后来产生的思想理念也许只有十几种能够与耶稣基督死前大约六个世纪里出现的思想观念相匹敌。古代圣贤们的思想填平了逻辑和科学方面的沟壑,而这些知识我们至今仍然需要运用。他们提出了现在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关于人性的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办法,对这些办法我们时而采用,时而抛弃。”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也称拜火教,始于古代波斯,宣扬一神论,认为世界上存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永恒斗争——译注)或犹太教、耆那教(Jainism,公元前6世纪创立的印度非有神论宗教,反对正统的婆罗门教,以其禁欲主义而著称——译注)或佛教、儒家思想或道教,都可以追溯至那个时代于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之中孕育和发酵产生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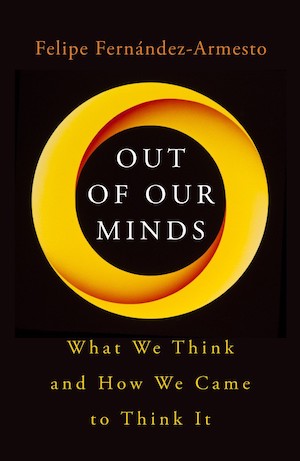
在今天的传教士信仰中,基督教思想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那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犹太拉比,他向世人传递激进的信息。”在耶稣基督之后,穆罕默德出现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传统基础上发展并产生的。“《古兰经》是真主安拉向穆罕默德耳语传授的启示录,上面的每一页都显示出犹太教(以及少量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
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认为,也许是一种比一神教(monotheism)更古老的思想成就了人类今天的主流思维方式。在古代印度产生过一种思想,认为世界可能就是一种幻觉。最早的古梵文奥义书(Upanishads,印度古代哲学典籍,主要探讨人与宇宙的关系——译注)中的一部《蒙达卡》,可以追溯到耶稣诞生前的第二个千年的后期,书中认为世界源于婆罗门(Brahman),就像火花从火焰中迸发出来一样。后来在柏拉图的神话和隐喻中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思想,将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认知与原始人类的洞穴壁画相比较:我们所感知的特定事物其实是空幻的,只有永恒而不可变的普世思想才是确切真实的。
费尔南多认为这种神秘主义的哲学观是现代科学的源头之一,这点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确实起始于某种类型的怀疑主义:例如对感觉的不信任。科学探索的目的在于穿透事物的表面现象,揭示其中潜在的真相。”现代科学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的经验主义思维传统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和激励。天主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学说“是欧洲中世纪巅峰时期发生的或许可以称为科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时期发生的甚至也可以称作是科学的革命或复兴运动”。在托马斯的神学理论中,上帝是受自然法则约束的,因此,对自然世界进行研究是一项宗教义务。由理性神学发展出的观点认为,科学其实是对宇宙中存在的理性秩序的发现。
在受到当今理性主义者推崇的思想史的漫画作品中,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被誉为欧洲中世纪“科学革命”的发起者之一。事实上,正如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所指出的那样,“牛顿其实是一个传统型的人物:他是一个老式守旧的人文主义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一个痴迷于宗教编年表的圣经学者——甚至,在他更狂野的幻想中,他是一个努力破解有系统的宇宙之秘密的魔法师,或者一个寻找魔法石(Philosopher’s Stone)的炼金术士。”牛顿不是第一次得到后人这样的评价,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篇题为《此人,牛顿》(Newton, the Man)的演讲词中写道:“牛顿并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Babylonian)和苏美尔人(Sumerian),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头脑,他以与那些近一万年前就开始建立我们现有的知识遗产的人完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可见的知识世界。”这次演讲原本定于1942年牛顿诞辰3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进行,但因二战的原因推迟了,后来在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由他的弟弟代为完成。

凯恩斯是第一个看过牛顿手稿的人,这些手稿在1936年被售出之前一直被秘密收藏,因此凯恩斯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他以上的说法。然而,这些说法并没有削弱或损害理性主义者对现代科学的看法,他们认为现代科学就是那一次“复兴运动“的产物——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一场反对神秘主义和魔法巫术,支持理性思考的运动。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异常苛刻,他说:“如果我想得出好的办法,我们应当把‘复兴’这个词从我们的历史词典中删除。这个词是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于1855年发明的,他希望通过人们看待和描绘世界的方式,来强调使古代学问、经典著作以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遗产得到复苏或‘重生’。”但是米什莱是从他自己的时代来看待过去,在他那个时代,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跟随米什莱的思想,我们被告知中世纪的那场复兴“推翻了经院哲学,开创了人文主义”,但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其实是由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发展而来。我们被灌输说那场复兴运动是世俗的或异教的,但是在整个复兴运动时期,这个词总是联系着“教会仍然是大多数艺术和学术活动的赞助者”。那场复兴运动的主流理念是由大批猛烈抨击中世纪主义和宗教的作家进行传播的,那种理念只是一种幻象,并不是历史现实。
在这本精彩刺激的书中,还有不少篇幅颠覆了人们对人类过去的已有认知。在书中,现代种族主义的异常之处被强调和突出。本书将种族主义与“对相异性的偏见”和“对狭隘的同类道德共同体的承诺”区别开来,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信条,即相信有些人由于属于一个具有种族遗传缺陷的群体而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低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就是“启蒙主义科学产生的一个意外的后果,因为那时的科学确实着迷于各种分类和测量”。
到了现代,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种族科学”与乌托邦想象混合在一起而得出的产物:“因此产生的第一批灭绝种族文化和种族大屠杀的行凶者,以及第一批大屠杀理论家,都是真正的激进乌托邦式空想家。”纳粹分子利用中世纪的千禧年主义思想(millenarian ideas,某些基督教派的信仰,笃信耶稣基督在新千年再临地球时会出现天堂一样的大一统太平盛世——译注)在他们发起的种族纯粹运动中妖魔化少数族裔,但他们也运用现代科学的权威来验证他们对和谐、种族平等的社会的幻想。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在推翻传统的史学诠释的时候能够提供更多的例证,而且他指出另一些诠释不仅更有趣,而且还可能更加真实。
这本书并非所有内容都坚实可信。在讲述单个思想家的章节中,有关弗洛伊德和尼采的章节就明显比较薄弱。但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的另一些论断却难以置信地强有力。“如果没有存在主义,”他写道,“数百万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将会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垮掉一代’的文化以及1960年代的宽容放任思潮(permissiveness)。同样的,20世纪后期反对社会规划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行动或许也无法得以实现。”但是如果认为放任思潮就意味着更多的性自由,那么应当归功于其他思想的出现,而且更应当归功于节育方法的改进。而自由意志主义者抗拒国家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数学在经济学中建立的声望,数学使人们相信了自由市场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形式的说法。存在主义则不在其中。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主张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如果存在主义确实对大众社会运动产生了影响,我们又如何得知?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思想究竟是什么?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体现的思想是哥特式建筑的思想理念吗?或者它所体现的是一位超验的神的思想?总之,我们何以得知?
在这一系列令人着迷的各种思想理念之中,最令人感到费解的是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是一种非物质的能力,他断言:“人类的智力很可能根本就是非机械性的:因为在像机器一样的人类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幽灵。”这一次也一样,他并不是第一个指出人类的思想也许不能完全用机械术语来进行解释的人。与达尔文一起提出现代进化论的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认为,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人类从一种非自然的资源中获得了更高的心智能力。在研究了动物的思想和情感之后,达尔文为拉塞尔·华莱士的设想感到震惊。达尔文感到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理论,华莱士的设想意味着必须将人类的思想能力纳入进化理论。正是科学的理念使达尔文认为,应该参考世上万物内部的自然发展进程来解释事物本身,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抗拒有神论。而至于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是否反对这种关于科学的理念我们尚不清楚。
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观察,人类的大多数思想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错误的,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观察结果加深了他的困惑。如果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具有看到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那么人类之所以具有破坏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不计其数的人为了追求梦想而丧命,众神、乌托邦、过去或未来的幻象,一切的一切都浮现在人类的想象之中。古代诺斯替主义者(Gnostics)认为,有一个邪恶的神或“造物主”(demiurge),将人类送去了一个由幽灵和幻想组成的更低级的世界,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在思考基督教教义的起源时讨论过这种思想。这是一个有趣的形而上学的推测。但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一种更加世俗的可能性,即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也许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人类思想的破坏力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合乎自然的解释。也许在像机器一样的人类身体里并没有幽灵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我们无法解开的杂乱交织的线路。
本文作者John Gray是《新政治家》的首席书评撰稿人。他的最新著作包括《木偶的灵魂:对人类自由的简短探问》( The Soul of the Marionette: A Short Enquiry into Human Freedom)和《七种无神论》(Seven Types of Atheism)。
(翻译:郑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