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能读懂这个句子(指英语原文),那你就可以和科学家对话了。虽然对话内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细节无关,但起码你俩共享同一门语言。如今,自然科学当中的沟通——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绝大部分是以英语来进行的;无论刊物、会议、电邮还是以Skype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机会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维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机构大楼,那就更能明白这一点。可以说,当今的科学就是说英语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科学只说一种语言(monoglot):每个人都说英语,其它语言几乎被排斥殆尽。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里的绝大多数至少都懂一些英语,但他们也会以法语和德语来阅读、写作和发言,有时还有别的“小语种”,譬如方兴未艾的俄语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语。
现代科学一度具有多语言共存(ployglot)的特点,这或许会令人有些惊讶。只说一种语言难道不会更高效吗?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学习三种语言的读写,那会浪费掉多少时间!如果每个人都操同一门语言,源自翻译的隔阂就会更少——譬如,若有多种语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结论,便会产生谁最先有此发现的争论——而教学上的浪费也较轻。根据这种观点,当今的科学之所以进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我们聚焦于“科学本身”而非诸如语言之类的表面功夫。
假如讲者是说英语长大的,此论就显得更加有理有据了,但如今活跃在一线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考虑到他们学语言所花费的时间,征服英语未必比容许多语言的科学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种低效。语言学习和翻译依旧在大举进行当中,且并不仅仅在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交流中的障碍是减少了,但远远谈不上顺畅和精准。
如今的科学家仍旧彻底被英语包围,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缩短了对学科的记忆。科学总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它以前不是这样,但只有年龄很大的科学家才能记起以前是何等样貌。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一般认为,西方科学在其开端上由希腊语统治,并呈现为拉丁语取代希腊语、法语取代拉丁语、德语取代法语再到英语取代德语这一进程。将科学史理解为不同的单一语言接连占据主导地位的链条式演进,表面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这并不正确,也从来不会正确。
宽泛地讲,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科学里有两套基本的语言体系:多语种共存和单一语种。后者是新近才有的现象,它不过发端于1920年代,仅仅到了1970年代就战胜了历史悠久的多语种共存体系。现在的科学的确说英语,但在多语种体系里长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这一重要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纪的西欧,自然哲学和自然史——这两大领域就是19世纪所称的“科学”——从根本上讲都是多语言的事业。此论的确不假,虽然中世纪盛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语言都是拉丁语。
拉丁语的特殊地位和多语言共存的体系并不矛盾;相反,它认肯了这一体系。任何一个靠谱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或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都知道,以拉丁语为正宗的自然哲学可以追溯到全盛时期的罗马。(西塞罗和塞涅卡在这一领域都有重要作品)。但这群人文学者和经院学者也知道一点,那就是从古典时代一直到罗马末期,学术语言乃是希腊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因亚历山大的征战而有过一阵东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称“希腊化时期”,希腊化了的希腊语已不同于上古希腊语——译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他们还知道,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自然哲学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语而非任何一门古典语言写成。将自然哲学经典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文,对西方学术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稍有学养的人都明白,学习乃是一项多语言的事业。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见的、父母特别奇葩的怪人(蒙田就这样自诩),没人会把拉丁语当成第一语言,且很少有口头的运用。拉丁语乃是用于书面学术的,但每个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都将它与其它的语言混用,例如与仆人、家庭成员和恩主沟通的语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语是一种工具性的语言,起到联结不同的语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认为大致是中性的。确切地讲,它凸显了阶级差异,毕竟学习它需要专门的教育,但它能轻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经常用拉丁语(且经常比天主教徒还要文雅),至18世纪,它甚至还被引入了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成为其新建立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学术语言。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由于拉丁语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全欧洲和阿拉伯范围内的学者都可以平等地运用它,这门语言并不“专属于”谁。基于这些理由,拉丁语成为了探讨普遍自然的适当工具。但对话的参与者也都是操多门语言的,在其中选一门适合于听众的即可。在面向国际上的化学家写作时,瑞典人会使用拉丁语;当与矿业工程师交流时,他们又较多使用瑞典语。
这一体系在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里开始崩溃,而崩溃也是这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伽利略于1610年在拉丁语写成的《星际信使》一书里公布了他发现的木星卫星,但其晚期的主要作品则以意大利语完成。为了在更加本土化的听众那里寻求赞助和支持,他会相应地切换语言。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拉丁语写成,但1704年的《光学》却是英语著作(拉丁文译本于170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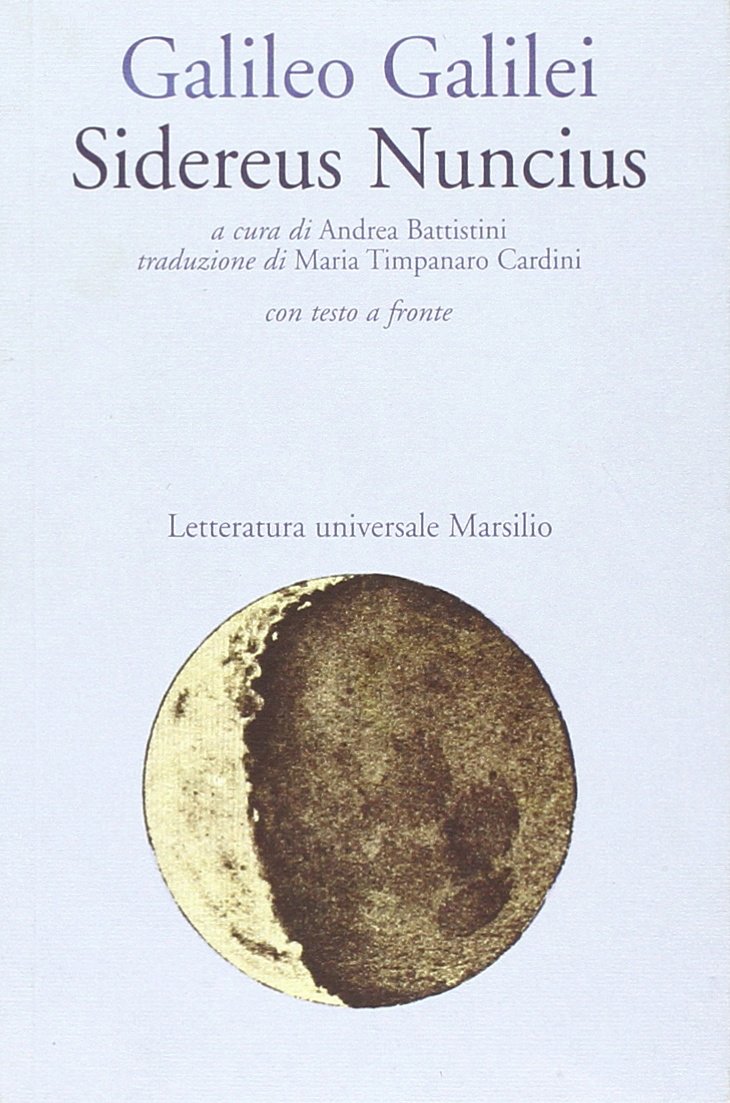
在欧洲,学者们开始使用一种多语言的大杂烩,拉丁语和法语译著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学术交流。到18世纪末,以英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化学、物理学、生理学和植物学论著日益增多,但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及其它语言的著作也有一席之地。直到19世纪的前30年里,许多教养良好的精英阶层仍青睐拉丁语。(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学术笔记使用的就是和尤利乌斯·恺撒相同的语言,至少在1810年代如此。)可见,现代科学在其开端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多语种大杂烩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
人们一般不假思索地认为考虑效率是一件好事,再加上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历史悠久的多语种共存体系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许多语言被认为是无用功,为了阅读自然哲学的最新进展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语言上,那你就没法做任何研究了。1850年前后,科学语言的范围开始缩小到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三门,它们在学术出产上大致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虽然比例也会因学科而异:19世纪末,化学的主要语言是德语)。
与工业化的勃兴相伴随的,是席卷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由诗人和知识分子培植乃至于精心编纂过的本土语言成了19世纪现代性的载体。这群语言卫士需要克服困难,设法转化粗鄙的市井口语,使之符合高雅文学和自然科学的需求。相关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现代匈牙利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希伯来、波兰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文学都是19世纪后半期才发展起来的。然而,科学中对效率的推崇在某种意义上压制了这座新生的巴别塔,只有俄语成功突围,成为了科学出版的重要(哪怕地位不那么显赫)语言之一。“小语种”的拥护者经常抱怨这种排斥,而英德法三大语言的使用者则对自己还必须另学两门(指英德法里的任意两种)语言颇有微词。
毫无疑问,三语并立是一种负担。有人主张科学训练应只使用一门语言,并专门强调了之前拉丁语的普遍性及广为接受的中立性。他们呼唤世界语(Esperanto),同时也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论证,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论证被用来支持英语。甚至还有一小群社会贤达为世界语背书,例如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和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贝尔森(Otto Jespersen),但他们很快就被斥为乌托邦空想家,虽然他们的热情后来演变为了更加极端的人工语言计划。显而易见,人们大都认为科学乃是一项多语种共存的事业,否则它便无法存在。

某些东西显然发生了变化。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世界语支持者梦寐以求的世界,但自然科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它是某些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母语,从结果上讲也完全谈不上中立。科学的多语种共存体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崩溃了。更准确地说,它被摧毁了。1914年夏天,同盟国(原则上指德国和奥匈帝国)和协约国(英法俄三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当其冲的“伤者”便是一种好心的国际主义(beneficent internationalism)理想。德国科学家与其它科学家一道加入了对德国战争目标的歌颂当中,法国与英国科学家则作壁上观。
战后,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即今天的国际科学理事会——译注)在协约国胜利的庇护下成立——当时它接纳美国但却排斥了俄国,后者随后又陷入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漩涡中——并发起了抵制同盟国科学家的运动。1920年代新成立的诸多国际性科学机构都对来自战败国的、说德语的科学家紧闭大门。这一排斥之举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线,令德语在未来几十年中渐渐丧失了作为顶尖科学语言的地位。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三语并立变成了两语并立。德国人回应此困境的方式,则是复兴其对本土语言的忠诚。多语言体系的崩溃就此开始,但最终为之敲响丧钟的乃是美国人。
1917年4月,美国加入一战,随之而来的恐德情绪使得德国成了罪人。艾奥瓦、俄亥俄、内布拉斯加等州取消了德语的地位,截至当时,它在美国是除了英语之外第二常用的口头语言(此为吸收大量中欧移民的后果)。停战后,禁止德语的做法反倒更加风行。到1923年,有一半的州都限制了德语在公共场合、电报、电话连线以及儿童教育当中的使用。
同年,最高法院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中推翻了这些法规,但损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外语教育几近全毁,法语和西班牙语也受到波及,整整一代美国人以及未来的科学家都在一种基本不接触外语的环境里长大。1920年代中期,当德国和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发表了新的量子力学研究成果时,美国的物理学家是唯一能读懂德语论文的群体了,因为他们仍会跨过大西洋去魏玛德国进行硕博士层次的学习,也就必定学过德语。
出国的方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一股脑地开除了“非雅利安”和左倾的教授,德国科学受到严重打击。有幸能在1930年代移民的犹太人科学家面临着许多挑战。曾担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助手的科奈利乌斯·兰佐斯(Cornelius Lanczos)在英语发表上陷入了困难,这既与他的课题有关,也源于“人所共知的‘坏语言’借口”,哪怕他“提交的文本经过好友的全盘润色”也未能改变这一结果。爱因斯坦本人甚至也要依赖翻译和合作者。
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朗克(James Franck)来到芝加哥,并逐渐适应了英语,而马克斯·波恩(Max Born)则在爱丁堡定居,拾起了他在少年时代曾饶有兴趣学习过的英语。诸如此类的许多名人都曾经谈到过自己与新语言较劲的经历,就像今天的日本诺奖得主在自传里所强调的那样,第一篇英文论文的发表对其在日本之外确立其研究成果及风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回到1930年代,希特勒也取消了大部分外国学生的签证。限制赴德留学,意味着对德语的进一步扼杀,可谓是一战以来德语在科学中的消亡进程里的最后一击。

二战结束后,上述进程的主导因素开始偏向于人口学及地缘政治。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扩张对多语种共存仍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出身和崛起于20世纪美帝国的科学家则并不被要求掌握多门外语。战后迅速壮大的苏联科学家与工程师,是美国在科学上的新竞争对手。在1950至1960年代,世界上约有25%的科学出版物是俄语写成的,俄语成了世界第二大科学语言,紧跟在英语的60%这一比例之后。然而,到了19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都倾向于用英语交流,俄语出版物的数量又开始下降。
美国人无法——或拒绝——学习俄语来从事科学,更不用说别的外语了,再加上美式科研体制跨过大西洋输出到了别的英语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令科学的英语化(Anglicisation)愈发加剧。 欧洲、拉美及其它地区学者加入这一新的单一语言体系的意愿也有一定影响。 鉴于希望被名列前茅的同行引用,荷兰人、北欧人和伊比利亚人也减少了法语或德语的发表,转而使用英语。 颇为矛盾的是,以英语之外的任何语言出版都会被视为在表达一种民族主义的特殊主义(nationalist particularism):非法语母语者不会用法语出版,德语也是一样。
随着冷战的白热化,以俄语发表也被解读成了一种明确的政治宣言。同时,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继续学习着英语,但科学史上的这一反常发展却一般不被看作有深刻的政治性。到1980年代早期,英语基本上占据了全球自然科学出版物里的超过80%,如今则发展到了99%左右。
那又如何?信奉效率或许有一定道理,而如今只用一门语言的科学在沟通上也很方便——近来科学的显见成功似乎可以用这种思路来解释,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代价。在1869年,迪米特里·门捷列夫几乎丧失了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身份,因为他是用俄语而非德语出版的;如今,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学术领域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以及在非顶级期刊——出版,学术成果几乎肯定会遭到无视。
法国数学家通常以用法语写作为骄傲,其高度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有助于让操英语的学者跟上证明的思路。在实验性较强、较少使用方程的科学里,这种奢侈是不可思议的。试想,有多少原本前途无量的学生因为学不好英语——而不是多变量代数——而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随着全球教科书产业日益英语化,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甚至于高中也开始出现类似问题:市场根本不认可捷克语或者斯瓦西里语的微生物学教科书。单一语言的科学也有其代价。
这种格局一旦确立,似乎就只会越来越稳固。在当下的形势都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下,要揣测科学语言的未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单一语言体系下的科学交流,更不用说某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母语深入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并成为其默认设定的情形了。
话说回来,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维持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单一语言体系,既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也需要在非英语国家对语言培训和翻译投入海量的资源。第二,哪怕所有英语国家在明天立刻消亡,英语也仍将是重要的科学语言,惯性毕竟是难以消除的。以往的知识积累在科学家当中形成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心理学术语,人们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它就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简言之,人们在决策时会不自觉地过度重视最初获得的信息——译注)同时支持了以往的多语言共存体系和如今的单一语言体系。
问一下你身边的科学家即可。她一定能理解你。
本文作者Michael D Gordin系普林斯顿大学现代与当代史教授、校人文学者联合会负责人,著有《组织有序之物:迪米特里·门捷列夫与元素周期表的阴影》)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