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纽约时报》Motherlode博客的生育日记专栏撰写周记,记录我试管受精怀孕的过程。刚开始,我讶异于文章底下留言的尖酸刻薄。确实,我41岁了,年纪是有点大,这个时候才怀孕可能确实很高龄,但这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吗?除了我的银行卡,难道我还伤害了别的东西?
“你的老了,干枯了。”一位网友如此评论。那是2013年,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来得及分化美国;那时候他们还不像现在这样气焰嚣张;那时候发表以上言论的人很有可能被视为疯子。
“艾米(本文作者)的怀孕日记似乎全部都是她自己和她本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这个问题完全是关于母亲的,而不是关于孩子的,”来自西雅图的罗斯留言道,“你为什么想为人母?”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如果我在文章中坦陈心迹,我就可以改变对话的走向,让网友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但现实很残酷。他们一如既往地刻薄——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在怀孕后期就不再看网友评论了。我怎么可能看得下去呢?我被激素搞得心力交瘁,数次怀孕失败的经历让我身心俱疲,还得担心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我的编辑坚持让我多与读者互动。我的解决办法是让我丈夫帮我看评论。“你这样做很自私,你已经老了,你应该去领养一个小孩……”——这是他的总结。
一些女读者给我发私信,因为她们害怕和那些刻薄的女性打交道。“我不想在你的博客上发表评论,因为在那里评论的人大半都令我生厌。天哪……美国人对生命、孩子、母亲、同理心和正直的看法特别奇怪。他们真是可怕!”
正是从这些电子邮件中,我意识到我文章下面的评论到底有多糟糕(我说的就是你,“jzzy55”),但我不明白的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卡罗琳·卡斯蒂利亚(Carolyn Castiglia)在育儿杂志《Babbl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已经删除了,但是其他网站仍有转载),题为《42岁还想生孩子,我们应该同情她吗?》为什么会有人——不,是另一个女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在她文章的结尾找到了一条线索。她先是指责了我没有早点要孩子或收养孩子,然后她写道:“我很早就结婚了,因为我觉得我想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想拥有一个家。我那时候还年轻,作出的决定并不明智,所以我现在离婚了,但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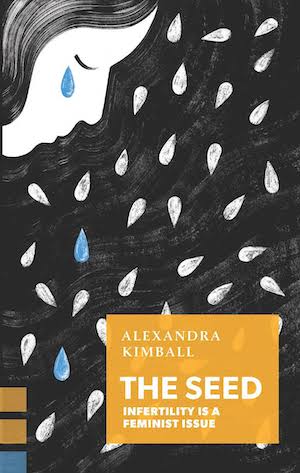
她不希望我成功通过试管受精生子,是因为我在年轻时并未如她一般匆忙恋爱结婚。如果现在42岁的我也能生孩子,岂非意味着她当初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错误?
这段赤裸裸的话——不像备受追捧的“灰衣女士”(Gray Lady,指《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那样以训导人为乐——为我提供了一个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女性对不孕妇女如此刻薄。
他们对我们充满恐惧,没错。他们中的某些人似乎并不希望我们能生孩子。
***
从亚历山德拉·金博尔(Alexandra Kimball)的《种子:不孕不育是一个女权问题》(The Seed: Infertility Is a Feminist Issue)一书中,我了解到,不孕女性经受的敌意由来已久。除不孕女性以外(不孕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可解决的问题),石女被视为贱民,是其他母亲嘲笑的对象。金博尔写道:“从史上首次出现的记录来看,不孕女性是怪物,明显有别于正常女性。”她在书中细数了绑架孩童、引起流产、难产、造成男性不孕的神话人物,包括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阿特拉哈西斯、犹太神话中的莉莉丝(我女儿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和埃及神话里的Alabasandria。她指出,许多出名的的巫术审判都针对不孕妇女。认为不孕妇女“不正常”这一现象可上溯至圣经时期,且至今仍然存在。没有孩子的女人常常被视为“恶魔”——就像电影《推动摇篮的手》中,图谋报复的保姆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她因流产而无法怀孕),试图偷走雇主的孩子。
不过,如今在科技的帮助下,不孕的巫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生育自己孩子的不育者。
这些医学创新,使原本只能在异性夫妇床上达成的“繁殖”进入公众视线中(事实上,目前仍然需要异性生殖细胞的结合),使他们热切地讨论起世界末日和反乌托邦来:新闻头条到处吹嘘“狂野西部”式的生育科学、繁殖的科幻小说式未来……与此同时,评论专栏已经开始思考经医学手段协助出生的婴儿带来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人们的担忧已经从职业女性的不孕转移至她可能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上。
就像蒂娜·菲在《我为喜剧狂》中饰演的电视制片人莉兹·莱蒙一样,张牙舞爪却又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已经变成了绝望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生育狂。或者更可怕的是,成为《使女的故事》中无法生育的年老女性。

现在我承认,因为我接受了试管受精,我很难看得下去这部反乌托邦电视剧——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不孕的沃特福德夫人存在相似之处。在剧中,沃特福德夫人的丈夫强制与代孕女佣发生性行为,夫妻俩才拥有了孩子。在这个反移民、反女权主义的时代,尽管这部电视剧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却无法像金博尔那样严厉指责电视剧原著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金博尔称阿特伍德“将不孕妇女定义为家庭中的弃子、父权社会的为虎作伥者,无疑(正在)背叛不孕者”。
当然,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一部前提是科技高度发展且泛滥的反乌托邦小说。但金博尔的观点是,女权主义(以及蒂娜·菲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女权主义者)“素来要么对不孕妇女的困境不屑一顾,要么对她们充满敌意”。
《种子》一书向我们说明了不孕不育者是如何被女权主义排除在外的。女权主义一直在争取避孕、性教育和堕胎的权利,他们的口号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是父母想要的孩子”,但是他们却忽视那些想要却不能有孩子的人。
尽管我本人确实是女权主义者,但我对它的理论并不精通,我也不是什么学者,所以我对这样的陈述很是疑惑:“一位女权主义性工作者曾告诉我,社会大众害怕妓女,是因为妓女让资本主义的谎言无所遁行。我认为,同样地,不孕妇女也揭发了‘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的谎言。”
我不得不谷歌一下什么是“性别本质主义”(一个用来检验固有的、内在的、天生的男女特质归属的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金博尔所言的“一个女人不应该由她的子宫来定义”。事实上,她注意到,当她堕胎时,其他女权主义者对她的欢迎程度,要远远超过她多年以来忍受不孕症时的欢迎程度。
诚然,如今女权主义者有很多东西要争取,“罗诉韦德案”和堕胎权便是其中重要角色。然而,不孕妇女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当一项反堕胎(“人格地位,personhood”)法案认为生命始于受孕时,胚胎也包含在内。“如果胚胎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堕胎等常见做法将构成谋杀。”金博尔认为,如果堕胎被定义为犯罪,那么试管婴儿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女权主义者不会为不育者而斗争,而女性——无论是母亲还是丁克族——都劝我们“收养一个就行了”,劝我们享受没有孩子的人生,或者劝我们“等待戈多”……这让金博尔和我这样的女性如同置身冰窖。“如果要写一个关于不孕妇女的故事,它的主题会是孤独。”她断言道。
不孕妇女坦言,不孕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社会,包括正常生活轨道遭中断的感觉、遭到污名化……大众(仍然)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活意义应来自于其母亲身份,成为母亲后,她人生中的其他方面便自然而然地成形。而不孕妇女,则无法拥有正常女性的人生路径。
***
金博尔尤其善于描述不孕妇女的孤独感和孤立感:书中一位女性想要孩子,但不幸流产。一天,她陪同丈夫出席商务晚宴,中途却离席而去(当然,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桌上有长舌妇问“你打算要孩子吗?”)。又或者,在网上抱团的不孕不育群体中,每位女性都只能被不孕症定义,这确实怪异至极。
我最喜欢的描述精准地概括了几乎所有与不孕有关的社交生活。金博尔在书中写道,不孕“产生了一个令人苦恼的难题:它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事情,除了其他不育女性,没有人愿意谈论它”。当然,在书中末尾,金博尔发现很大程度上,公众已经开始接受试管婴儿(除了部分宗教仍然持反对态度)。在现在的流行文化中,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都是由正和不孕不育作斗争的艺术家制作的。
然而,仍然被大众回避的是第三方生殖:捐赠精子使用者、卵子捐赠者和代孕者。其中代孕母亲受到女权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他们称其为“出租子宫”,并谴责对卵子捐赠者的剥削。这种分裂甚至存在于可生育的群体中,这里的每个女性都在试图比拼谁的生育过程最“自然”,或者谁的最艰难。
林赛·费舍尔(Lindsay Fischer)是网络社区“不孕不育音频”(Infertile AF)的联合创始人,由于丈夫不孕,他们一直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我注意到很多女性不太愿意表达对我的支持,也不太愿意理解我的压力和焦虑,因为‘我并非问题所在’。找到一个支持我的女性群体并不容易,所以我很难产生归属感。”尤其是在她第一次进行胚胎移植便“轻松”地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她表示道。
不孕群体中同样出现了分化,互相都高高在上看不起对方:雇佣代孕母亲的人会强调基因如何重要,因为她们使用的是自己的卵子;而购买了捐赠卵子或捐赠胚胎的妇女则会强调怀孕过程的重要性。金博尔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群体——她聘请了代孕母亲,也使用了他人捐赠的卵子,最后用她丈夫的精子完成受精过程,生下了他们的儿子。
不过,讽刺的是,金博尔并没有忘记,她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另一个女人的慷慨。在代孕妈妈分娩后的那一刻:
明迪转过头来,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下。哦,我想。这就是她想让我拥有的。这就是她一直说的。这种我从未有过的强烈感觉,以及另一个女人愿意将十月怀胎的“孩子”给我这个事实,让我感到不知所措。
***
《种子》的副标题是“不孕不育是一个女权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比尔·克林顿曾经很受女权主义者拥护,后来却遭女权主义者唾骂,用他的话来说:“这取决于‘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不孕不育应该归在女权范畴内。在争取生育权利的斗争中,它也应该在场。有子女者与无子女者都应意识到不孕的痛苦。这绝对是所有妇女都应该学会接受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拥有孩子时,招致了很多尖刻无情的批评,这让我震惊不已。毕竟我以为女性都会站在同一阵线上,也许金博尔也犯了这个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除了生活比小说更离奇这个事实之外,如果说2017年美国大选还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那就是女性尚未团结起来。我们不想重蹈覆辙。无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多少“加油女孩”的“梗”,我们的性别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我并不是故意找茬(我没有提我三年不育、四次流产,看了十个医生,辗转跋涉三个国家只为生下我的女儿),但我想说,不孕的经历确实使我充分做好了当一名母亲的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使我更有余力地对付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摩擦: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支持雇佣保姆者和支持日托者、支持母乳喂养者与支持奶粉喂养者……当然,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要求得到更为完善的探亲假和工作保护制度,而不是在网上互相抨击,大部分摩擦都可以得到解决。
由于我在网上受到其他女性的公开严厉指责,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这些“妈咪战争”(以及2017年大选结果)感到惊讶。没错,有些女士对我很友善,但很多人没有如此。所以,对于像Jzzy55和Castiglia这样的人——我曾经想掐死她们——我现在很感激她们为我揭露了姐妹情谊的阴暗面。或者,用学术术语来说,这就是女权主义的谎言。
最后,我想说,我想要的东西其实和金博尔想要的东西一样。
当她终于拥有自己的孩子之后,她重返了她以前加入的试管婴儿和代孕委员会,因为她想知道这些社区是如何被女权主义思潮改变的。“如果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将我们视为姐妹,而非男权社会的愚弄对象或帮凶,”那么,她认为我们可以发起一场由女性主导的运动,深入研究不孕不育的原因、治疗的有效性和风险,为穷人、有色人种、非异性恋者争取更多保健权利,更好地保护代孕母亲和卵子捐献者。
她打算动员其中一个委员会,让我们这些不孕女权主义者可以团结起来,“挑战‘成为母亲是轻率、自然、本能的’这一想法,以身作则告诉他人如何为母,告诉他人母亲并非只能当家庭主妇或职业女性。有时我们可以多人行动,有时甚至可以把男性也动员进来。”
正说着,她的孩子哭着要找妈妈了。就像大多数终于成功拥有自己孩子的不孕妇女一样,她抽身去照顾她的小孩了。
本文作者Amy Klein是即将出版的新书《尝试的游戏:深思熟虑后借助医学手段怀孕》(The Trying Game: Get Through Fertility Treatment and Get Pregnant WithoutLosing Your Mind,Ballantine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作者。
(翻译:刘其瑜)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