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物是遮羞布,是身体的铠甲,是心灵的慰藉。从出生时的襁褓,到临终时的寿衣,终其一生,人类都在衣物的陪伴下过活。19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衣服,就像房屋,内含一切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因素,足以“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然而遗憾的是,衣物——人类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保护者,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正行其责,反而成为邪恶的杀手、死神的帮凶。奇装异服当然杀伤力更强,无聊的常服也不遑多让:袜子、衬衫、短裙、长裙,就连看似舒服的棉质睡袍,都是杀手阵营里的一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英国、北美,从那时起,时尚机器与其载体——服饰,就一步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对“优雅精致”的时尚男女来说,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女士们脚踩高跟鞋,身穿有箍衬裙,内裹紧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们头戴厚重的礼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勒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搁到现在,估计没人受得了。最可怕的,还是所谓的“贵妇时装”,这种强大的社交机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与它“近身相搏”的人,不论是制衣者,还是穿衣人,都饱受折磨,身心俱疲。这些人是“奴隶”,是“受害者”,若将他们神化,还可以称其为“殉道者”。

1827年,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时尚与死神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中,将“时尚”拟人化,称为死神的姐妹。“时尚”骄傲地宣称,她最爱玩死亡游戏,“被鞋子禁锢的蹒跚世人,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眼珠鼓起……我好心劝慰,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然而,他们爱我,宁受每日千般折磨,万般痛苦,就算因此光荣就义,也要爱我。”
19世纪初,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男女。然而到了1830年,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对男性来说,黑色套装独占鳌头,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民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相反,女性“自然而然地”成为愚昧、疯狂、专断的时尚界受众。无论在家或是外出,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阻碍着女性的行动与健康。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舒适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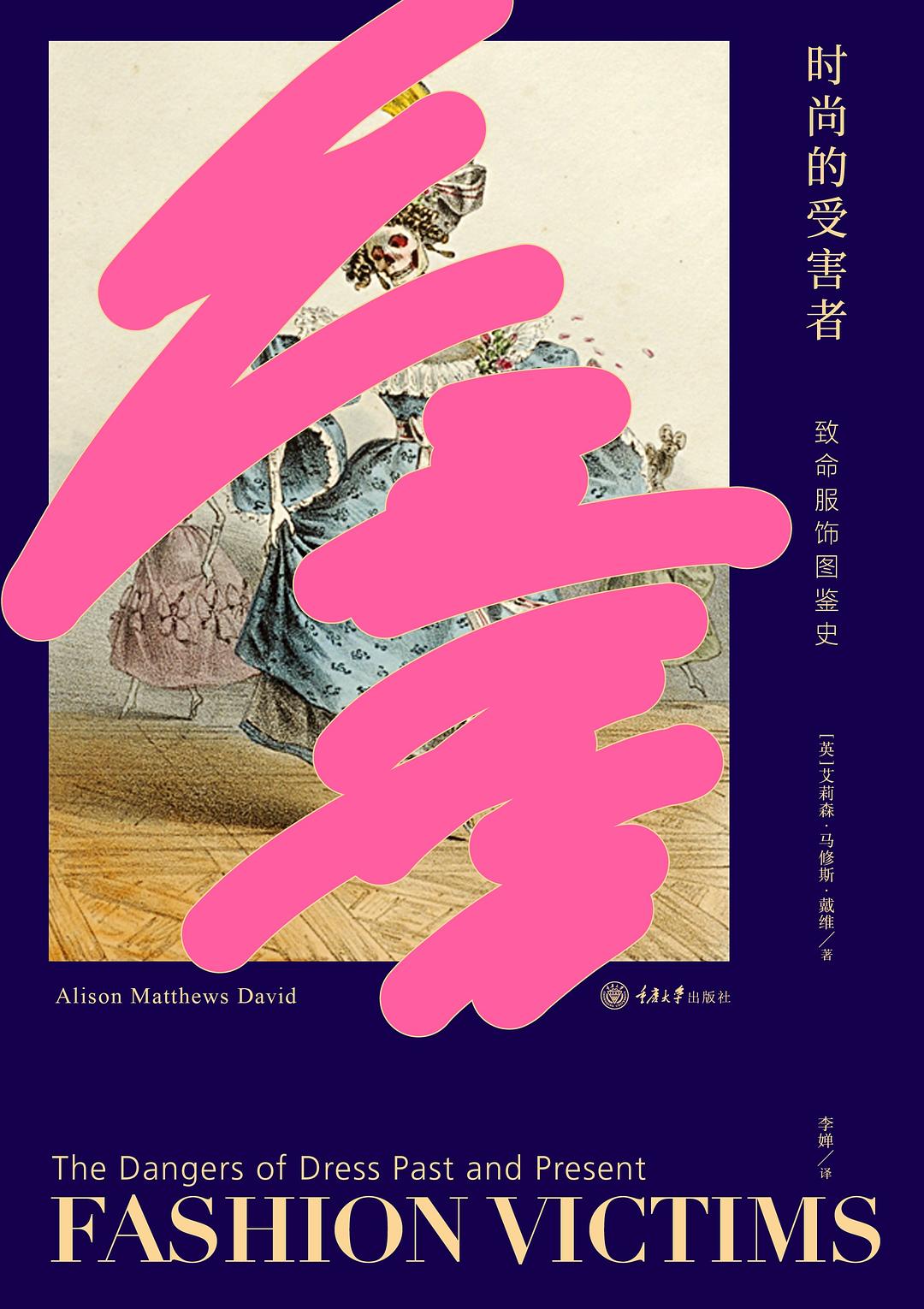
[英]艾莉森·马修斯·戴维 著 李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08
时尚受害者的过去与现在
从1999年到2006年,日本摄影家都筑响一用镜头书写了这样一系列的故事:《穿衣穿到穷》。每张照片分别记录一位品牌拥护者的“港湾”——从满满一柜子的爱马仕(Hermès)到一屋子闪闪亮亮的日本朋克品牌Fotus——镜头里的人对特定品牌的痴迷,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照片的每一位主角,都是时尚受害者的绝佳诠释。在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女士展示了她的全部藏品:衣服、鞋子、化妆品、香水。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美国品牌——安娜苏。照片中的女主角躺在镜头的最前方,周身波希米亚风——人造皮草、针织、蕾丝、精致的眼妆。

在疯狂的“血拼”后,她双目紧闭,精疲力竭,像死了一样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中间。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这组照片,把它当作对品牌忠实粉丝的讽刺挖苦,但是对都筑响一来说,创作的出发点不过“兴趣”二字。他想知道,在日本,“品牌的忠实粉丝究竟如何生存。”“这些人并不富有,为了买衣服,他们租住在很小的房间里,省吃俭用。虽然买了一大堆,实际并没有好地方可去,衣服也没有用武之地”。
都筑响一的照片表达得客观谨慎,他不希望引导读者对时尚消费者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情绪,但他也说,与这些拼命购买服饰的“瘾君子”相比,其他物品爱好者,尤其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内涵的物品的收集者们,往往不会受到他人的轻视。这些物品可以是书籍,或是黑胶唱片,而我,还想在物品名录里加上一种特别的服饰——“古董衣”。
都筑响一的作品发人深省,既催人思考时尚受害者的本质,也使人意识到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无论是做衣服的人,还是穿衣服的人,都在疯狂滋长的消费主义浪潮中饱受折磨。在都筑响一的镜头下,消费者是唯一的受害人,而在约翰·坦尼尔的插画《穿衣镜中的幽灵》里,主人翁(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在镜子里看到的,却是女裁缝的死亡影像——她死在量身裁衣的工作中。这幅插画以真实事故为背景,一位名叫玛丽·安·沃克利(Mary Ann Walkley)的女裁缝,年仅20岁,受雇于宫廷服装制衣商埃莉斯夫人(Madame Elise)。在连续工作二十六个半小时后,玛丽死于疲劳过度。那是1863年,当时玛丽的工作内容是为庆祝丹麦新王妃的到来,缝制庆典专用的礼服。卡尔·马克思曾在其名著《资本论》(Capital)中提及玛丽·安·沃克利,称她的死亡为“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还在报纸上发稿,谴责此类悲剧的发生:“我们白人奴隶,被苦役埋入坟墓,沉默、苍白、死去。”

这幅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正面抨击了时尚行业的残酷,然而此后,自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现代的营销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大地美化了“死亡”“毁灭”和“创伤”。时尚行业的营销机制老辣世故,它极力缩小人们的眼界,说,来!别揪着“时尚”不放,还是看看社会学和心理学吧,这样就能知道罹难者们究竟有些啥毛病了!于是,时装里的危险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人们不再害怕它,更不会谴责它。一想到“时尚”二字,人们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个打擦边球的心理学名词:买太多的人是“购物狂”;奇装异服是“青春期”的表现,活该被同龄人嘲笑排斥;而貌美如花的“自恋狂”们,自视甚高,只要稍微被网络、杂志和T台上又瘦又白的明星一撩拨,出问题是早晚的事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尚的面孔,它精心算计,营造魔性魅力,引诱每一个人。即使你对它的狭隘嗤之以鼻,却仍难逃其诱惑。提到“时尚的受害者”这个词,首先蹦入我们脑海的,总是非西方文化对人体的伤残行为,例如古代中国裹脚的行为、当今社会的整形术或是硅胶填充……然而,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时尚魔爪,剧毒无比,却深藏不露,隐而不现。几个世纪以来,时尚对人类的伤害由外而内,无论制衣者或是穿衣人都难逃其害。土地、空气、水、人和动物,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时尚的牺牲品。
日益发展的工业化水平,以及不断精进的科学技术,对于服装行业来说喜忧参半。男人们,无论是化学家、工程师,还是工业家,不断利用新技术发展服装行业,扩大生产和推广新型材料,将过去上流社会才能穿戴的服装、配饰、色彩,引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危险。“奢侈品”范围的“扩大”,引起许多观察家的谴责,认为这将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客观地指出,与男性消费者有限的兴趣相比,女性对新款服饰的欲望简直毫无理智可言,更应受到批判。
医学界鼓励这种性别偏见,它鼓励各界人士加大对女性的谴责,因为她们的确是生病、受害的主体。于是,19世纪的医生和大众媒体联合起来,广而告之,利用《时尚的自杀》《车间里的死亡》等杂志,明确指出时尚对女性的伤害。大多数中产阶级评论员尤其关心女性的时装是如何伤害人体的,人们认为它是一系列疾病,包括内脏器官疾病的诱因。过紧的蕾丝、束身衣均可致病。虽然这类猜测不乏夸张之处,但是,所谓的时尚文化的确打造了许多莫名其妙不合乎人体生理特征的东西。

鞋就是个绝佳范例。19世纪50年代前流行一种“平鞋”,这种鞋子完全不考虑双脚的形状及其对称性,没有左右之分。虽说对制鞋人来讲是个好事,节约时间又省事,但长期穿着这种鞋子,会让脚部变形。在那个时代,男女鞋都是这样,鞋底窄得不可思议。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获得一双小巧的脚,不少女性选择用布条绑住脚趾,就像为脚穿上束身服一样,不是为脚选择合适的鞋,而是为鞋塑造合适的脚。人体的其他部分也遭受着同样的噩运,不得不屈从于一系列“修正”行为,改变“天然”形态。
19世纪60年代的女性流行一种走路姿态,被戏称为“希腊式弯曲”:挺胸翘臀,将周身平衡和安危系于脚后跟。当然,不是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都会摆出这种极端的造型,但是,只要有人用这种姿势走路,一定会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和服装历史研究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机械束缚方向,但是时尚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大大小小的致命案例占据着19世纪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

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我们忘记了这些恐怖致命的危险:有些衣料就是传染病源,或是遗留有化学毒素;工人作业一个不小心,身上的衣物就可能被卷进机器,或者冒烟着火,连带着衣服主人也没有好结果。翻开当年的报纸或是医学杂志,各式各样的警告铺天盖地,告诫人们小心传播可怕疾病的洗衣房:迷人的绿色裙子是用砷染的色,易使人窒息死亡;裙箍是用易燃材料做的,穿着它有可能被活活烧死。谢天谢地这些事故都发生在过去,但是,只需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时尚行业依然荆棘密布,危机四伏。
致命的鞋、围巾和短裙
接下来的三个案例表明,女性的穿着打扮较男性艳丽,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事故也有性别之分。家庭、城市、工业环境在改变,而女性的穿衣风格,非但没能与时俱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更加轻视着装的风险。从历史上看,男性衣裤鞋帽主要用于彰显权力,让他们在公众场合行动自如,安全无忧。反之,女性的鞋从来都是时髦重于实用。因此,各式各样的防水台和恨天高成为多起事故的诱因,着实不令人吃惊。这些鞋要么让人摔倒,要么增加了工作难度。现代时尚圈里最有名的尴尬事件莫过于1993年黑人超模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在天桥上的一摔。当时她脚蹬一双蓝色的鳄鱼皮制高跟厚底鞋,为Vivienne Westwood品牌走秀。受过专业训练的模特儿穿着厚底鞋都难逃一摔,对业余爱好者们来说,上街就更是苦差事一件了。一般情况下,穿这种超高防水台的后果,不外乎伤筋动骨,但在1999年,一位日本的保育员,因为穿着高跟的软木厚底鞋,狠狠摔了一跤,摔坏了头盖骨,几小时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级流行的超高厚底鞋被认为是造成车祸事故的原因之一。尽管那时也有部分男性穿着厚底鞋,1974年的某研究却把矛头直指女司机,他们将年轻的女学生作为调研对象,明显透着性别歧视的味道。女学生们在实验室里模拟开车,然后进行紧急刹车操作。实验对象的征集标准为“厚底鞋拥有者,有不低于两月穿厚底鞋开车的经历”。她们需在实验时穿着厚底鞋开车40分钟,然后换上普通鞋继续实验。实验表明,厚底鞋无一例外地降低了刹车速度,而且在速度为每小时70英里的高速路段,即使穿着普通的平底鞋,与普通路段相比,驾驶者仍需要额外滑行10英尺才能将车完全停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尚圈再刮厚底鞋风,类似Ginger Spice的这种黑红相间的水牛厚底靴受到粉丝追捧。这种鞋底约6英寸高,对于警务人员来说,它们简直是驾驶界的不定时炸弹,其危险程度等同于醉酒驾车或边开车边打电话。1995年,日本东京一位25岁的年轻女士和同伴一起开车从购物中心回家。因为鞋底厚8英寸,严重影响刹车效果,车撞上了一个混凝土桩,副驾驶位上的朋友当场死亡。日本的交通法规已明令禁止穿着传统木屐或拖鞋驾驶,但大阪的警察表示,这份名单里还应该加上厚底高跟鞋。厚底鞋事故告诉我们,流行趋势和都市生活并非协调一致。然而,究竟谁该成为我们问责的对象呢?肇事的那位时尚消费者?还是推动他们的时尚潮流和经济需求?

20世纪70年代,复古风胜行,许多20年代的时尚单品重新登上舞台,其中之一就是长围巾——汤姆·贝克(Tom Baker)在系列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里戴的那种,看着挺古怪,针织质地。来自遥远星系的时间之主戴这种围巾毫无违和感,但当越来越多的“凡人”复制“时间之主”的风格时,这种围巾带来了致命危险。1971年,美国一位20多岁的年轻母亲“乘坐缆车时,长围巾缠在对面过来的缆车上,被扯出座位”。《美国医学期刊》曾登载一篇文章,抨击了这类长围巾综合征,该文现在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例作。文中说,这位不幸的女士“死于窒息,因为她被拖出椅子以后,被长围巾吊在了半空中”。也有幸运儿!同年,一位10岁女孩儿的围巾被缠在上山缆索上,另一位11岁的男孩儿的围巾被搅进雪地车的引擎里,还有一位花季少年弯腰检查摩托车时,围巾卡在了发动机里。好在,这些人都保住了性命,只是面部多处严重撕裂和擦伤。医生总结说,这类事故的死亡率高达45%,而且新的“流行、时尚总在不断刷新此类危险”,儿童更是高危人群。由围巾或是其他服装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例如,如果外套的纽扣卡进游乐场设施里,或者背扣式毛衣缠在玩耍护栏上,一旦小孩钻回护栏内,滑倒在地,毛衣很可能会像“鞋带”一样勒住小孩的脖子,令他无法呼吸。1982年,科学家曾针对儿童的意外死亡事件展开研究,发现在共计233起致死案例中,19起死于衣服引起的事故,20起死于床单缠绕事件。因此,高寒地带国家的许多学校和幼儿园出台政策,禁止儿童佩戴围巾外出,鼓励使用简易围脖保暖。例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卫生部日前发文告诫儿童看护类专业人士,“确保儿童不戴围巾、领结,不穿带有抽绳或过于宽松的衣服。”
2004年,英国演员西恩娜·米勒(Sienna Miller)将波希米亚风重新带到时尚巅峰。这种打扮的诀窍是,身着白色的乡村风格或吉卜赛风格的长裙。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颜色、风格的棉质轻薄长裙,裙子上通常有一层层的荷叶边。荷叶边轻盈舞动,摩擦着脚部关节,看起来灵动可爱。然而,正是这种可爱的裙子,带来了严重的火灾隐患。2005年秋,在一位9岁女孩重度烧伤事件后,北安普顿贸易标准协会发布了一条关于这种吉卜赛裙子的高危警告。同年,大不列颠默西医院烧伤科发表名为“吉卜赛裙烧伤病例”的文章,因为仅在2005年一年之内,该专科就接诊了6起因吉卜赛裙子起火烧伤的病例。有两起这类案例,俱因事件的女主角打电话分散了注意力,一不留神,裙子起了火。其中一位女士的裙子是在跳舞时燃起来的,另一位的裙子则是被地板上的装饰蜡烛点着的。这两位女士在事故发生时均未饮酒,可以排除酒精因素。因此,想象一下吧,不过是一条日常穿着的裙子,样式也不算夸张,只不过因为布料有点轻飘飘,就引发了那么多起火灾,随便来点烛火就完蛋,好在我们有现代医学,若是换在古代,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危险的服装,加上生活中充斥的明火——可燃气体、木材、煤、蜡烛——危险系数岂不噌噌上涨?!
现代社会,事故发生后,警察、儿保专家、急诊医生,都会立刻跳出来,告诫和保护大家。政府机构常常出台新规,禁止销售有安全隐患的衣服,防患于未然。例如,欧洲委员会下设RAPEX系统(非食物危险产品的快速警报系统),每周定期公布危险品名录,种类包括服装、化妆品,甚至文身药水。只要产品具有“极大的风险”,就会被该机构明文禁止。2013年,超过200种女性比基尼和帽衫,因为带有蕾丝和抽绳,可能致人受伤或窒息,被勒令退出市场,禁止发售。纵观历史,人类对待意外事故的态度在不停地变化。19世纪以前,时装的危害多在道德层面,而非医学层面。夸张的服饰,往往只出现在上流社会。作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小众,这些人成为漫画的主人翁,既能娱乐大众,又能顺带起到教育作用。18世纪的一幅画作《假发之火》,就是一幅讽刺假发的佳作。

画面描绘了一对夫妇,在D’Alexandre皇家咖啡馆享受茶点。这家咖啡馆是典型的巴黎风格,有着巨大的玻璃橱窗。行人透过橱窗,就能看到咖啡馆内华贵时尚的男男女女。画面上,男主角正为同行的女伴拉开座椅,一派绅士风度,然而此时,女伴头顶高高的假发,无意中碰到了天花板上的枝形烛台,被蜡烛一燎,冒出滚滚浓烟。服务员们吓坏了,他们搭起梯子,争先恐后爬上去灭火。配图的文字刚好相反,没有一丝同情:“浇什么水呢?这种愚蠢的发型烧起来才好呢。”当然,真正的假发不可能有图上描绘的那么高,但是固定假发的发胶确属易燃物质。这幅《假发之火》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将发饰的危险描绘无遗。然而,此画问世的几十年后,女性的衣饰仍未吸取前车之鉴,棉质衣物、宽大的衬裙、塑料梳子……它们变身火引,将无数爱美女性卷入大火之中——死神降临。
从神话到现实:有毒斗篷和化妆品
毒,对于服装而言,是古已有之但乏人问津的一大危机。过去,衣服及化妆品往往由有毒化学物质制成,但直至今天,人们穿的、用的还是它们。正是这种对有毒衣物的恐惧,衍生出无数与有毒衣服相关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存在于各个时期,流传于各种文化之间。只要吸入毒素,人体就会迅速受到伤害。有毒衣物是一件利器,是从古代延续至今的隐形杀手,它直接接触皮肤,毒通过毛孔被人体慢慢吸收。但是,慢,不等于无害,历史和今天都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剥离化学毒品和传染疾病的关系,只需一片被感染的布料,死亡就能在人群之中蔓延。

19世纪以前,科学的毒物学和辩论术还未出现,谈到毒物,人们很难说得清它究竟是真实还是幻想。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病就是毒,它通过难闻的空气传播,因此,只要带上一双香喷喷的手套,香水的浓烈气味就可以保护手套主人免受传染病的困扰。但是,手套这东西,可以被喷上香水,也能被喷上毒药。凯瑟琳·美第奇王后(Catherine de Medici,1519—1589)就被指控利用手套投毒。在拜占庭帝国,在这个跨越南亚与中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的帝国的传统庆典上,人们需着“Khil’at”,又称荣耀之袍(Robes of Honor),因此这种长袍成为当时流行的暗杀工具。按照传统,收到这种华丽丝袍的人,必须立刻穿上这件礼服,于是,两难的局面出现了:“要么拒绝接受这件可能被染上毒物的衣服,然后成为他人眼中的不忠之人;要么平静地接受并穿上它,然后静静地等待可能到来的死神。”
虽然毒物不同,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许多腐蚀性的化学药剂也像神话中的毒液一样,通过热和汗水激发活性。无论是发明这些试剂的化学家,还是染布工人、缝纫师,都深受其害。当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还是消费者。涅索斯的神话不断上演。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The Lancet)困惑于为何读者读到“袜子或内衣使人中毒”这类文章时总是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或许,这类文章总使人联想到神话故事——诸如赫拉克勒斯之死一类”。一位法国医生曾写道,毒神话变成了毒科学,“就像是涅索斯之袍,被人从幻想作品中,直接拉入了现实。”

今天,人类用毒的技能日益增强,尤其擅长用毒品帮自己变美。肉毒素由肉毒杆菌繁殖产生,是人类世界已知最致命的病菌之一。肉毒素经稀释后,可注射到人体面部,使面部神经瘫痪,从而平复皱纹。这种做法已经被大多数时尚教主们接受,甚至连一些政治领袖也采用这种方法“永驻青春”。我们或许认为,化妆品含铅的问题,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就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事实上,化妆品的时尚“进化”之路漫长曲折,即使是今天,口红中含铅的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文艺复兴时期,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常常在脸上涂抹厚厚的铅粉用于美白,这种粉被称作“威尼斯铅粉”(Venetian Ceruse)。因为“铅”能使颜色均匀透亮,创造出令人渴求的“白皙”的皮肤。几个世纪以来,铅一直被用在各种化妆品中。涂抹上铅粉的皮肤,与劳动人民日晒雨淋、又黑又糙的皮肤截然不同,还能进一步强调白种人的优越感。这一时尚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彼时医学界终于将视线投向化妆品领域。一份医学报告的出现,曾直接导致纽约某品牌化妆品生产商被告上法庭。1869年,美国医学协会的创办者之一,刘易斯·塞尔(Lewis Sayre)医生接连救治了三位年轻女士,她们都是在使用了莱而德(Laird)品牌的“绽放青春”系列化妆品后,身体开始变得极度虚弱,刘易斯医生将此种病症命名为“铅麻痹”。该产品的广告声称,该产品具有美白、去皱,使皮肤光滑的作用,然而除此以外,它还具有致残效果。三位女士大约每月一瓶,在连续使用该产品两到三年后,手部肌肉麻痹瘫痪,“枯瘦如柴”。其中一个女孩年仅21岁,显然足够年轻,根本不需要用什么“绽放青春”的产品。

该产品的广告和医学杂志插画,如同两个极端的对立面,一方描绘“高效的美容”,另一方则刻画“高效的致残”。广告中,女孩优雅地打开手中“液体珍珠”的盒盖,然后涂涂抹抹;医学插图里呢,只有一个无头的病人,两手扭曲,无力下垂。现在,我们称这种病症为“腕下垂”或“桡神经麻痹”,致病原因就是铅中毒。插图中19岁的女孩不能“吃饭、梳头,连一根针或是衣物上的一颗纽扣也拿不动,事实上,她的手什么也做不了。”好在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和“电疗”,通过在手上植入假体,三位女士“幸运地”康复了。此后几十年间,该品牌产品继续在市面上销售。我们可以通过19世纪80年代的广告看出,该品牌向消费者宣称,产品经美国卫生委员会检测,“完全不含任何有害物质,不损害人体皮肤和健康。”
1875年上市的美国粉饼品牌泰特洛(Tetlow)的“SwanDown”系列,曾经风靡一时。该产品以“安全”作为卖点,外包装上直接印有“无害”两字。品牌创始人亨利·泰特洛是英国人,移民费城后,成立了一家化妆品及香水公司,大放异彩。泰特洛的品牌之所以取得成功,从表面上看,在于他发现了一种廉价的美白代替品——氧化锌(这种配料现在仍用在防晒产品中),取代了早期化妆品行业使用的有毒物质。于是,原本买不起化妆品的普通妇女们,也能买上一两盒胭脂水粉了。靠着这些人,亨利·泰特洛发家致富。这款粉盒内包装上印着一只天鹅,它悠闲自在,浮在水面上,湖水下方,有这样一行标语,“其他粉饼来了又去,只有SwanDown伴你永恒”。后来,我从古董商那里买到一盒未开封的SwanDown,并送到瑞尔森大学实验室进行检测。实验结果让人笑不出来:这种粉饼中确实含有锌,但也含有大量铅粉。泰特洛的市场宣传无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SwanDown本应起到温和美白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该产品,其中的铅粉可能通过血液进入肺部,在人体内堆积,然后,“伴你永恒”。遗憾的是,你的永恒不在脸上,而在骨头里、牙齿中。

历史上,这样的有毒化妆品不胜枚举,令人毛骨悚然,然而,铅作为染料的重要原料,今时今日,其危害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铅为重污染物,法律明令禁止将其用作化妆品配料,因此我们很难在口红的配方表上看到这个成分。口红可能被吃进嘴里,唇部皮肤又薄,有毒物质特别容易经由唇部被人体吸收。尽管法律规定,只要产品含铅,不论含量多少,均为不安全产品,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该机关负责规范化妆品安全)表示,就口红而言,现今还没有绝对安全的产品,因为铅仍被“有意”地加入唇膏之中。2011年,FDA抽查了400支口红,成分中无一例外含铅。
另外我得说,这种危险还有“性别特色”。许多国家的健康与安全的相关规定,将化妆产品明确地区分为两类,一类产品监管力度小,主要用于女性,称为“美容”类产品,包括化妆品、染发剂等,另一类产品监管力度较大,称为“洗护”类产品,包括洗发沐浴液及香水香氛。这种明显具有性别歧视的条款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作及社交环境要求女性化妆。因此,虽然从古至今,男性因时尚而受害的案例数不胜数,但是,就现代社会而言,社会及科学调研的重点,应该更多地放在那些至今仍被要求穿着时尚的群体,即女性身上,这样,你才能看到延续至今的危险。
本文书摘部分及图片节选自《时尚的受害者》一书引言部分《时尚的死亡陷阱:现实?抑或故事?》,限于篇幅对原文进行了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