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现实世界比基列国更加残酷
在《使女的故事》中,我们把奥芙瑞德停在了这里:“篷车停在车道上,双重门敞开着。那两个人,现在是站在左右两边,一人抓着我的一只胳膊肘拉我上车。我无从知道这究竟是我生命的结束还是新的开始:我把自己交到陌生人的手里任其发落,因为我别无选择。于是,我登上车子,踏进黑暗抑或光明之中。”读者要求《使女的故事》出续作,《遗嘱》便是续作,但并不是人们曾经期待的那个。他们想让我重拾原本的叙事线索。但我不可能重现原本那个声音,因此我一直说不。后来,我看到了通往基列共和国的另一种途径:一段时间后,不同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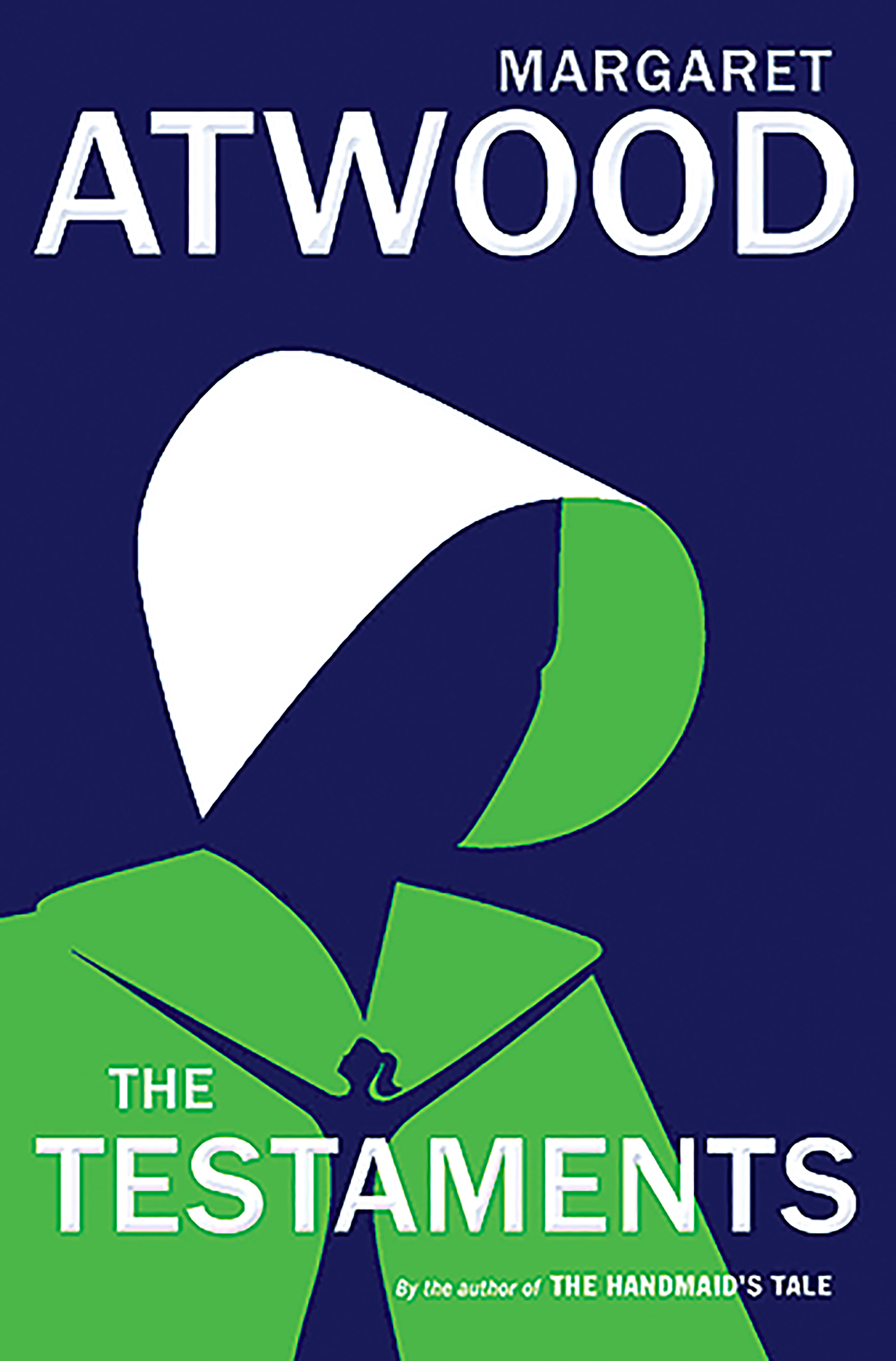
在很多方面,《遗嘱》回答了读者多年来一直问我的、关于《使女的故事》的所有问题。但它也是属于我们的历史时刻,现实中许多国家似乎更多地是朝着基列共和国前进,而不是远离它。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都再次受到了威胁。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国家是否有权力违背你的意愿来征用你的身体,用它来提供服务,也不需要为这些服务付费?但即使在基列共和国,女性也有饭吃,也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从某些角度来看,现实世界更加残酷。
《遗嘱》的故事发生在《使女的故事》结束的15年后。这本书有三个女性叙述者。有两个是新世代的人,并不知晓基列共和国以前的世界。《使女的故事》中有很多描写女性如何难以适应基列共和国的生活,但“对于之后的人来说,会更容易一些。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职责”。在基列共和国成长的少女是怎样的体验?在边境另一边的加拿大长大,把基列共和国视为西方人曾经视之为铁幕的国家——既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又是一个神秘的隐秘王国,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至于第三位女性叙述者:作为一个年长的女性,在基列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秘密影响力会是什么样子?如何在一个独裁政权中获得权力,特别是如果你属于一个被定义为相对无权的群体时?你的背景是什么?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为了避免命运而指责和压迫别人的幸存者吗?你害怕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谁是你的敌人?你可能有自己的秘密计划吗?
自从我开始写《遗嘱》以来,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有些是令人担忧的,预示着西方民主国家对权力的攫取和对自由的压制,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好几个世纪没见过了。另一些则更加充满希望: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正意识到政治和环境的危险——这两者往往同时存在——并组织起来对抗这些危险。

这就引出了我想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从《使女的故事》结尾的历史记载中得知,基列共和国并没有延续下去——是什么导致了它的衰落?在我的小说里,是人。我天性乐观,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萨尔曼·鲁西迪:《吉诃德》从《堂吉诃德》而来,但走出了自己的路

《吉诃德》本质上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小说,它源于三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它们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是怎样的。这也是对事实的认识,对我来说,家庭关系、家庭内部的爱和失败的爱,和浪漫的爱一样重要。兄弟姐妹、父亲和儿子是小说的核心(当然,浪漫也是如此,书中吉诃德对萨尔玛的追求被悲剧性地回应了,但其实它值得被珍视)。另外,这是一部关于变老和面对生命的终结的小说,并对生命的逝去进行了某种猜想。除此之外,人物和故事的细节都是创作出来的,而不只是文字描述。我对自传的渴求已经在回忆录《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中结束了。
写这本书的想法起源于几年前。大约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堂吉诃德》,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读它,我几乎同时想到了自己创作的老傻瓜和他想象中的儿子/伙伴。但他们并不像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萨。我笔下的吉诃德不是愁眉苦脸,而是兴高采烈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相信爱情的乐观主义者,而我笔下的桑丘是个叛逆的少年。而且,他们的旅程也不是以塞万提斯的书为原型的。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伟大的先行者,但后来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不过,两本书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堂吉诃德》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小说”,它试图捕捉尽可能多的人类生活,而这也是我的本能。《堂吉诃德》颇有现代气息,甚至是后现代气息——小说中的人物知道他们正在被写入书中,甚至对这本书的写作有自己的意见。我也希望我的书有一个平行的故事线,关于我的角色的创造者和他的生活,然后慢慢地展示这两个故事,让两条叙述线融合成为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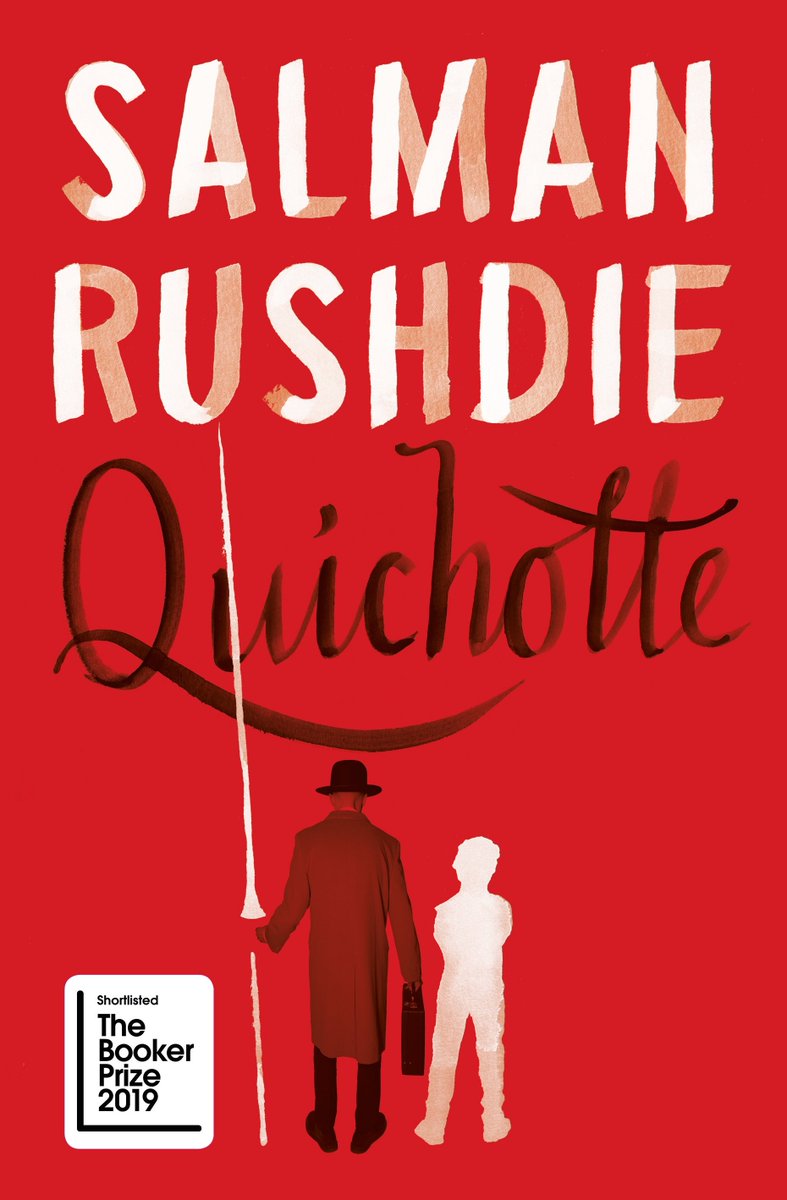
《堂吉诃德》是一本变形的书,充满了离题和故事中的故事,我想自己的书也能拥有自己的道路,成为一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用了许多手法——流浪冒险、荒诞、间谍小说、科幻小说、现实主义情感剧——可以说,我在书中抛出了很多不同的网,试图捕捉我们这个超现实的变形时代的全景。
我想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有趣的书,但在有趣的背后,也想让它呈现一些黑暗的东西:药物成瘾、腐败、种族主义、美国英国和印度的社会分裂。除了塞万提斯,我还想到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以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和《逍遥骑士》等公路故事。很久以前阅读的科幻小说的记忆也帮到了我。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作家(越南裔诗人Ocean Vuong、印度裔作家Jhumpa Lahiri、尼日利亚裔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和有色人种作家(Jesmyn Ward、Ta-Nehisi Coates、Tracy KSmith)正在给美国文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让我深受启发。是的,我认为自己属于这两类人,我很高兴——作为这里面的老人——加入这个行列。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我不想写作为悲剧受害者的黑人女性

小说可以挖掘和重新想象我们的历史,也可以调查、扰乱、验证或思考我们的社会和主观性,还能通过幻想之旅锻炼我们的想象力,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冒险,呈现和探索其中的动机、问题和戏剧性。那么,如果你在自己国家的故事中看不到自己的影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近40年写作生涯中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们英国黑人女性深切地知晓,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写进文学作品,就没有别人会这么做。
但也许她们不应该被期望这样做。毕竟,人类是一个关心那些被认为与自己最接近的同类的种族。但我知道,我们最擅长的,是用自己的知识,透过身为黑人和女性的棱镜来看待这个世界,用自己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黑人女性不能通过非自我的想象来叙述。看看电视剧和戏剧,我的写作是跨越种族和性别的。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但我们能意识到的是,我们这些有抱负的黑人女性作家想要突破出版的重重阻隔是多么困难,而我们并没有占据应有的小说版面。这些东西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激怒和伤害我们,直到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总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没有价值的文学主题。而那些高傲地反驳说文学比特定的人口统计更有意义的人,通常是从特殊的角度写作的——关于异性恋白人男性的特定人口统计。我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成为“人”,但如今我们还没有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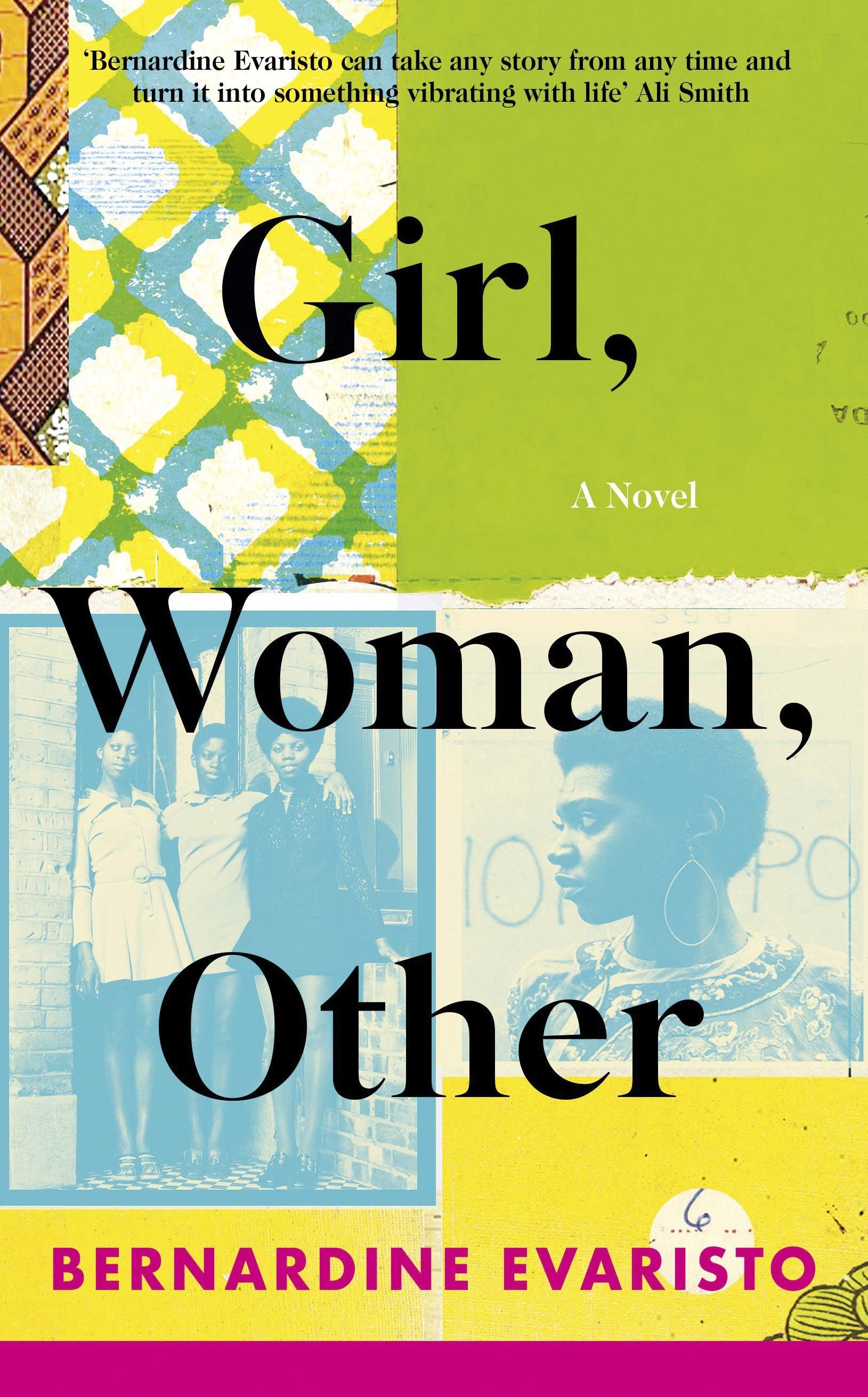
我在《女孩,女人和其她人》一书中使用复调手法作为一种隐形的对抗策略。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得很宏大,告诉大家我们很重要,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重要,一样不完美,一样复杂,一样富有同情心,一样有趣,一样自私,一样迷人。这部小说跨越100多年,有12个黑人女性主人公,跨越几代人,我希望能消除人们对40岁以下女性的偏见,年长的女性也并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这本书中的角色还包括各种性别、职业、地理和文化背景,主要来自于英国、非洲、印度和加勒比地区,而每个角色不同的性别、种族和性行为又表达了工作、家庭、社区和人际关系等主题。例如,哈蒂(Hattie)是诺森伯兰郡一位九十多岁的农民,艾玛(Amma)是一位中年女同性恋戏剧导演,拉蒂莎(LaTisha)是在超市工作的职员。
我称这本书为“融合小说”,我认为它非常好地描述了这样一部作品: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章节,但这些角色也被“融合”到彼此相互关联的故事中。我采用了一种适用于自由流畅的散文风格的描述方法,区别于传统的标点符号,包括大多数句号和所有的语音符号,而采用了我所说的“亲诗意”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让我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无缝切换,表现其外在性和内在性。
最近,我在一次读书活动上谈到了《女孩,女人和其她人》,当时一名没有读过这本小说的观众很自信地猜测,这本书讲的是黑人女性的创伤。这并不是我说的或以任何方式暗示的,但这是她听到的。很明显,她希望,或者期待,我笔下的角色被降格成悲剧黑人的形象,成为受压迫的个人、文化或政权折磨的受害者。但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为悲剧受害者的黑人女性或黑人。我相信希望和救赎,总是给我的角色以希望。一部歌颂英国黑人女性的小说,无疑是围绕着幽默这一主轴来旋转的。我们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喜剧,最重要的是,我们嘲笑自己,就像其他人一样。
齐格奇·欧比欧马:非洲问题的核心是无意识的自卑感

在目睹了一个名叫杰伊(Jay)的人的悲惨遭遇后,我开始写作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成为了后来的《少数族裔乐团》。2009年的时候,我在北塞浦路斯的一所大学上学,杰伊被伪装成外国大学代理人的骗子骗到了这所学校。这个男人内心崩溃,陷入深深的心理危机,几天后最终以横死告终——从高楼上掉下来,头朝下。在那之前的几天,杰伊曾告诉我,他来塞浦路斯是因为他深爱着一个女人。这让我开始探索他和未婚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什么样的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与爱人在一起的一切?我试着追溯他的旅程,我书中的主人公屈农索(Chinonso)在他的奇幻历险中得益于爱的现实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被爱的神话摧毁了。
杰伊特殊的崩溃经历本身就是一次教育。我对人物角色复杂变化的心理非常感兴趣:我曾在自己的小说《钓鱼的男孩》中问,一个爱自己兄弟的人是如何走向仇恨兄弟的;在一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管弦乐队里,我问屈农索是如何从一开始的低调转向复仇。对我来说,这便是我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探索人类情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过程。所以,在故事的设定上,我需要一个特殊的结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学习“气”(chi),这种无处不在的宇宙存在,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名字前加上前缀,变成了“Chi-gozie”。我的外祖父是尼日利亚东部少数几个从未皈依基督教的人之一,自然而然,我的母亲是在奥迪纳尼(odinani)的宗教氛围中长大的,她有着伊博族(Igbo)的世界观,经常提到“气”,特别是当事情发生负面变化的时候,她就会说:“这种困难是你的‘气’失败而导致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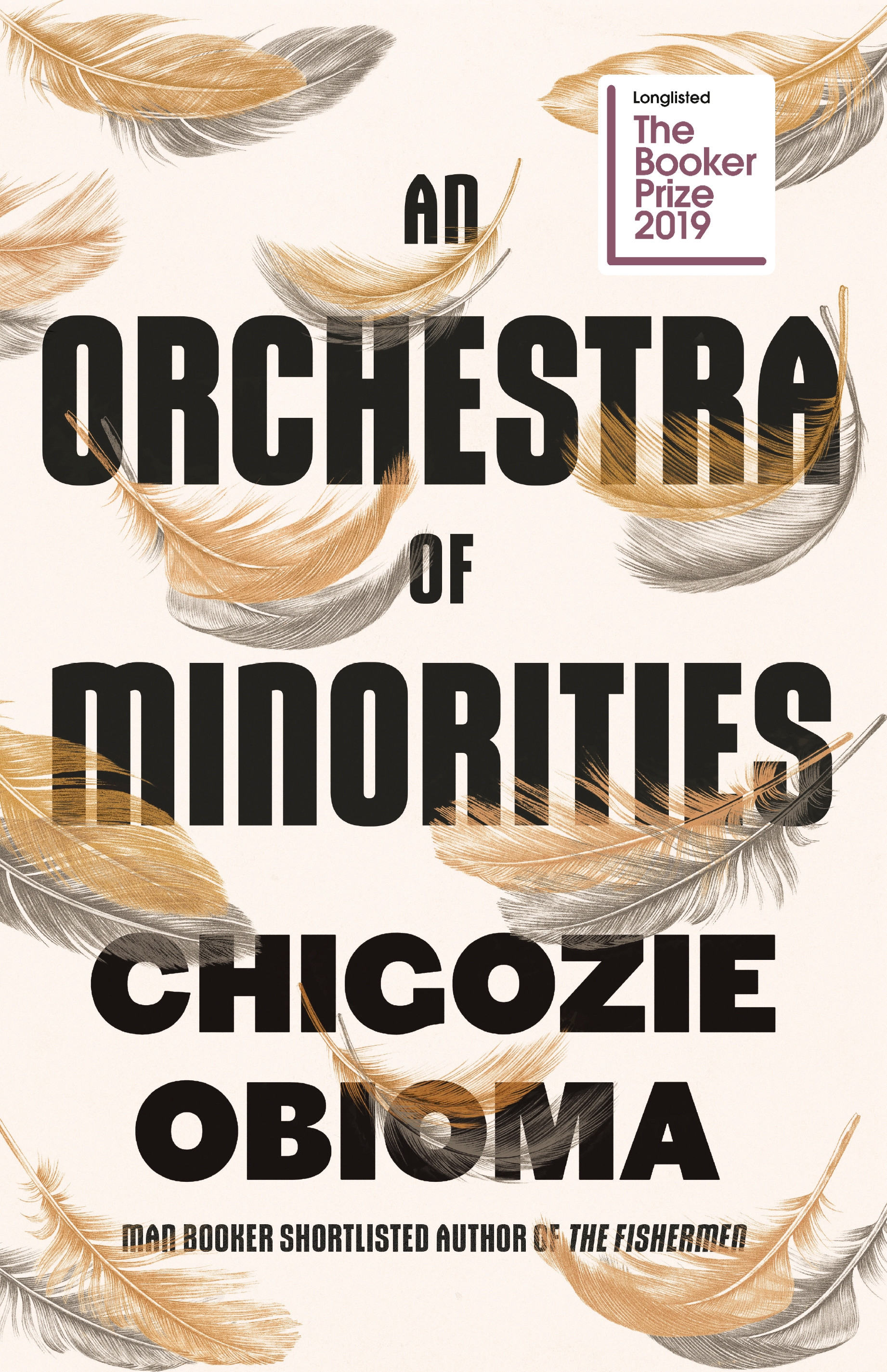
如何讲述这个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定数、命运、自由意志、爱、移民、阶级、种族和报复的故事?我起初只有一些基本框架,直到我遇到了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对我来说,这本探讨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基本支点——自由意志——的书就是答案。我知道我将通过“气”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转世的灵魂已经重生了700年。我会尝试绘制伊博文明的地图,包括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如16世纪伊博族与葡萄牙人的第一次相遇、奴隶制、英国殖民时期、比亚法拉战争和如今的境遇。“气”将是伊博本体论的核心,也是伊博平等主义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而伊博本体论则是我们在殖民主义之前的非洲所拥有复杂信仰的一个缩影,因此我可以确定,非洲在前殖民时代并不是在等待白人来拯救我们的漫漫长夜。我相信,非洲(以及散居在外的黑人)问题的核心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制度,因此我们会有一种应被抛弃的、无意识的自卑感。
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挖掘这些被掩埋的城市,揭示这些宇宙观,让我的人民看到这些真理并提醒他们:“看看我们过去是谁。”这始于书写我们自己的宇宙论小说《伊博失乐园》(Igbo Paradise Lost),在这部小说中,一个灵魂试图证明人类对上帝的行为是正当的。
埃利芙·沙法克:文学旨在重新赋予那些被剥夺人性的人以人性的光辉

伊斯坦布尔郊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墓地,被称为无人陪伴的墓地,那里几乎没有访客。有人说,即使是这个城市臭名昭著的盗墓者也会对它敬而远之,因为害怕“被诅咒者的诅咒”。没有花束,没有大理石墓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姓氏,只有数字,木牌上的数字,一排又一排。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对这个墓地很感兴趣。几年前我去过那个墓地几次,发现自己被这里的宁静所打动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阅读——研究、思考、做笔记。但是收集这里信息是很困难的。这个地方所象征的,大多是关于遗忘、抹去、假装它从未存在过。当名牌上的数字消失时,所有的个人信息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乎每个葬在这个墓地里的人,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弃儿,被他们的家人或社区所回避。他们都被剥夺了葬礼,一个体面的葬礼。这里埋葬着各种各样的LGBTQ人群,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些人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疾病。由于耻辱,他们被送到这里,埋葬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瘾君子、酗酒者、露宿者、失踪者、精神病患者……都是不受欢迎的人。还有那些自杀的人。还有一些库尔德反叛分子的尸体从伊拉克各地被带到这里,因为国家不希望他们成为人民眼中的烈士。除了这些灵魂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难民。在这个不寻常的墓地,一个阿富汗难民或叙利亚难民可能被埋葬在一个图鲁人旁边,你会在报纸上读到后者的难民船试图进入欧洲却倾覆在大海里的新闻,但是这些尸体一旦从水里捞出来,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会被带到这个无人陪伴的墓地。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基什的变性歌手或库尔德的性工作者。作为一名作家,我想至少从这些数字中选取一个,给它起个名字,编个故事……我书中的主角特基拉·莱拉(Tequila Leila)就埋在这里。我相信,文学现在是而且一直都是一种顽固的尝试,去重新赋予那些被剥夺人性的人以人性的光辉。
当我写这本小说时,数字很重要。我对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很感兴趣,这些研究表明,在死亡的那一刻,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大脑可以再活跃几分钟。在某些情况下,最多10分钟。我想再加上自己的38秒。在那个时候,人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如果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确实是最后关闭的,那么一生中留下的记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便成为了这本小说的结构。这本书的头两个字是“结束”。读者马上就知道主人公死了,但随着她的大脑不断运转,她在一分一秒地回忆着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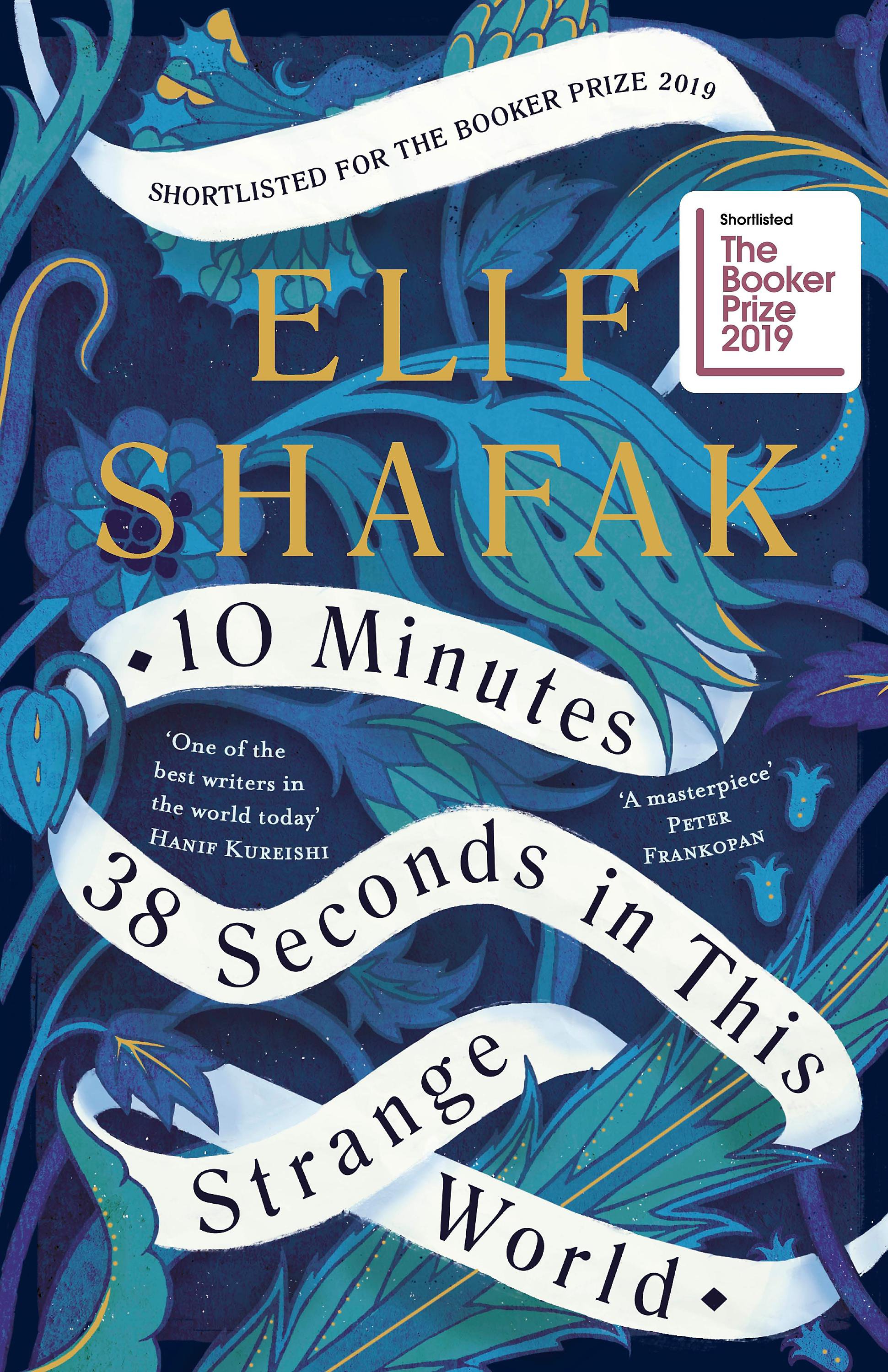
我不想要一个线性的故事情节,因为我们的思维不是那样工作的。正如东方和西方在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融为一体,过去和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头脑中融为一体。非线性的故事线也让我意识到每一段记忆是多么珍贵。每当我翻开新的一章时,我都必须有所选择。莱拉现在还记得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得不删除许多已经写下的东西,不得不写一部更短的小说,一个更紧凑的故事。莱拉记得的东西,主要是通过感官来回忆的,比如柠檬和糖的味道、豆蔻咖啡的味道。也许这与我自己在祖国的经历相呼应。我在生命中一个奇怪的时刻写了这本书,不是去伊斯坦布尔旅行,而是以某种方式随身携带着它。
尽管一切都是虚构的,但莱拉的故事灵感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我曾经在旧城里看到的真实的人和地方。多年以来,我逐渐认识到,除了故事,我还会被沉默所吸引。这本书里有许多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尽管小说涉及了沉重的主题,但依然是一个肯定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赞美了人类的多样性和友谊,以及人们在面对暴力和压迫时的韧性。
露西·埃尔曼:生与死之间的一切都是拼贴

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对人和环境的绝望。但我的写作方式很有趣。事实上,这种方式是来自过去,为了表达一个人的思想活动,我找回了以前的一个技巧:拼贴(collage)。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很喜欢用小图片代替所有名词的故事。这便是一种拼贴的形式,两种不同东西的相遇,预期的和意想不到的——传统的文字和意外的插图。我很喜欢这种不和谐的并置。当你把一件看似无关的事情与另一件相比较时,就会发生炼金术般的奇妙组合。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就很奇妙地有《星条旗永不落》的特色,充满了辛酸和控诉。杜尚用小便池制作的雕塑《喷泉》也是一种拼贴:所有的现成品都是,因为它们在客体和潜意识(或崇高)艺术意蕴之间来回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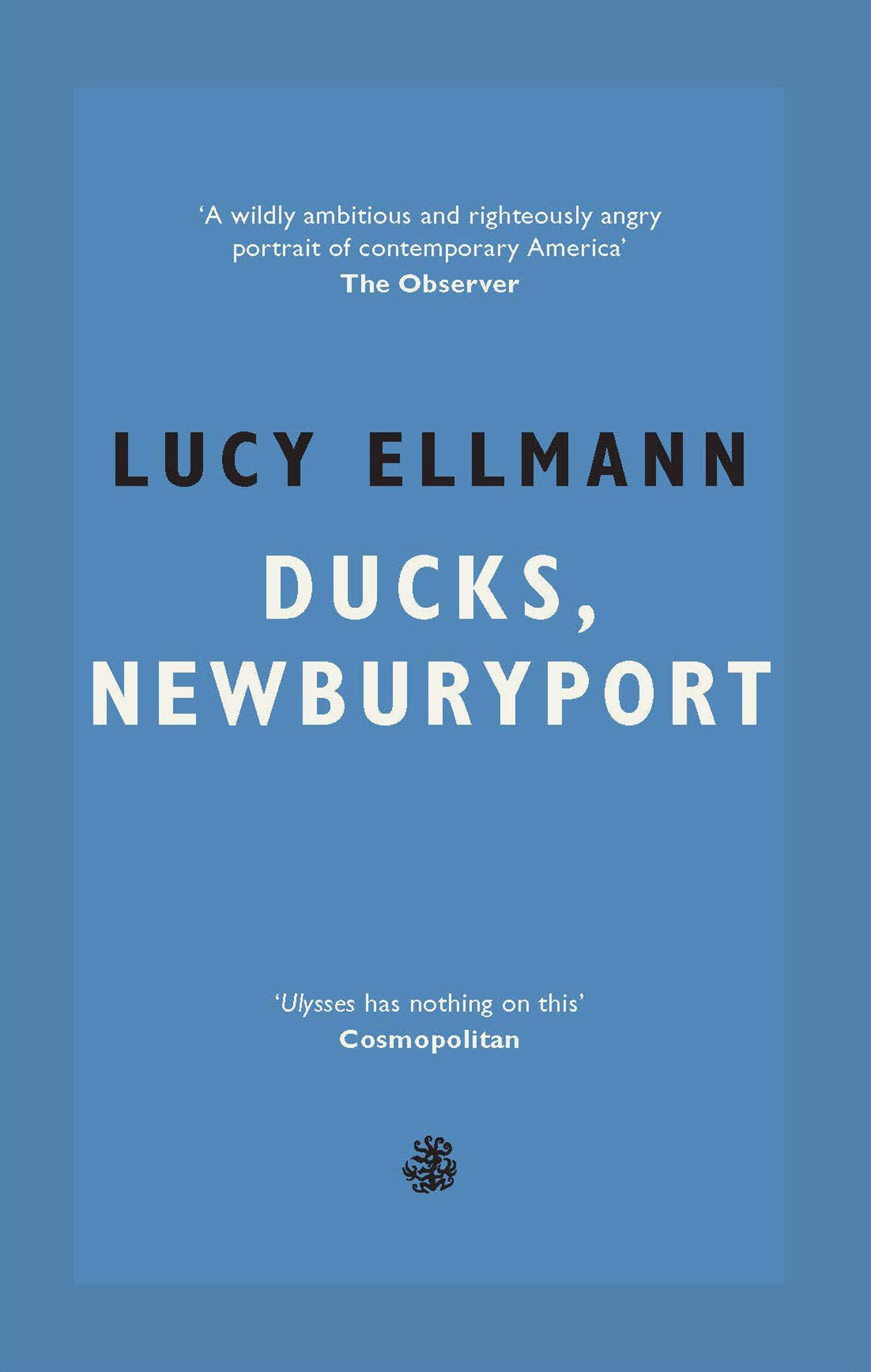
苏格兰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的拼贴展——“剪与贴:拼贴400年”( Cut and Paste: 400 Years of Collage)向我们表明,拼贴不只是20世纪或21世纪的反常现象。令人吃惊的是,在很早之前,不同元素之间的特别结合就开始了。二维拼贴至少可以追溯到纸的发明。收藏珍品的柜子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拼贴:聚合(assemblage)。而在拼贴织物上,各种各样图案的相互组合,令人眼花缭乱。立体派和抽象派表现艺术家也会采用拼贴的形式,例如美国艺术家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流行歌手也是拼贴者,他们会把找到的东西硬塞进自己的作品中。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中,柯特·希维特斯(Kurt Schwitters)便是熟练的纸质拼贴画的实践者,而艾琳·阿格尔(Eileen Agar)则将拼贴描述为“一种受启发的修正形式,一种通过大量的偶然或巧合的干预来取代平庸的形式”。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正在攻读拼贴学的博士学位,并与伟大的美术史学家道恩·阿德斯(Dawn Adès)教授发现了许多研究材料。后来我怀孕了,道恩告诉我,读博士很适合做母亲,所以我继续读博士,不过更专注于孩子。几年后,维拉戈出版社(Virago Press)的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Alexandra Pringle)委托我写第一部小说,我便放弃了学业,改写小说。我在博士期间所做的些许工作,最终在整部小说中形成了零星的拼贴元素。
在那之后,我本想抵制拼贴,但为了《纽伯里波特的鸭子》中角色的内心独白,我又回到了拼贴。我尽量不让这些内容上的跳跃变得太令人费解。我想写一本人们可以读懂的书,一本不需要解释的书。那么我来解释一下!
这本书另一个灵感来源是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他曾经说过“战争是我的大学”。维希留曾写过很多关于20世纪艺术中暴力元素的研究文章,他认为,这些艺术中的暴力元素是对大规模恐怖战争影响的回应。艺术不是空中楼阁,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同谋,在暴力时代,艺术就会变得暴力。所以我们会用错误的方式把东西撕扯和粘贴在一起,然后把疯狂的拼贴扔到空中。我所处的时代甚至可能使我有资格不时地把句子结构弄乱。
我的书主要是关于母性。从一方面来讲,生育不就是拼贴吗?从单个的存在,到两个或多个存在的相互竞争。而死亡是另一种主要的拼贴,在这种拼贴中,曾经有生命的人通过裹尸布、棺材、火焰或六英尺的土壤,以及“我的方式”的张力,被无生命的人所包容。生与死是人生中最离奇的时刻,其间的一切都是拼贴。
布克奖的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14日在伦敦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附:2019年布克文学奖短名单: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遗嘱》
萨尔曼·鲁西迪,《吉诃德》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女孩,女人和其她人》
齐格奇·欧比欧马,《少数族裔乐团》
埃利芙·沙法克,《这个奇怪世界里的10分38秒》
露西·埃尔曼,《纽伯里波特的鸭子》
(翻译:张海宁)
来源:卫报
原标题:How to write a Booker contender – by Margaret Atwood, Salman Rushdie and others
最新更新时间:10/13 11:58




评论